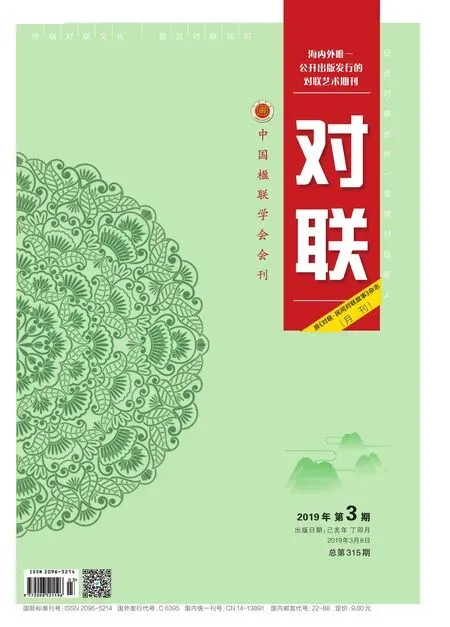詩心酬歲月
張丹薇
時光,輕輕穿過春日的和煦,夏日的火熱,秋日的清涼,在冬日里靜靜沉思。“猶殘臘月酒,更值早梅春”。歲月匆匆,日子簡單而明朗。詩心恰是一杯酒,讓匆匆凝結成溫潤,把簡單濡染到幽香。
“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很喜歡老杜的這兩句詩,有一種氣定神閑的風度。宋人陳與義的詩句講得更直接:“有詩酬歲月,無夢到功名”。浸潤在詩詞中久了,漸漸喜歡避開浮囂,喜歡這一份與古人相處的超然,與自己對話的寧靜。
燈里偶然同一笑,人生何處問多情。結識詩詞,緣于家學。兒時常常看到這樣的畫面:案上一杯清茶,一本厚書,燈下的祖父時而啜茶,時而沉醉地吟誦。我就稚氣問背的什么書,祖父告訴我是好書啊,是唐詩。我懵懵懂懂翻開,答應祖父每天背一首唐詩。納蘭說“人生若只如初見”,然而我對詩的“初見”并沒有一往情深。那時的我更像是個野小子,答應祖父背詩的事常常故意“忘記”。后來上學,直到大學畢業,我的語文成績似乎還好,然而對于詩詞,仍舊“美人如花隔云端”,竟沒有欣之喜之引為“知音”。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緣分在該來的時候總會來,或早或遲。工作后的第十個年頭,一個夏日的午后,偶然間我闖入了網絡上百花綻放的文學部落,叩響了一個叫做“蝴蝶谷”的詩詞楹聯群。群里的才子才女溫文爾雅,最令人傾慕的是他們會寫楹聯詩詞!我被四面八方的唐風宋雨包圍,呼吸間都是詩詞的幽香,從此我滿心喜悅地擁抱詩詞,做了蝴蝶谷的一員。“花落去,燕歸來”,十年間蝴蝶谷幾經曲折,漸漸衰落離散。然而我與詩詞楹聯,卻再也沒有分開。生命中有一些因緣際會,婉轉到不可說,最好的莫過于,對的人,對的事遇上,不再分崩離析。
學詩的時候,也漸漸懂得許多詩內詩外功夫。
詩詞有入門功夫,比如格律。古體且不說,倘若從近體學起,對仗和平仄是渡人的舟楫。倘若沒有耐心學格律,就永遠只能是心向往之,而手不能至。當聽懂平平仄仄的韻律時,詩詞才真正向我們走來。
《紅樓夢》里香菱學詩,如癡如醉。黛玉教她精讀王維、杜甫、李白,以這三人做底子,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黛玉無疑是高明的老師,學詩先要仿古,始能得己。學寫詩詞,一開始就率性而為,就永遠只能是“打油”。一位書法大家告訴我,學書先要臨古人的帖,不臨帖而隨意寫的人,多少年也寫不出名堂來。藝術都是相通的,細細想來,藝術和人生也是相通的。取法乎上,學詩如此,做事何嘗不如此,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與詩相伴的春秋多佳日,我與詩詞也漸漸由新知到故人。我寫春晴“案伏晴光暖,窗開蘭氣舒”;寫秋思“鴻雁未從云外過,梧桐先自雨中看”;寫冬梅“清魂修得同瓊雪,謝卻東風第一枝”。寫七夕“碧海長帷,涼云翠幄,多情不見藍橋鵲”;寫中秋“云微月淡三分夜,露重簫吹一半秋”;寫小寒“拋卻詩書枕上閑,青燈對壁怯生寒”。寫思親“殷殷故里問安恙,不待登高已斷腸”;寫念友“滿城燈火人迢遞,一歲襟期夢有無”;寫人生感懷“眼昧猶能憑外物,心愚卻欲假誰人”……循著詩歌的河流,慢慢找尋內心渴望的光亮,以此酬答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