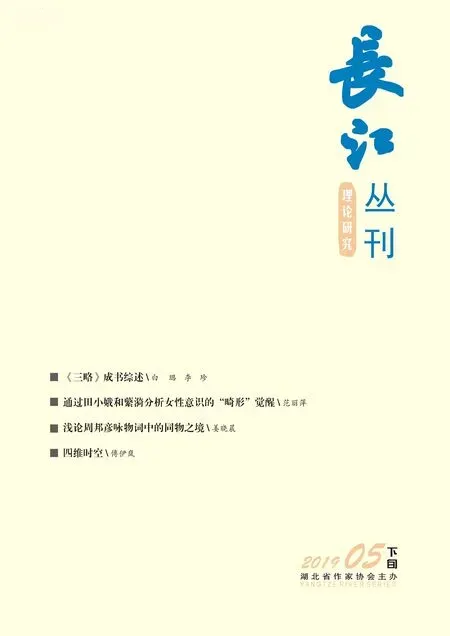中國文化下的人格研究
■
談到特定文化下的人格,其實就是研究“國民性”或“民族性”。心理學家林頓、卡丁納、杜寶婭和丁·威斯特于1945年合著了《社會的心理疆界》(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一書,系統地提出了“基本人格結構”(Basic Personolity Structure)理論。所謂基本人格結構是指一個社會的成員因共同的早期養育和訓練而具有的共同人格結構,一個民族的基本人格結構受該民族的“初級制度”,如生產方式、家庭婚姻、兒童養育等影響,而基本人格結構又投射形成民族的“二次級制度”,如宗教信仰和神話傳統等。為了更為具體和廣泛地概括,林頓又提出一個“角色人格結構”概念加以補充。“角色人格結構”其實意在說明每一個民族都有基本人格特征,而同一民族內部,由于人們扮演角色各異,其人格也是存在差異的。可以這樣認為,“基本人格結構”更注重種族的共性,而“角色人格結構”更關注個性差異。
直到1944年,杜寶婭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眾趨人格結構”,社會成員與基本人格的合致程度,只能以統計數的眾數來表示,也就是說同一民族的特定性格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普遍行為。“眾趨人格結構”這一概念日后為各領域學者所引用,并逐漸發展為“國民性”或“民族性”。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民族性是與該國所處社會文化、意識形態息息相關的。那種被時代文化所深深打下的烙印無法根除和替換。
個體在接受特定文化熏陶時,通過對特定文化的內化及個體社會化后所形成的穩定的心理結構和行為方式。當固定群體共同接受來自文化的浸潤,那么所形成的人格特征就是國民性。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擁有淵源歷史沉淀的產物,其與人格的復雜性和包容性是任何國家也是望塵莫及的。因此,有關中國國民性的研究一直是大批學者爭先熱議的話題。梁啟超曾寫出了若干論文探究中國的國民性,從救國的立場出發,他斷言中國國民性格缺乏獨立性,并為此思考改良之道。魯迅也探討那時的中華民族性格,他的“看客”理論和《阿Q正傳》以文學的手法揭示了那時中華民族性格的弱點。著名學者柏楊以其辛辣的語氣和尖銳的筆鋒控訴了當下中國人的劣根性,也因此歸于中國的“醬缸文化”等等。可以這樣說,所有文人在從自我視角去解讀中國國民性特征時,本身就已經陷入文化標簽的漩渦,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其理論就包含著某種政治訴求和憂國憂民的論調。但是,在心理學領域,我們似乎更關注文化與人格的影響機制、發展態勢以及文化背景下人格特質研究等。
特質心理學家經過幾代努力,提出人格的大五模型,被稱為人格心理學上的一場偉大革命。學者們通過詞匯學的方式,總結概念出五種特質,希望可以涵蓋人格的所有方面。當然,從普遍意義上說,大五人格模型是西方心理學家依據西方參考框架而提出的,對中國人格的吻合度適用性存在質疑與疑問。為此,我國學者王登峰、崔紅等人在考察中國本土文化下成長的人群,對比西方文化的異同,提出更具代表中國文化標簽的大七人格理論,主要包括以下維度:外向性、善良、行事風格、才干、情緒性、人際關系和處世態度。西方的“大五”人格結構反映的是行為或人格特征的五個相互獨立的方面,這五個維度或行為范疇中所涉及的行為很少重合,都是相互獨立的,任何一個維度都有著完整的意義。相比之下,中國人的人格維度在結構上則更復雜一些。不管是帶有西方文化標簽的大五人格理論,還是蘊含中國本土化意味的大七人格理論,都似乎通過用一種模型量化手段來建構起文化與人格間隱約的內涵關系機制。這倒是給我們一個啟發,即種族文化專有制,不同文化背景下必定在其人格上印刻下專屬的特征符號,在中國,最突出的符號就是集體主義和孝順。
中國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im)是相對于西方文化體制下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個體主義文化傾向于把注意的焦點放在個體身上,強調個體的獨特性、獨立性、自主性,強調個體與他人和群體的不同;而集體主義文化把主義的焦點放在群體或社會水平上,強調和睦的關系、人際之間的相互依賴、個人為集體利益所做的犧牲、個人對社會的義務和職責、個體在群體和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中國國民性所體現出的集體主義是與中國集體主義文化相契合的。從道德思想上來講,中國從古至今都奉行“國先于家”、“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道德準則。我們對于為國為集體甘愿奉獻的人物形象總是賦予崇高的英雄色彩,并為之歌功頌德,而并不在意行為結果是否成功。某種程度上來說,如果個體有為集體奉獻的行為,便可定義為道德高尚的形象,一旦有悖于集體主義原則,那么就一票否決個體的全部,并不在意行為背后的心理表征。此種道德準則成為中國社會當下一條無形的鋼索,歷經千年,不曾褪色。從歷史溯源來看,中國一直是農耕文化,所提倡的就是和諧、穩定、協作精神,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讓我們深刻體會到自己和他人是相互依賴的整體。統治者關注的是社會關系的穩定性和和諧程度,身處困境首先便是抱成團,而區別于一個人去戰斗,適者生存在中國集體主義文化演繹下,成了壯年照顧少年、男人照顧女人的抱團形式,而絕非任其弱者被自然淘汰的個體主義。
除了集體主義,中國文化模式下,“孝”成為另一個主要特色。楊國樞認為:“傳統的中國不僅以農立國,而且以孝立國”,這兩點有效地概括了中國的文化特征,他把孝作為本土心理學的研究主題之一。孝文化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之一。孝文化這種存在幾千年的意識形態,必然在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習慣、民德、民風和民俗中留下深刻的不可磨滅的痕跡,它不但作為內在機理深刻影響著現實的制度設計,也作為外在規范影響著人們的行為習慣。中國的孝道文化是被打上國別標簽的,是滲透到中國人骨髓里的東西。孝文化的實質其實就是儒家文化,表現為狹義的順從父母和長輩的意愿,廣義的為以仁愛之心對待普天下的朋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從教育機制上看,孝道主要通過教養方式和親子關系得以傳承。一方面,孩子一出生,從取名字甚至到以后路途選擇,父母更多地表達了自己的希望,這種希望體現在言語、姿勢、手勢和行為等方面,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往往背負了更多的家庭責任和外在壓力,而我們習慣性地稱之為“孝”,因此我們不能反抗,因為一旦反抗,就意味著“不孝”,這在中國是一樁不小的罪名,這是中國文化領域中不被接受的行為。而西方文化下的個體主要是為“自己”活,并不成為誰的附庸,只是為自己為當下負責。另一方面,中國從古至今的等級森嚴的長幼尊卑、上下級關系,深受儒家正統的“天地君親師”觀點影響,致使中國人格中對“孝”的看重,對家庭關系的推崇,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對“孝”的推崇和奉行達到了幾近盲目和瘋狂的程度,不免被文人批為“奴性”。
奧爾波特認為人格是個人對文化環境的一種獨特的適應機制。作為文化產物的人格,必定與文化存在著同源性和契合性。正是中國文化土壤的孕育,才能形成集體主義和“孝”的國民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