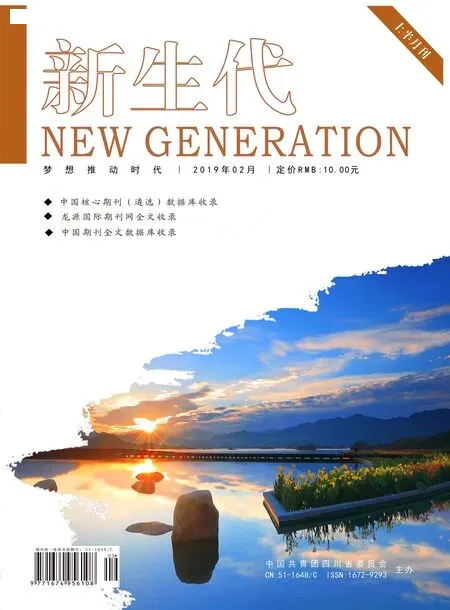價值觀外交與國際政治倫理沖突
劉景明 武漢理工大學 湖北武漢 430070
價值觀外交是指一國政府在對外政策和國際交往實踐中以其國民所認可的主流價值訴求為指導而形成的外交方式。在國人看來,價值觀外交通常被視作西方國家利用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觀作為外交政策的基礎和原則,并在實踐中賦予外交行為以強烈的價值觀色彩的外交方式。
價值觀外交源自西方,根植于其人文觀念和宗教價值之中,構建于其國內政治生態與國民倫理認同的基礎之上,具有利益負載和價值負載的特征,并折射出權利、行為、責任三個層面的國際政治倫理沖突。
一、為何可能存在價值觀外交
從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實現歷史性會面,到日本首相安倍安倍晉三訪華破解多年中日“政治冰封”;從“洞朗事件”后印度總理莫迪訪華到英國圍繞“脫歐”與歐盟陷入拉鋸戰;從沙特與土耳其圍繞記者“卡舒吉死亡案”演繹出來的種種內幕,到法國、葡萄牙等先后表達希望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對比幾年前西方國家以“人權”和“自由”為借口處理國際關系的傳統方式,似乎給人一種天地倒置的感覺。這一系列外交現象的變化,其實都揭示了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所推行的、由不同層次角色參與的價值觀外交正逐漸成為國家間外交的典型代表。
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再固守著“冷戰思維”,以侵犯主權和干涉別國內政參與國際事務的話,只能成為一種陳舊的、毫無影響力的激憤,遠遠無法實現以外交手段維護本國利益和占據國際政治道德制高點的目標。
無倫理不成自助,無正義無以和平。國際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鮮明的規范性、功能性和目的性的價值體系,具有追求和平、發展和正義的價值取向。因此,價值觀外交代表著國際政治倫理富有爭議的勃興與演進。從歷史來看,價值觀外交來源于價值動力和現實動力兩個方面。在國際政治中,全部的外交政策和政治行為都是價值判斷和道德選擇,倫理考量始終伴隨著國際政治的全過程。從現實角度來說,政治活動就是權力與道德的結合。而即使從理想主義角度來看,政治道德與外交之間也是一種正向關系。
不同于以往人們的傳統認知,冷戰后曾長期存在的受意識形態驅動的價值觀爭奪不再是世界政治沖突的根源。在西方看來,意識形態以不再被視作界定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首選方式,而隨著特朗普以“美國優先”口號當選美國總統為代表,以“孤立主義”、“雙邊關系取代多邊關系”、“反對聯盟倡導交易”為特征新型外交關系出現,標志著全球外交關系的變化日益多元化。以往以對人權的尊重和保障作為西方制定世界通行外交政策,遭到“國家民族主義”外交策略的沉重打擊,由此引發國際間外交關系的重新洗牌。而對于以“習近平新時代外交關系”的中國來說,價值觀外交的存在和劇變,給自身造成了一定的戰略困境和國際政治倫理沖突。中國所提倡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政策在當前國際政治全球價值化的時代中,被由于美國顛覆性外交價值觀而陷入迷茫廣大國家所吸引,進而贏得了更多國家的支持和歡迎。由于國際政治本身就是一個國際政治倫理產生、確立和發展的過程,因此倫理取向不僅是國際關系理論各主要思想的根本坐標,也是一切外交分析的標尺。
二、價值觀外交的利益負載和價值負載
與傳統外交不同,價值觀外交集利益負載與價值負載于一身。盡管外交行為包含利益內涵的出現一直在國際交往中飽受詬病,但當國家的外交行為與本身國家利益的聯系日益深化的今天,由國家對外輸出的外交行為往往與本國利益群體的政策訴求形成鮮明對照。
價值觀外交作為保障國家利益的工具,實現外交政策的“名利雙收”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以美國對華政策為例,從最早的擁抱中國,到如今的遏制中國,從希望構建中美新型伙伴關系到再次渲染中國威脅論,從重返亞太政策到挑起關稅貿易戰。美國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反復演變,無不真實貫徹著美國的國家利益。對于歐盟而言,無論對于中國投資歐盟企業設置嚴苛門檻,還是配合美國對于中國擴大市場開放繼續施壓,乃至于依然堅持對華武器禁運,以及堅持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批評,絲毫不影響其成員國與中國的外貿交易屢創新高。乃至于在美國與歐盟的傳統盟友關系因特朗普遭遇嚴重信任危機的情況下,一方面表達希望繼續深化與中國“合作共贏”推動發展雙邊關系的愿望,另一方面以安全為目的,通過收緊中資企業在歐投資的法律規定和監管標準的方式遏制中國,相對于美國的簡單粗暴而言更像是“隱形貿易戰”。而作為相反的典型是日本。在因為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防空識別區等問題導致從中日貿易從“政冷經熱”逐步轉向“政冷經冷”后,隨著日本首相時隔七年后再次訪華而有所回暖。由于價值觀外交具有不可交易性,而日本相對于其他西方國家來說,其國內對西方語境的價值觀熱情度不高,加上當前國際局勢動蕩,不確定性增加,使得中日兩國全球大國間博弈時,有了調整彼此間外交關系的必要。因此相對于西方而言,日本的價值觀外交并不具備深厚的西方傳統外交價值觀基礎,更具有功利性和脆弱性。
在價值觀外交的價值負載方面,德國可以被視作是典型代表。德國的外交政策始終堅持以價值為導向,認為共同的價值觀是保證世界各民族和國家和平共處的基礎。在政治哲學意義上,價值觀外交的負載意義與西方思想領域的最大主流自由主義一脈相承。在價值觀外交的主要鼓吹者中,以西方新教倫理占據主導的國家為多數,他們都因高度契合的地緣同質特性或政治同質結構在國家關系中占據一定的主動權。
康德認為,國際政治問題以國內政治為先決條件。“中國威脅論”或者“中國應當承擔拯救世界的責任”之類的觀點,與其說是當國政治首腦的價值傾向,更不如說來自于其國內民眾價值觀帶來的價值觀外交。
從美國的對華關系上來說,美國在確保對華“利益攸關者”的原則基礎上,對于其他西方國家在對華關系上的施壓始終保持默認態度,這在華為遭遇西方各國以保護國家安全名義的遏制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了,而諸如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不持立場”的觀點,則確保在不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價值觀外交的壓制來尋求在中美外交和貿易關系方面獲得更大利益。從根本上將,這種價值觀外交格局,也是一種隱性的國家政治理論沖突。
三、三個層面的國際政治倫理沖突
國際政治倫理沖突源自對主權原則之于維系國際秩序的重要性的倫理認知差異、多元化的國際政治倫理主體在道德發展水平上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國際政治倫理知識共識的有限性。價值觀外交折射出的三個層面國際政治倫理沖突——權利倫理沖突、行為倫理沖突和責任倫理沖突。
國際政治倫理主體是由政治倫理主體衍生而來,為在國際政治活動中建構并實踐特定倫理的國際政治實體,也是國際政治實體在道德上由他律向自律轉化、過渡的必然結果。國際政治權利倫理沖突主要來自國際政治倫理主體的復雜化和多元化,從而與價值觀外交形成互動關系。國際政治的終極關懷對象,也由民族國家逐漸下沉至“人”的層次,最終形成類似“國際公民社會’的當代國際政治倫理體系,這就與國際視線廣泛存在的權利倫理產生沖突。
與外交政策和實踐相同,一切國家政治行為都是價值判斷和道德選擇。伴隨這種判斷和選擇的必然是國家政治行為倫理的沖突。當一個國家“所做的善大于惡或預防了大惡的發生”時,就獲得了國際政治行為的對稱性。因此,對于價值觀外交必須予以充分的分析和判斷,以此來確定價值觀外交實踐是否符合相稱性原則。以曾經地處歐債危機發源地之一的希臘來說,對待國際經濟援助提出的通貨緊縮和縮減社會福利開支的要求,如果選擇對西方價值觀的固守和排斥,那么它將因喪失來自國際社會的援助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而如果選擇接受則會導致國家政治環境的劇烈動蕩和社會不穩定。基于此,希臘的外交價值觀潛在的折射出國際政治行為倫理沖突,更不用說其國內各政黨領袖因此獲得民意支持。
“道德的第一個命題就是:一個行為要具有道德價值,必然是出自責任”。國際政治責任倫理沖突可以由國際政治倫理沖突推導出來,人們認為國家在被賦予“人格”的前提下,國家的義務和責任構成了國際倫理的主要內容。因此可以說義務和責任是國際政治倫理的兩大主題,一個有效的國際道德體系,其前提必須是有一個被明確指定的、對行為負責的國家領導人。但這也產生了國際政治責任倫理沖突的一個悖論,即領袖雖然是責任倫理沖突主體和主要參與者,但未必是沖突責任的義務者和承擔者。在價值觀外交語境中,對責任倫理沖突的界定和化解變得復雜。在伊拉克戰爭結束后,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組成了完整的倫理沖突系統。將個人從戰爭的道德責任中解脫出來,將這一責任交予政府。伊拉克成為典型的價值觀介入式的國際政治倫理沖突,如果我們不以恰當態度鑒別其中內涵,則會有更多人成為不必要受害者。
在各國政治中,一種開明的仁慈只能來自這樣的記憶:甚至最大的集團也是有個人組成,只有個人才能具有歡樂和痛苦,在這個世界里,遭受苦難的每一個人都證明了人類缺乏理智和共同的智慧。這句話對于作為價值存在的人類理解國際政治倫理沖突,具有特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