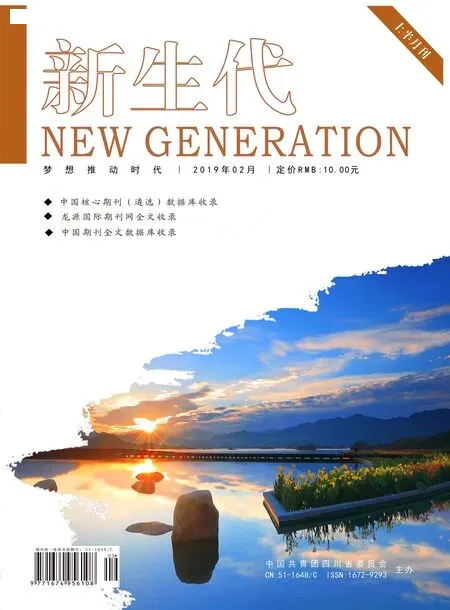馬克思恩格斯的悲劇理論淺析
劉伯麟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天津 300387
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討論悲劇問題。他們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應用于悲劇理論。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文論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革命性變革的產物。
馬克思恩格斯對于悲劇理論的闡釋比較集中在1859年評論拉薩爾的歷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的兩封信中。在信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悲劇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悲劇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沖突。”同時指出,任何悲劇沖突都應該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分析;任何悲劇的產生都有其社會的階級的根源。在馬恩對于悲劇的定義中所謂的“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沖突”其實就是指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會提出一些新的亟待解決的課題或者問題,這些新的課題或者問題所代表的是時代的進步力量,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的理想和愿望無法得到實現,這便產生了悲劇沖突。
當代作家劉心武在他的代表作《鐘鼓樓》中寫過這樣一段話:“時代的步伐既然邁進的這么快,它所來不及清掃的舊時代積垢必然顯得更加觸目驚心,問題在于你要有歷史的眼光,冷靜、沉著地去對待這些東西。”馬克思在談論事物的變化發展時講到:“發展是前進的、上升的運動,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所謂“新事物”就是指合乎歷史前進方向、具有遠大前途的東西;舊事物就是指喪失歷史必然性,日漸滅亡的東西。新事物在舊事物的母體中孕育成熟,它既否定了舊事物中消極腐朽的東西,又保留了舊事物中合理的、適應新條件的因素,并添加了舊事物所不能容納的新內容,它是有新的要素、結構和功能,適應了已經變化的環境和條件,是順歷史潮流的。但是,這些新生力量在一開始是非常弱小的,社會上的舊勢力會對他們進行合力圍剿,期望將其扼殺在襁褓之中。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引言”中所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用這一觀點來解釋文學作品,便很合理的揭示了悲劇產生的根源。從這一角度來看,古今中外的悲劇作品,其悲劇產生的根源也便昭然若揭了。例如在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卡列尼娜最終身著一襲黑天鵝絨長裙,在火車站的鐵軌前,讓呼嘯而過的火車結束了自己無望的愛情和生命。這個悲劇的結尾也說明了歷史提出了“個性解放”的新課題,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這種“個性的解放”沒有能夠實現,最終導致了安娜臥軌自殺的悲劇。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中的寶黛的悲劇愛情故事也是如此,寶玉和黛玉當然代表了社會先進力量,但是不論從小環境——大觀園、賈府還是從大環境——整個封建末世,都沒能給寶黛二人的愛情自由提供充分的條件。與此相似的情節還有很多,如魯迅的《傷逝》、《在酒樓上》、《藥》、《狂人日記》等小說中的主人公,他們雖然擁有先進的思想(理想),是社會進步力量的代表,但是囿于歷史條件,時代沒有能夠提供給他們實現這種理想的條件,面對整個社會的合力圍剿,覺醒者們勢單力薄,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進行抵抗,所以才會產生覺醒者被庸眾“反噬”的悲劇。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悲劇劃分為以下三類:
(一)舊制度的悲劇: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謂舊制度的悲劇就是指在心就歷史的交替時期,當新的制度剛剛建立,舊的制度還沒有完全滅亡之時,舊的制度、階級或某種力量依然相信它還有存在的合理性時,那么這種舊的制度或階級的滅亡是悲劇性的。馬克思在講人類社會發展時說:“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從原始社會發展到奴隸社會,再從奴隸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有的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從這個角度看,社會制度的進步是必然的,舊制度的滅亡也是必然的。但是,文學的發展是復雜的,文學的發展有其特殊性。舊階級的作家在熱情呼喚新制度的到來時,常常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對于其本階級的同情,如法國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家巴爾扎克就在其代表作《人間喜劇》中對于其本階級表現了極大的同情。這同時說明其本階級(資產階級)在19世紀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后來的歷史(如“巴黎公社”)也證明了這一點——資本主義仍處在上升期;再如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對于西楚霸王項羽也包含了極大的同情。從歷史上看項羽當然不代表社會先進的力量,相反劉邦代表的是先進的力量。但是,項羽身上體現了舊的階級和舊的制度的價值,比如,項羽為人坦蕩,鴻門宴即是這方面的證明;再如,項羽對于愛情忠貞不渝,這一點在后世戲劇中多有表現,梅蘭芳先生的《霸王別姬》即是體現。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舊制度的滅亡雖然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但也是悲劇性的。
(二)意識超前者的悲劇:
在馬克思看來,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發展不是亦步亦趨的
它有時先于社會存在,有時落后于社會存在。而意識超前者的悲劇就是指悲劇人物以超前的意識同應該變革的現實時代相對抗,他們的毀滅是帶有悲劇性的。古今中外歷史上存在著大量這類人物,他們的思想意識都是超越于當時的時代的。如古希臘戲劇家埃斯庫羅斯筆下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盜取天火,敢于反抗宙斯的權威,在當時看來他的意識是超前的;又如,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他開始反思“人文主義”,他的思想意識在當時具有著先進性;再如,中國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從某種意義上,他們的意識是超前的,他們不與世俗化的封建社會相妥協,他們在真性情,真血性里挖掘著人生的真諦。再如魯迅先生作品中的覺醒者——《藥》中的夏瑜,《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他們無一不是以超前的思想意識來對抗一個相對落后于他們的時代。這便是意識超前者與時代的沖突,其結局自然也是富于悲劇意義的。
(三)被殖民國家的悲劇:
從世界范圍來看,某些古老的民族變成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殖民地。他們對殖民者的侵略所進行的反抗以及最后的覆滅也是具有悲劇性的。盡管時代是在沒落,但是整個民族合力對于殖民者的反抗以及最終的覆滅是帶有悲劇意義的。
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相結合,推動事物的發展。
在悲劇的根源方面,馬克思提出了人物內心的矛盾是導致悲劇的根源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爾悲劇沖突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把兩個不同人物間的矛盾沖突發展為同一人物內心的矛盾的兩個方面。悲劇人物的不幸結局不是由于外在的矛盾斗爭導致,而是由于其內心的矛盾。
在人物性格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理想的悲劇性格應是矛盾復雜的性格。具有這種性格的人,被內心兩種激情所煎熬,產生巨大的痛苦。內心的矛盾將悲劇人物引向悲劇結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悲劇理論認為悲劇根源產生于主人公的性格缺陷。這從根源上來說屬于性格悲劇的范疇。馬克思和恩格斯將性格的實質內容擴展到社會范圍,這樣悲劇人物的毀滅就與社會發展緊密聯系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