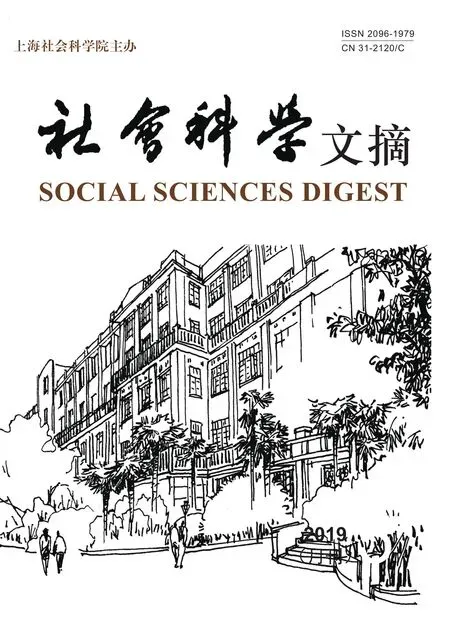探究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的基因奧秘
——當代西方基因政治學述評
基因政治學(Genopolitics)是近十年來西方政治學新興的一個跨學科研究分支,其主旨在于試圖從政治學、心理學、生物學、病理學、遺傳學和認知神經學等跨學科的視角,運用雙生子研究法、大家庭研究法、候選基因相關性研究以及把幾千種基因納入分析過程的全基因組關聯性研究等自然科學方法來分析人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進而獲知態度和行為背后更為深刻的基因奧秘及其作用機制。
基因政治學研究興起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首先,源自“人天生是政治動物”這一經典政治學命題的隱喻。該命題在強調人的政治社會性的同時,也隱含著人具有政治本性的生物學暗示,從而為基因政治學的興起提供了某種指引。自19世紀開始,一些思想家認為,生物學能夠解釋復雜的人類行為甚至政治信念,并進行了若干研究,開啟了基因政治學研究的先河。其次,遺傳科學發展積累的技術和知識儲備提供了技術可能。19世紀以來,許多人文社會學科如心理學、人類學、經濟學和生態學等紛紛與遺傳學進行了學科對話,它們圍繞著進化發展模型找到了清晰的理論聚合,確認人類行為和價值取向與遺傳相關。隨著遺傳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正式完成,為發現和解釋基因作用于政治行為和態度的機制提供了技術可能。再次,認知科學發展的啟示和推動。這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兩個維度。認知科學研究實現了從外在世界向主觀世界的轉變,它希望能夠用“處理物理現象的自然科學去解釋具有精神屬性的意識現象”,這對基因政治學的研究內容具有較強的啟迪,從人自身內部尋找行為和意識的解釋機制成為兩個學科的共同特征和屬性。認知科學也承認環境及文化作用對大腦功能和認知結構的重要影響。這對基因政治學的“基因-環境”范式的形成也具有明顯的啟發意義。此外,認知科學研究者以基因圖譜為線索,利用分子細胞生物學技術,找到了相當數量的抽象認知功能的物理基質(如控制記憶的基因)。基因政治學也因此受到了啟示:既然基因結構能夠影響認知功能,那么它是否可以同樣影響政治意識和政治行為?最后,美國政治極化現象也促進了基因政治學的發展。在過去的50多年時間里,美國政治極化現象嚴重,“否決政治”盛行,政治生活不斷陷入困境,政治和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學者難以理解:為什么在20世紀后期至21世紀早期保守主義運動獲得民眾支持?為什么在美國大選時,公民之間會出現“政治狂熱”和“政治冷漠”的事實反差?部分學者希冀從人的基因之中獲得答案。
基因政治學研究歷經兩個發展階段,即理論假設提出階段(2005—2008)和理論檢驗階段(2008年至今)。
在理論假設提出階段,基因政治學研究內容主要聚焦于兩大理論假設:基因影響政治觀念和基因影響政治行為模式。基因政治學研究者認為,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是先天遺傳性因素和后天社會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他們通過多次實驗發現,“政治自由主義”傾向和“政治保守主義”傾向可能具備遺傳性特征。而在“理論假設提出階段”后期,研究人員發現,黨派認同強度、政治和經濟偏好、宗教態度以及公民責任感等方面也可能受到遺傳因素的影響。基因政治學研究者通過研究發現,政治行為模式或許可以實現代際遺傳。2008年,福勒指出,在政治參與中的個體行為差異可能與遺傳性因素(基因)相關。他們在對洛杉磯地區的雙胞胎選民登記情況進行分析后發現,“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更有可能表現出相似的投票行為,投票行為中53%的變化可能歸因于基因。此外,他們還發現遺傳因素導致占比60%的雙胞胎選民的政治參與行為如為競選捐款、競選公職、為政治組織志愿服務等方面存在著差異。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人員沒有否認社會環境對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的解釋價值,他們從未表達“基因決定論”的觀點。“社會環境與基因共同作用于政治態度和行為”也是基因政治學隱含的一貫假設。
在理論檢驗階段,基因政治學研究者主要發現了MAOA基因、5-HTT基因、DRD4基因和DRD2基因能夠與政治行為和政治態度相關聯。還有學者認為,心理特質是基因與政治參與行為相關聯的中介。福勒和達韋斯(Christopher T.Dawes)最先識別了導致政治參與行為差異的基因,他們發現擁有MAOA基因多態性的人更有可能參加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以及5HTT基因多態性與投票率之間的關系受到宗教活動參與率的影響。在控制了已知的能夠影響投票率的變量之后,高表達的MAOA等位基因大約提高了5%的投票率;在那些活躍于宗教組織的人當中,較長的5-HTT等位基因能夠提高10%左右的投票率。產生這一現象的機制是:這兩種基因能夠轉錄化學物質,對大腦部分調節恐懼、信任和社會互動的5-羥色胺系統產生巨大影響。當其水平較高時,神經遞質活躍度會很高,人們更有可能去參加投票;反之亦然。2009年,他們又發現攜帶D2多巴胺受體基因的A2等位基因的人明顯地比那些攜帶A1等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成為某黨派成員;尤其是攜帶兩條DRD2基因的A2等位基因的人比沒有攜帶者有超過8%的可能性成為某黨派成員。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大腦中多巴胺的水平高低受到DRD2基因的影響,多巴胺水平與黨派意識呈正相關關系,從而左右公民的投票意愿和行為。2010年,福勒等人發現了DRD4基因與政治意識具有緊密關系。他們發現,身上攜帶某種特殊形態的DRD4基因的人更有可能在成年后成為自由主義者,但前提是這些人必須處在能夠為他們提供多元觀點的社會環境中。基因政治學對此的解釋是,DRD4基因會制造出影響和調節多巴胺的受器,DRD4基因的變體7R基因(即DRD4-7R)能夠影響大腦的多巴胺水平,從而左右對大腦的影響。多巴胺水平越高時,個人越有可能成為“新奇事物的追尋者”,同時如果個人在青少年時期朋友數量越多,就會欣然接觸各種不同的觀點和想法,從而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反之亦然。2014年,達韋斯等人發現并證實:心理特質促成了基因與政治參與之間的聯系。心理特質是政治參與行為和基因發生作用的中介物,政治參與行為和政治傾向是被心理特質所調節的,而非受到認知能力、個人控制和外向性等因素的調節。
但基因政治學也面臨兩個方面的強烈質疑和批評。首先,一些學者認為,基因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幼稚”,這主要體現在:一是“相同環境假設”的有效性存在問題。因為同卵雙胞胎與潛在相似反應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在家庭和社會中,這些相同特征很可能會影響兒童的行為發展方向,從而使他們更相似。因此,盲目接受相同環境假設可能會導致對雙胞胎研究的遺傳度測量被夸大。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出現,同、異卵雙胞胎應該擁有(經歷)相同的特質——相關環境。然而,現有研究尚未完全做到這點,相同環境假設的有效性還存在很大的缺陷。二是具體統計方法的不成熟。在既有研究中,基因政治學研究者主要采用多分格相關系數轉換和最大似然框架下的結構方程進行數據處理。反對者認為,基因政治學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是“科學的所有裝飾,例如實證研究、數據收集、使用統計方法分析數據”,“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種存在根本缺陷的實證研究技術”,都依賴于平等的環境假設、不帶偏見的樣本和對所研究現象的準確測量,而現實情況是“他們根本無法克服方法的局限性”。二是批評者認為基因政治學是“貪婪的”還原主義。基因政治學的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二分法夸大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這種“左-右”的二元劃分明顯不符合政治現實;“政治態度是由遺傳決定的”這一假設并不具備合理性,因為它不能比其他假設更好地解釋所要考察的研究對象;“基因影響政治行為”假設也存在問題,因為研究過程不僅存在方法問題,也沒有考慮到群體分層,即由于獨特的祖先遷徙模式和交配做法,不同族裔群體的多態性頻率各不相同。人類行為主要由一兩種基因進行解釋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此,反對者認為,基因政治學研究者所做的不過是妄圖把錯綜復雜的人類態度和行為進行嚴重錯誤的描述,以便把它納入一個“還原論者的解釋模型”,基因政治學是一種“貪婪的還原論”。
學界對基因政治學的批評并不能掩蓋其學術價值。一是促進政治學研究范式的轉變。基因政治學基本上確立了一種“基因范式”,對主流政治學的“環境范式”及其相關的“環境-心理范式”產生了沖擊,“反駁了政治學領域幾十年來的‘環境決定論’,證明了用以解釋態度和行為的社會化范式雖不一定是錯誤的,但在實質上是不完整的”。基因政治學所提出的“基因范式”可以與“環境范式”相互補充和促進,有可能共同形成一種新的“基因-環境”范式。二是推動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突破。包括雙生子研究法、大家庭研究法、候選基因相關性研究以及全基因組關聯性研究等在內的自然實驗法構成了基因政治學的主要工具箱,它具有直觀性、便捷性、可重復性、專業性、科學性、精確性等諸多優勢。基因政治學所使用的自然實驗法還經常利用數據統計工具來分析“大數據集”,從而實現既定研究目標。因此,該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滿足政治學家的科學性期待,能夠有力推動政治學的科學化發展。三是驅動跨學科的交流和對話。基因政治學主要是政治學與自然科學之間交流和融合的結果,它運用生物學、遺傳學、神經科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的知識和技術分析政治主題,為理解政治生活提供了新視角,促進了政治學的知識增長。四是提升了政治學對人類行為的解釋能力。傳統政治學和新政治學知識對人類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解釋力不足,要求政治學亟需從其他領域汲取資源來提升解釋能力,而基因政治學則正好可以有效地提供解釋資源。基因政治學借助最新發展的科學技術手段,找出影響人類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的特定基因,并發現具體的因果機制。這使得政治學對人類行為的復雜解釋朝著更加符合客觀經驗的認識又推進了一步,提升了政治學對于人類行為的解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