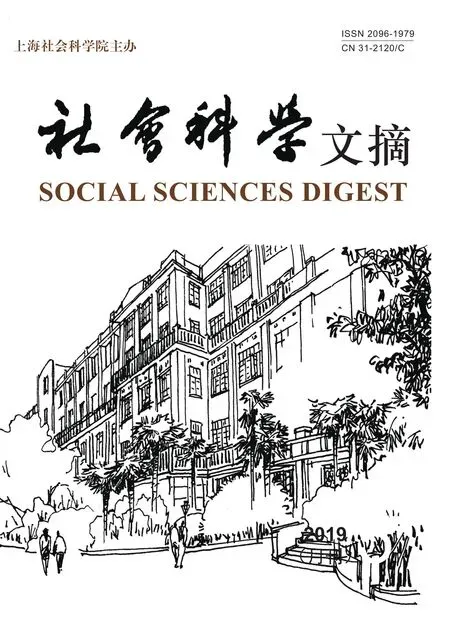國際關系研究“歷史路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誕生于1919年,為了防止一戰這種人類自相殘殺的悲劇重演而開啟的國際關系學,今年迎來了百歲誕辰,而有關國際關系理論前景的爭論也來到了一個轉折點。盡管國際關系學依然是大學中的一個熱門專業,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她能在日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指點迷津,但這個被形容為“美國的社會科學”的學科先是沉湎于理論的構建和范式的爭論,接著又在范式的爭論之后消沉下來。有學者甚至圍繞“國際關系理論的終結?”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當然,也有西方學者早就指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五大弊端”,并就重構國際關系學進行嘗試,提出了“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建設方案;非西方國家的學者也在通過不同路徑構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在所有這些反思、批判、構建和重構國際關系理論的努力之中,“進化思維、權利政治和多元理論”成為重要的發展取向,同時與國際關系演變的歷史和現實更為直接地聯系起來。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遭遇如此尷尬局面的重要原因,是1919年以來世界的發展變化“撐破”了原來人們對解讀國際關系所設計的框架,其內涵和外延的“野蠻”生長早已超越了任何一個單一學科的界限,而國際關系研究“歷史路徑”的拓展或將是其重獲生命力的必由之路。
國際關系研究“歷史路徑”的必要性
首先,所謂的“國際關系”研究自古以來就是歷史研究的一部分,許多歷史學家的經典著作也被視為國際關系研究的經典著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國際關系學的產生也和歷史學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出現這樣一種情形的重要原因是,歷史學一直把人類共同體的演進作為其研究的主要內容,這種共同體包括部落、城邦、帝國,當然也包括帝國之后的“民族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家從事“國際關系”研究并不是“越界”,而是其學科發展的傳統,只不過歷史學家研究國際關系的視角和方法與政治學家的視角和方法不同而已。其次,盡管國際關系理論在美國經歷了一個“去歷史化”的過程,但迄今為止,歷史學中的國際關系研究與政治學中(在中國,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和外交學都是政治學的“二級學科”)的國際關系研究依然有許多重疊之處。特別是在地緣政治研究和大戰略研究方面,歷史學家和國際關系理論家更是難分彼此。許多杰出的地緣政治學家和戰略學家既是國際關系領域中的領軍人物,也是在歷史學領域中享有盛譽的學者。最后,尤為重要的是,對比1919年,我們會發現,這個世界已經被“嚴重地”重新塑造過了:整個世界已經按照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原則組織起來,新興的“主權國家”幾乎蔓延到這個星球的每一個角落。這些“類似單位”表象的背后是傳統的種族、族群、部落、宗教和教派利益的重新組合,是新興政黨的生死博弈,是血與火的“洗禮”。幸運的國家,這一過程綿延數千載;不幸的國家,幾十年過去,依然在國家建設的路上躑躅前行。一戰和二戰之后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都沒有能夠消解掉這些國家的“前現代遺產”,而冷戰后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沖擊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貧富分化,民粹主義卷土重來,新的國家、區域和全球治理模式,以及新的世界秩序,又在探索、過渡乃至重構之中。如何解讀這一被重塑的過程,既是歷史學的責任,也是其他學科包括國際關系學的需求,更有可能是國際關系學的一個新的出發點。
國際關系研究“歷史路徑”的可能性
歷史學的特點決定了國際關系研究“歷史路徑”的可能性。當然,關于什么是“歷史”和“歷史學”,學界有諸多爭論,也有諸多誤解。對于許多其他學科的人來講,歷史或歷史學的價值,就在于把歷史的“真相”挖掘出來。但對于歷史學家而言,歷史和歷史學遠遠沒有那么簡單,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歷史學的突出特點是她的雙重特性:它一方面研究人類所有“過去”的活動,有著獨立的研究對象、領域及理論和方法,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但另一方面,其研究領域又與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相關學科的“歷史”研究部分相交集。有學者甚至認為這種交集不僅僅涉及他學科的“專門史”,而且還涉及他學科的“學科史”。這種“交集”為國際關系學“歷史路徑”的開辟奠定了基礎。
當然,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在考察同一歷史現象時出發點是不一樣的。歷史學家往往傾向于把歷史事件都作為個案考察,努力挖掘出它的特殊性;國際關系學家則傾向于把歷史的分析簡約化,為理論抽象創造空間。在這方面,法國學派的研究呈現了理解國際關系的復雜性,時間變量的多元性和空間維度的多層性。歷史理解離不開時間、空間、記憶、過程等范疇。美國的國際關系研究中常常將這些因素默認為常量,而歷史研究則將其作為影響國際關系的變量來考量。這或許是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陷入“僵局”的原因所在,也是國際關系研究歷史路徑的優勢和價值所在。
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雙邊關系”不同,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在過去百年的演化中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內涵和外延都“無休止地擴大了”。歷史學已經不再僅僅專注于政治史,而是深入拓展到文化史、社會史、觀念史以及環境史等領域,歷史人類學和歷史社會學更是已經各成體系,成為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歷史學也不再僅僅在國別史和區域史方面下功夫,而是在跨國史和全球史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國際關系學也已經超出了“一個傳統學科的想象”,不僅把非國家行為體納入研究范圍,而且也把目光投向資源、環境、人口和氣候等領域,“國際”的范疇被大大拓展了。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都在向學科群的方向發展。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正在經歷歷史性的變化,人文社會科學都在重新匡正學科視角,跨越“國界”的束縛,而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最新“拓展”的領域有高度重合性,這也為國際關系研究“歷史路徑”的拓展創造了廣闊的空間。
國際關系研究“歷史路徑”的選題
國際關系研究“歷史路徑”的選題有許多。首先是對“前現代”國際關系行為體的探究。盡管“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已經蔓延到全世界,但傳統的種族、族群、部落、宗教和教派等所謂“前現代”國際關系行為體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頑固地生存下來,并且在許多新興國家的構建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中東、中亞、東南亞以及非洲等地區。在這些“構建中國家”中,種族、族群、部落、宗教和教派等歷史的演進已逾千百年,而“民族國家”是一種新鮮事物,許多國家的邊界都是西方殖民者人為制造出來的。當一個新興國家的民族認同或國家認同一直不能取代或超越其他社會組織認同的時候,這個國家的聚合的力量就難以平衡和戰勝分裂的力量,國家建設的任務就依然沒有完成。
其次,國家的歷史類型學分析。關于國家的類型學分析,政治學已經有大量優秀作品問世,但大多沒有把足夠的歷史背景納入其中。面對當今國際關系的發展變化,有學者已經放棄對國家的專注,轉而把目光投向族群研究。當然,被納入國家體系的族群、部落和宗教或教派等社會組織,也已經與原初不一樣了,進入了一個新的演化過程。國家的歷史類型學分析,就是要把這種演進過程的取向分析出來,以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前景有一個明確的把握。筆者曾經以國家形成的歷史背景為線索,把當今國家分成“已構建國家”、“再構建國家”和“構建中國家”,并試圖對“構建中國家”再行細分。這樣一種分法也是初步的,期待學界同仁有更為精致的劃分方法。
最后,人類共同體演進的邏輯。人類歷史演進的過程,也是“我者”與“他者”之間分化與轉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不同類型和規模的共同體演進的過程。比如在古埃及,“我者”指的就是居住在古埃及疆域內有著相同的價值觀念、語言文化、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的群體,反之即是“他者”。“我者”與“他者”的關系還有三個遞進層次:相互對立;“我者”的構建以承認“他者”的存在為前提;二者非此即彼的關系也可以發生轉化,并最終走向認同。古埃及文明中“我者”與“他者”的關系在人類歷史的演進中是一種普遍現象。“我者”的聚合便是共同體形成的過程。關于共同體的定義有許多,一般指的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聚合在一起生活的群體、組織或團隊”的含義,既包括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關系和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家庭,也包括以共同的經濟生活、居住地域、語言和文化心理素質為紐帶形成的民族。實際上,當今世界并不僅僅是由威斯特伐利亞式國家構成的,而是由千百個共同體聚合而成的世界,其中既包括在主權國家之內或跨國界存在的族群、部落、宗教或教派組織,也包括以超越主權國家為特征的區域共同體等。
我者與他者的轉換,人類共同體演進邏輯的研究,將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彈性”發展指明一個方向。國際關系理論不應該“僵化”在國家身上,因為現實的“國際”已經不僅僅是國家之間的互動,而國家也只是人類共同體演進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主導單位而已。如果要想消除國家之間的“零和”游戲,擴大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消除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負面”作用,就必須逐漸推進“我者”與“他者”之間的轉換,構建更大的超越國家邊界的共同體,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奠定基礎。這似乎已經超越了國際關系理論的初衷,但它與當初創建國際關系學科的目標相一致,這就是消弭戰爭,實現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