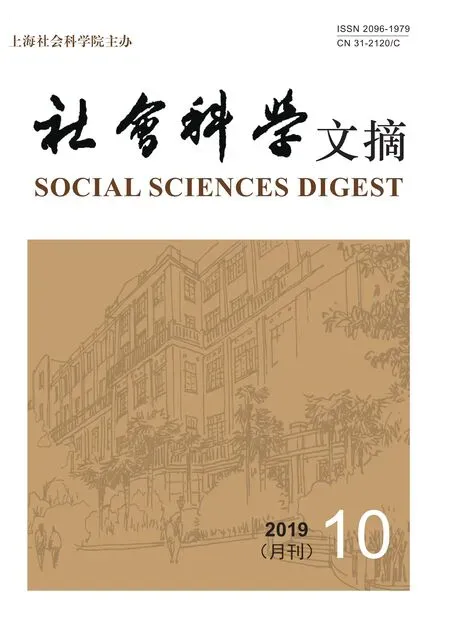國際安全競爭必定導向國內軍事化?
——競爭態勢、戰略反應與制度調適
文/肖河
安全領域“國際—國內”范式的關切、缺陷及其研究意義
探討國際競爭對國內制度的影響是一種“逆轉的第二意向”(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研究,即不是關注既定的國內結構(domestic structure)對國際行為的影響,而是反過來強調國際行為可能改變國內結構。這一范式可被稱為“國際—國內”理論,其將國內結構作為因變量并不是要否定國內結構的重要性及其塑造國際結構的能力。相反,正是因為重視國內結構對國際行為和國際環境的影響,才必須打破對國內結構的簡單化認識,去深入理解其形成和變遷的國際動因。
美國社會學家哈羅德·拉斯維爾(Harold Lasswell)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社會的影響,于1941年提出了“堡壘國家”(garrison state)的概念,用社會學的語言闡述了隱含的“國際—國內”理論——較高暴力預期的國際環境將促進各國的軍事化。
“堡壘國家之爭”雖然是一條重要線索,但是并非國內—國際理論的源泉。美國政治學家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指出,“逆轉的第二意向”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約翰·西利(John R.Seeley)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國和魏瑪時期的德國歷史學家奧托·欣茨(Otto Hintze),其中后者顛覆了“從亞里士多德經馬基雅維利、孟德斯鳩至馬克思的所有建立在內因之上的政治理論”。在發表于1902年的一篇論文中,欣茨指出,無論是馬克思還是黑格爾都是孤立地考察一國的上層建筑或精神意志,從而將整個外部世界都從國家的發展中排除出去。與之相反,他主張一國與他國的互動至少是與一國內部因素同等重要的因素。
欣茨之后,最出色地發展了這一學術傳統的是美國歷史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他的研究重點是從國家能力的角度考察國家間競爭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影響。其理論是國際安全競爭決定了在資源汲取方面擁有獨特優勢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成為歐洲的主流國家形態。蒂利特別指出,民族國家之所以適應安全競爭,并非是其能實現最大程度的軍事化,而是能夠更好地平衡強制(coercive)和資本(capital)的關系。與阿爾蒙德的線性的政治發展理論不同,蒂利不認為國家的發展是單向度的,而是遵循一種建立在歷史機遇和偶然之上的特殊規律性。國家在面對國際安全競爭時可能無動于衷,它們的制度反應也是多樣化的,結果也各不相同。
總體而言,國家因國際互動而導致的制度趨同是國際—國內研究的一大關切。特別是在國際安全領域,大部分研究認為,國際安全競爭總是會鼓勵國家強化社會資源汲取,從而具有更多的強制色彩。它們將國際競爭對國內結構的影響視作同質、單向的作用,即推動國家汲取更多資源。在競爭中,如果各國國內結構的發展存在差異,那么這往往被歸因于各國的內在稟賦。由于將國際安全競爭的影響視為同質的作用力,這降低了該自變量的重要性。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而言,這種對國際安全競爭作用的簡單化正是現有研究的缺陷所在。
重新審視國際安全競爭與國內結構之間的關系也有其政策價值。在中國持續崛起、與外部世界的安全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之際,堡壘國家論是否適用于中國同樣是一個問題。歷史上,不少新興強國都因此遭遇崛起失敗。總之,從理論和政策角度來看,審視國際安全競爭是否會推動國內結構的軍事化均有其意義。
國際安全競爭的分類與國內結構變化的界定
(一)區分國際安全競爭的類型
在拉斯維爾、欣茨和蒂利的理論中,國際安全競爭并非直接導致軍事化,需要以對安全威脅的“恐懼”作為中介。只有當國家對于國際安全威脅切實感到恐懼時,后者才能發揮作用。只有當對暴力的預期(expectation of violence)更加迫切時,暴力精英取代交易精英成為國家主導者的設想才能變為現實。顯然,并非所有的安全競爭都會給國家帶來同等程度的恐懼。因此,應當識別出能夠顯著提高暴力預期的安全競爭。
應當認識到,在一對安全競爭關系中,互相競爭的國家基于力量對比的差異,可能對競爭產生不同的感知,從而采取不同的內部制衡。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在《大戰勝利之后: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后秩序重建》一書中提出,霸權國與其他國家的實力差距會影響前者的偏好和行為——差距越大,霸權國越傾向于通過合作和自我限制來鎖定長期收益;反之,則更不愿意受到限制。對力量對比長期變化的感知也會影響國家行為。國家在面對短期和長期的力量對比失衡時會采取不同的內部制衡策略。在很多研究中,經濟發展增速被當作識別力量對比趨勢的指標。這樣一來,根據國家對現有和長期力量對比的感知,能夠得出一個國際安全競爭的分類矩陣。
(二)界定國內結構的軍事化
古勒維奇較為系統地歸納了國內結構(domestic structure),將其分為政權類型(regime type)和聯盟樣式(coalition pattern)兩大類。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作為政權類型的國內結構。接下來,需要明確軍事化的概念。這種在權力和資源分配上偏重軍事部門的特征有時被稱為軍國主義,不過本文使用的是更加適度的軍事化的概念。這是因為,除非發生革命,外部環境對國內結構的影響是在同一或者相似政權類型下的漸進作用,大多是量的變化,罕有質變。軍事化對應著安全、經濟和政治權力分配,這一概念涉及國家對暴力(violence)、商品(good)和政治實踐(practice)的管理。
在暴力管理領域,廣義軍事化的極端狀態是軍人集團完全掌握了政治權力,不存在政治中立的職業軍官集團;狹義軍事化則僅是指軍官集團政治權力的提升。在經濟管理領域,廣義軍事化意味著國家對于經濟的干預增強,特別是在物資的生產和分配上;狹義軍事化則意味著軍事部門在國家資源分配中的地位上升。在政治實踐管理領域,廣義軍事化意味著權力中心對整個國家的暴力控制增強,在權力集團內部則表現為領導者的個人專斷,在整體民主的國內結構中同樣可能出現局部和有限的軍事化;狹義軍事化則體現為服從權威、追求絕對安全等保守的軍事倫理成為主流價值。
軍事化強調對權威的服從,以功能性討論代替合法性討論。究其實質,軍事化國家給予社會的“受保護的協商”(protected consultation)更少,公民從國家的專斷行為中得到保護的可能性更低,公民和社會集團對國家的制約逐漸消失。軍事化的實質后果是國家削減或者終止了與社會的利益協商和交換。
國際安全競爭與國內結構變化的作用機制
在明確了自變量的區分和因變量的概念后,接下來將建立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框架。
(一)從國際安全競爭到安全戰略反應
國際安全競爭必須被參與競爭的國家及其社會感知,才可能進一步作用于國內結構。由于起直接作用的是對安全競爭態勢的認知,其必然帶有主觀性。在“競爭—戰略—制度”的邏輯鏈條中,首先要確定不同態勢的國際安全競爭與國家戰略反應之間的關系。由于國家在實力上不可能完全一致,同時,對實力各組成部分的威脅感知也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很少有在認知上勢均力敵的競爭。按照對長期和短期力量對比的認識,感知可分為四類。它們的可能作用如下:
第一,短期優勢意味著一國擁有比競爭對手更充裕的軍事力量。這一方面意味著更強的威懾力和更自由的政策選擇,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更沉重的長期負擔。擁有短期優勢的國家傾向于最大可能地利用現有優勢,獲得最大化的戰略收益,彌補在長期經濟增長中的損失。
第二,長期優勢意味著一國擁有比競爭對手更強勁的經濟潛力。這意味著競爭時間越長,其在競爭中就越有利。擁有長期優勢的國家傾向于避免短期攤牌,通過拉開潛力差距來威懾對手。其戰略原則是避免反應過度,僅僅將部分經濟能力轉化為軍事力量。在軍力建設中,其會重視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建設”、防止資源浪費。
第三,短期劣勢意味著一國的競爭對手擁有更充裕的軍事力量。這會鼓勵后者發起安全挑戰,前者將面臨更緊迫的近期風險。此時,一國會將經濟潛力盡量轉化為足以彌補差距的軍事力量。由于風險緊迫,其將通過內部資源汲取的方式來實現轉化。在處于危機狀態時,這種緊急轉化戰略表現得最為明顯。
第四,長期劣勢意味著一國的競爭對手擁有更強勁的經濟潛力。此時,一國并不面臨緊迫的近期風險,但是其在安全競爭的地位將被持續削弱。因此,其將以內部動員(internal mobilization)的方式來增強國內的經濟基礎。
(二)從安全戰略選擇到制度調適
由戰略反應引發的制度調適在大部分情況下不會是“大刀闊斧”的變化。本文無法全面考察一國所有的制度調適,而是集中于軍政關系特別是文官控制的機制上。這是因為,該部分能夠最有針對性地考察國家的軍事化程度。
文官控制的核心是規制軍事部門,其有三方面內涵:(1)政治規制,包括軍事部門是否受到文官部門的控制以及受控程度;(2)政策規制,包括軍事部門在政策制定上的影響,這包括軍事部門及其主導的軍事戰略和軍力建設是否服務于文職部門制定的內外政策;(3)資源分配規制,包括軍事部門在預算分配中的影響。
融合與分離、集中與分散這兩組概念是理解軍政關系的關鍵維度。融合與分離在于政治層面,體現的是暴力部門和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相互滲透關系。融合意味著相互滲透較強,分離則意味著相互滲透較弱。集中與分散指的是政策和資源分配中的決策原則,是“全體一致”“少數服從多數”還是由最高權威獨立決策。極端的分散要求在決策中遵循全體一致原則,這大多意味著軍事部門將對政策和資源分配擁有否決權;集中則意味著決策者能夠更好地排除軍事部門的影響。
第一,當一國采取收益最大化的戰略時,其原則是利用短期力量優勢獲取收益。這會導致擴張性的對外政策,鼓勵各部門追求自身目標。此時,決策權會相對下放,軍事部門的自主性將會增強。但是由于已經擁有短期優勢,國家在資源分配上會偏向維持現狀。同樣,對現狀的滿意不會鼓勵政治層面的顯著變化。
第二,當一國采取防止反應過度的戰略時,其原則是避免資源的無謂消耗。這會導致收縮性的對外政策,限制各部門追求自身目標。此時,決策權將會被收回,軍事部門的自主性將會降低。同時,該戰略還會增強財政約束,減少消耗性資源投入。為了克服軍事部門的阻力,通常還需要更加集中的資源分配機制。為此,還需要進一步削弱軍事部門與其他部門的聯系,在政治層面趨于軍政分離。
第三,當一國采取增強實力轉化的戰略時,其原則是彌補現有力量差距。這會導致擴張性的資源分配政策,滿足各部門的資源需求,放松財政約束。這通常會帶來更加分散的資源分配機制,鼓勵各部門追求自身目標,下放決策權。在這一過程中,軍事和相關工業能力的增長會被視為優先目標,政府和社會的其他部門在很大程度要為此服務,其結果將是暴力部門的政治地位和對內干預能力上升,在政治層面將趨于軍政融合。
第四,當一國采取趕超發展的戰略時,其原則是彌補長期力量差距。這會導致擴張性的經濟扶植,將資源集中于少數關鍵部門,短期內會抑制對軍事部門的資源投入。這會帶來更加集中的決策和資源分配機制,軍事部門的自主性將會降低。但是該戰略會讓國家更多介入社會事務,軍事部門也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些經濟和社會部門可能會明顯地軍事化,在政治層面將趨于軍政融合。
不同戰略引發的制度調適方向可能相反,但兩個方向上的影響不一定相等,其最終影響取決于相對強度。歸納而言:第一,當一國處于長期劣勢時,其在政治層面的軍事化將較為顯著;第二,當一國處于短期優勢時,趨于集中的資源分配會顯著抑制軍事化;第三,當一國同時處于長期和短期優勢時,“去軍事化”效應將非常明顯。總而言之,沒有國際安全競爭未必會帶來非軍事化,而安全競爭有時還可能有助于抑制軍事化。在這里,安全競爭不再是單向的作用力、僅僅存在強度上的差異,而是帶來了更多可能。
國際安全競爭與制度調適的案例分析
在提出了關于國際安全競爭與國內制度調適的新框架后,以下將通過歷史案例展示其作用機制。在案例選擇上,主要目的是驗證避免過度反應和收益最大化這兩類機制。這是因為,競爭劣勢對軍事化的促進作用與傳統理論相似,沒有必要重復論述。相反,驗證國家在國際安全競爭中的短期和長期優勢會在資源分配、政策和政治層面抑制軍事化才是新框架的價值所在。案例中的安全競爭越是激烈,就越能證明其解釋力。基于上述理由,本文選擇了冷戰初期(1945—1950)的美國為單一案例來展示國際安全競爭、戰略反應和制度調適之間的作用機制。
(一)冷戰初期美國國家安全機制建構的兩種方案
1945—1950年是“冷戰美國”(Cold War America)的關鍵塑造期。這一時期,美國外交的主線是美蘇由“偉大聯盟”走向激烈對抗。制度調適的主線則是不同政治力量圍繞《國家安全法》展開的立法競爭,以及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和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的建立與發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的1944—1945年,以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和陸軍部部長史汀生(Henry L.Stimson)為代表的陸軍部門逐漸形成了美國應當改革國家安全機制的認識,其主要訴求是建立一個由內閣級別的文職部長領導的行政部門,統一管理陸海空三軍、承擔制訂軍事戰略和向總統提供整體國防預算的職責。這一方案意在減少因軍種獨立而產生的重復建設和部門本位主義,有利于制訂高效的國防預算陸軍的立場得到了以美國總統杜魯門為首的文職部門的歡迎。
與這一立場針鋒相對的是以海軍部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James Forrest)為代表的海軍部門,他們認識到,統一的文職國防部將意味著海軍失去獨立的預算權。為此,海軍派開始利用1945年后美蘇之間逐漸緊張的外交關系,向國會提出了以“為全面戰爭做全面準備”(total preparedness for total war)為原則的《埃伯斯塔特報告》(Eberstadt Report)。該報告涉及軍政關系的內容主要有三點:第一,維持分散決策的獨立軍種架構不變,將空軍從陸軍中分離出來;第二,建立由總統擔任主席、有權制定和審查外交和軍事政策以及國防預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三,建立協調產業政策和軍事戰略的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 Council)。
對比兩個方案,以應對“全面戰爭”為前提的《埃伯斯塔特報告》的真實目的是通過分權為包括海軍在內的各軍種在資源分配中獲得更多話語權。在政策上,報告試圖通過軍事部門首長和軍種參謀長占多數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來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部門對美國最高決策的強大影響制度化,使得軍事部門可以名正言順地插手外交政策。在政治上,報告試圖通過設置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讓產業界與軍事部門更緊密地結合。以此而言,在1945—1947年間的國家安全辯論中,確實存在借助對美蘇“全面戰爭”的恐懼推動軍事化的政治力量。
(二)兩種調適方案的戰略邏輯
對于海軍派而言,在美蘇關系由于波蘭選舉、土耳其海峽通行權和德國戰后管理問題而不斷惡化的情況下,渲染蘇聯的安全威脅和美國的安全需要成為最優政治策略。然而,《埃伯斯塔特報告》及其背后的“恐懼邏輯”并未打動整體的美國政治精英。該觀點既未能在行政部門中獲得支持,遑論立法部門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美國政治精英認為自身在美蘇競爭中擁有巨大的短期和長期優勢,發生直接軍事沖突的可能性極低,沒有必要過多地消耗資源。
“遏制政策之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在該時期清晰地闡述了防止反應過度的戰略。在1948年的國家安全評估文件中,凱南指出,雖然美蘇之間存在激烈競爭,美國也應該堅定地遏制蘇聯,但是蘇聯并不構成軍事威脅。凱南的觀點契合了美國政府和國會的主流看法。由于美國擁有相對于蘇聯的短期和長期優勢,可以毫無顧忌地一邊推行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等擴張性遏制戰略,一邊在國防開支上精打細算,防止不必要地資源浪費、損害長期經濟潛力。這正是利益最大化和防止反應過度這兩種戰略的組合。這種組合也被稱為“精打細算的冒險”(calculated risk-taking),即基于對蘇聯的顯著優勢,因而愿意承擔現實軍事力量無法完全支撐全部外交承諾的風險,以同時實現短期和長期收益的最大化。
(三)雙重優勢戰略的制度反映
收益最大化和防止過度反應的雙重戰略主導的制度調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1945—1947年的第一階段中,海軍派通過充分動員相關利益集團建立了一個分權的國家軍事部門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及體現總體戰需要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但是后兩者均遭到政府和國會的“無害化”改造,國家安全委員會由決策機構降格為咨詢機構。在1947—1949年的第二階段,杜魯門對分權的國家軍事部門施加嚴格的預算紀律,并以國務院來主導國家安全委員會,抑制了軍方在國家安全事務上的影響。這一雙重限制引發了軍方的激烈內斗,顯著削弱了軍隊的威望。最終,政府通過1949年的修正案實現了建立集中的國防部的初衷。
1949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法修正案》,將國家安全部門改組為國防部,剝奪了各軍事部門和部長的內閣地位、國家安全委員會席位和直接接觸總統的渠道,明確規定了“在遵循總統的權威和指示下,國防部部長能夠決定以何種形式和方法準備、發表和論證國防部的軍事預算評估,并且管理一切已批準的項目”。相應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決策方式也由一致同意變為多數決定。這一修正案的通過標志著美國最終建立起針對軍事部門的更為嚴格的文官控制,體現了“精打細算的冒險”這一雙重戰略在制度層面的勝出。
(四)小結
美國在冷戰初期的國家安全機制建構表明,一國在日益激烈的國際安全競爭中完全可能采取去軍事化的制度調適,而且這與推行擴張性的外交政策之間并不必然存在矛盾。在這種看似矛盾的組合之下,一以貫之的是美國政治精英對自身的短期和長期優勢的確信,以及建立在這一認知基礎上的戰略——在不增加軍事投入的前提下積極遏制競爭對手。在批評者看來,這種做法忽視了國防安全的專業性,將反映社會價值需要的政治決策凌駕于反映安全功能需要的軍事評估之上,但恰恰是這種做法顯著削弱了軍事化對軍事部門乃至整個政治制度的不良影響。這種去軍事化又是以軍事部門內部的集中決策和軍政部門間的分離為特征。
結論:競爭態勢感知的塑造
針對“逆轉的第二意向”研究在安全競爭議題上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來解釋安全競爭對國內結構的影響,其中的關鍵中間變量是一國的決策精英如何感知自身在安全競爭中的態勢。與強調安全競爭的強度差異的傳統邏輯不同,本文主張以長期和短期中的優勢或者劣勢地位來對競爭進行分類。在這一基礎上,競爭態勢的不同感知將引發不同的戰略反應,不同的戰略反應則會進一步呼喚相應的制度調適。可以看出,并非所有高強度的安全競爭都會促進國內制度的軍事化,相反,長期和短期優勢都能夠有效抑制國家的軍事化沖動。以此而言,安全競爭本身就存在對國內制度的積極影響,競爭和優勢感知的共存能夠最大程度地引發這一效應。
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不依賴于其他特定的單元層次的因素來構建安全競爭對國內結構影響的理論,而是以競爭中的長期和短期力量對比這一更加普適性的因素作為變量,這能夠顯著拓寬該框架的解釋范圍。本文認為,不同類型的國際安全競爭會對國內結構產生不同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并不完全由客觀現實決定,如何認識客觀現實會產生更加重大的影響。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國內制度并不存在由國際結構所決定的發展方向,其始終是作為整體的國內政治精英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