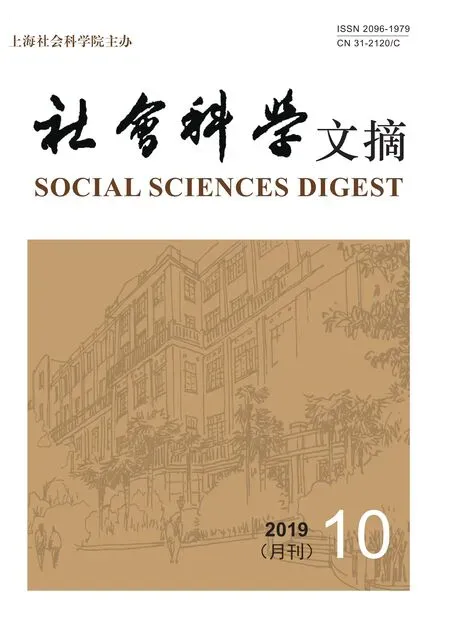邏輯能解法律論證之困嗎?
文/王洪
舒國瀅教授在《邏輯何以解法律論證之困?》中,基于約根森難題所揭示的經典邏輯在規范推理中遭遇的難題,提出了邏輯何以解法律論證之困的問題。他指出道義邏輯提供了一種新的邏輯手段和研究工具,并且指出法律規范適用的難題仍然需要建構出更為精致、實用的邏輯操作技術。接下來值得討論的問題是,道義邏輯能解法律論證之困嗎;進一步的問題是“更為精致、實用的邏輯操作技術”能解法律論證之困嗎;更為一般的問題是邏輯能解法律論證之困嗎。
約根森難題對邏輯提出的挑戰
丹麥邏輯學家約根森(J?rgensen)指出:“根據邏輯推理的一般定義,只有有真假的語句才能在一個推理中作假設或結論;然而事實是,一個祈使語態的結論可以由兩個假設得出,這兩個假設的其中一個是或兩個都是祈使語態的。”在真值邏輯中,對推理有效性作以下定義:一個推理是邏輯有效的,當且僅當不可能其前提為真而結論為假,即結論是前提的邏輯后承。而祈使句沒有真假,因此包含祈使句的推理不能被視為邏輯推理,因而無邏輯有效性可言,但事實上存在包含祈使句為前提或結論的推理,在直覺上是被認為有效的。這兩方面構成了沖突,這就是所謂的約根森難題。
約根森難題可推廣到法律論證與推理之上。約根森難題有兩個假設:一是有真假的語句才能作為邏輯推理中的前提與結論;二是祈使句沒有真假。法律論證是包含規范命題為前提或結論的推理,許多法律論證與規范推理在直覺上被承認是有效的,應該有相應的邏輯評價它們的有效性。但對于該類論證與推理,約根森難題指出無法從邏輯上作出評價,無法從邏輯上判斷其正確與否。約根森難題對規范推理構成了挑戰,對法律可推導性與判決可論證性構成了挑戰。
約根森與瓦爾特通過說明規范語句可以有真假而承認規范語句作為邏輯推理前提的合法性,以此消解約根森難題,此方案稱為真值語義學解決方案。約根森區分祈使句的祈使因素與指示因素,指出前者描述說話者的意愿與愿望,因而沒有邏輯后承,后者可以表達為指示性語句,因而有真假并能夠被一般邏輯規則所支配。瓦爾特將規范與規范語句區別開來,指出規范語句對應于規范世界,規范語句描述規范世界中的各種規范、規則和道義。規范沒有真假,但規范語句不是規范本身,規范語句可以為真,規范語句的真取決于與規范世界中的規范的符合。他指出:“如果將規范三段論的前提視作可以為真的句子,約根森關于邏輯應用的異議也就不再重要了。”
上述這種方案并沒有完全解決約根森難題。首先,上述方案沒有能夠完全解決規范語句可以為真的問題。正如魏因貝格爾指出:由于現實世界中的事實一致性,因而可以為事實語句確立真的標準。但規范世界中的規范并不具有如此一致性,因此,規范世界不能為規范語句確立真的標準,規范語句也就因此而不能被斷定為可以為真。其次,按照上述方案,規范之間不存在邏輯推理,就不能解釋法律規范基于推導的生成或衍生的現實。正如麥考密克所言:“在規范的領域內,有這樣一些邏輯的關系和聯系,借助于正式的規則可以使它們具有決定作用。如果規范被當作前提時是有效的話,那么規范的可以從邏輯上推導出來的后果也總是有效的。”再次,上述方案沒有觸及約根森難題的根本。盡管此方案強調規范語句與事實語句一樣可以有真值,但這兩種“真”其實是語詞相同但意謂完全不同,因此,僅僅說規范語句與事實語句一樣也可以有真值,并不能回答規范三段論為何是邏輯推理,不能解答“因現實世界中的事實而為真”的事實語句與“因規范世界中的規范而為真”的規范語句之間的推理為何是邏輯的。
因此,將司法三段論概括為亞里士多德三段論或一階謂詞邏輯推理就面臨約根森難題。國內外學界認識到,經典邏輯不足以刻畫法律論證與推理。一些學者建立了道義邏輯系統,馮·萊特和安德森的道義邏輯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應當指出,馮·萊特和安德森以及其后的道義邏輯系統存在著重大缺陷:一是上述系統建立在廣義模態邏輯理論之上,建立在基于真值的可能世界語義學之上,仍面臨約根森難題;二是其邏輯語言是貧乏的,缺乏對規范三段論的表達與刻畫;三是對規范算子的某些邏輯刻畫并不適用于法律規范詞,某些推理規則與法律規范推理相抵觸。
阿爾喬隆和馬爾蒂諾主張放棄真值語義學方案,甚至放棄語義學概念,尋求從邏輯的語法層面解答約根森難題。他們認為,規范沒有真假但有邏輯,從假設后承而不從真值概念或語義概念出發可以說明規范推理的邏輯性或有效性。主張邏輯無需真概念,主張“沒有真值的邏輯”(Logic without Truth),甚至主張邏輯推理不依賴語義。應當指出,這種放棄語義概念的方案擴大了邏輯的范圍,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消解約根森難題。僅對推理系統進行構造并不能使邏輯后承完全擺脫語義學概念。構造與刻畫邏輯推理不但要訴諸于語法層面的假設后承或邏輯后承概念,還需要其語義層面的解釋。正如達米特所言,任何一個邏輯系統未必需要真值語義學,但一定需要語義學,即一個正確性或合理性的評價系統。
弗雷格指出邏輯本質是追求真。真值語義學刻畫的是事實語句的推理有效性,而規范語句與事實語句有明顯的區別,因此,用真值語義學來刻畫規范推理的有效性,就必然面對約根森難題。問題并未就此終了,正如金岳霖所指出的:“事實上雖有不同的邏輯系統,理論上沒有不同的邏輯。”約根森難題實際上在問邏輯之義是什么。約根森難題實際上也揭示了經典邏輯不能充分表達基于內涵推理與語用推理的復雜的法律論證與推理。邏輯是對有效推理規則的研究,如何回答好約根森難題以及由此引發的問題是邏輯的重要任務與使命。
邏輯難解涵攝與例推難題
基于制定法的法律論證存在涵攝難題。事實涵攝(subsumption)是對個案事實是否符合法律中的構成要件作出裁決。事實涵攝不是概念的分析與推演,而是對事實的法律評判。正如拉倫茨所指出的:“作為法律適用基礎的涵攝推論,并不是將外延較窄的概念涵攝于較寬的概念之下,毋寧是將事實涵攝于法律描述的構成要件之下。”涵攝不是尋求概念與概念之間的包含關系,而是尋求事實與概念、事實與規范之間的對應關系,是“法律與事實間的目光流轉”,是在事實和規范之間的“等置”。事實涵攝包含價值評價與利益權衡。盡管法律設定了評價標準與尺度,但法官有可能對當事人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斷,有可能對事實的重要性程度及法律意義作出不同的評判,對案件作出不同的歸類與裁決,且其孰是孰非有時難以判斷與評價。因此,盡管有統一的制定法,但并不能確保事實涵攝的同一性或一致性。
基于判例法的法律論證存在例推難題。在司法中,有時面臨多個先例,相互爭奪對當前案件的支配力,需要法官進行區別性判斷(distinguishing),判斷本案與先例是否存在區別,以決定遵循先例還是區別先例。沒有兩個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當前案件是遵循先例還是區別先例,是由法官判斷當前案件與先例之間的相同點與不同點在法律上何者更為重要而決定的,法官有可能對當前案件與先例的相同點或不同點的重要性程度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斷,從而作出完全不同的例推與裁決。因此,盡管確立了遵循先例原則,但并不能確保例推或類推的一致性,且其孰是孰非也難以判斷與評價。
應當指出,涵攝難題與例推難題是法律論證的小前提證立難題。金岳霖指出:“積極地說,邏輯就是‘必然’;消極地說,它是取消矛盾。”但邏輯只解決名與名之間、概念與概念之間的一致性問題。涵攝是名與實之間、概念與事實之間、事實與規范之間的一致性問題;例推是個案與先例之間、個案事實與先例規則之間的一致性問題。邏輯不能解決“名與實”與“實與實”一致性問題,不能提供名與實、實與實之間的一致性判斷標準,不能解決案件事實與法定構成要件之間的一致性爭議問題,也不能解決個案與先例之間的一致性爭議問題,因而不能解決涵攝難題與例推難題。
邏輯不能解德沃金唯一正解難題
在司法中,人們爭論的問題之一就是法律問題有沒有唯一正確答案。美國法學家德沃金指出,由于有“整全性的法”存在,即使是疑難案件,也有“唯一正確的答案”(single right answer)。這一答案或者從法律規則中獲得或者從法律原則中獲得。即使在疑難案件中,法官也不應訴諸自由裁量權而應在作為整全性的法律框架之中,通過建構性闡釋(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以尋求唯一正解,這就是德沃金唯一正解問題。
在司法中,法官在解釋法律與適用法律上會有意見分歧或爭議。法官們有可能確立完全不同的權威性大前提作為裁決理由;有可能對法律概念作出不同的解釋,對法律含義或意思及文字所蘊含的“事物本然之理”作不同的探尋;或者在法律未作規定或者可以這樣決定也可以那樣決定時,各自運用自由裁量來填補法律空白或漏洞;或者只考慮一般規則而不考慮其例外情形,以此為裁判理由作出不同的裁決。因此,即使有統一的制定法也不足以確保釋法與裁決的一致性即法制的統一性。在普通法系國家,遵循先例原則也不能完全確保裁決的一致性即法制的統一性。因為法官們有可能識別和適用完全不同的權威性先例,并以此作出不同的裁決。
法官承擔依法裁判義務和公平與公正裁判義務,但實在法是開放的、非協調的、不完全的,不可能為每個具體案件都準備好現成答案。在審判案件中法官受制定法的約束,但法官對制定法具有廣泛的解釋權與酌處權。法官承擔著這樣的職責:澄清法律疑義、平衡法律沖突與填補法律空白。法官有權確定法律是什么,他們是“活著的法律宣示者”。在英美法的判例制度中,盡管在審判案件中法官受先例的約束,但法官在決定是否遵循先例方面具有廣泛的酌處權,有權決定何時遵循先例、區別先例、創制先例與推翻先例。法官有權從先例中抽象出基本的原則即判決理由,并且有權確定這些原則將要運行和發展的路徑或方向。因此,盡管實在法與公平正義原則有助于構成司法評價主觀自由游動的障礙,但最終也無法阻止法官個人的自由裁量,因為它們也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對象,存在著發生意見分歧與爭議的可能。
有分歧與爭議不等于不存在正確答案。但沒有正確答案的標準,就談不上有正確答案,更談不上有唯一正確答案。因此,唯一正解的問題就是唯一正解的標準問題。唯一正解理論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是否存在唯一正確標準?應當指出,唯一正解的標準是可爭議的,因此,唯一正解是可爭議的。這些司法裁決可以放在正義的天秤上進行衡量,但這些衡量標準進一步面臨著進一步的正義選擇與爭議。在通常情形下法律的正義之路是沒有沖突的,但有時這些正義之路分岔了,有的正義之路通向這樣一個正義,有的正義之路通向另一個正義,在這些正義追求之間就必須作出選擇。但亞里士多德指出:“由于不存在使結論具有必然性的無可辯駁的‘基本原則’,所以通常我們所能做的就只是通過提出似乎是有道理的、有說服力的、合理的論據去探索真理。”應當指出,德沃金唯一正解難題是法律論證的大前提證立難題。邏輯提出了法官釋法與裁決的內在一致性要求,但未能提供解決其沖突的選擇與平衡標準,因而不能消除法官意見分歧與爭議,不能終結其唯一正解難題。
邏輯難解法律論證終極之困
在法律論證中,面臨阿爾伯特所說的“明希豪森的三重困境”。德國法學家阿爾伯特指出,任何命題都可能遇到“為什么”之無窮追問的挑戰。正如亞里士多德指出:要求對一切命題都加以證明,就必然產生兩種情況,其一陷入無窮后退,其二陷入循環論證,無窮后退和循環論證都不是證明。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某個主觀選擇的節點上終止論證。這三種情況被阿爾伯特稱為“明希豪森的三重困境”。
在司法中,對判決理由進行證立是必要和必需的,是法律論證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法律論證的關鍵。司法裁決的最終走向取決于對這些裁判前提或理由的確立與選擇。法律獲取或理由確立是可爭議的,在疑難案件中涉及選擇時更是如此,要避免公眾合理的懷疑就必須對有爭議的前提或理由進行證立。圖爾敏認識到了對判決的爭議不但來自對推論的爭議而且來自對前提的爭議。他在《論證的使用》中指出,不但結論需要證立而且前提受到質疑時也要予以證立。尋找正確答案是擺在每一個裁判者面前的迫切任務。人們普遍地認為,不可能通過無窮后退或循環論證的方式來尋找正確的答案,也不能因為無法找到絕對正確的答案,而把裁決交給法官無根據的專斷或無理由的武斷。法官作出的裁判及其理由能夠回溯到實在法規則與原則上,外部證立鏈條最后能終止于既有法律之內,這是司法判決追求的目標,也是判決證立的一個標準。應當指出,雖然制定法存在開放性結構,但制定法原則與精神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與指引著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要盡力從法律上回答所有的法律問題。但制定法并沒有為具體案件提供現成答案,如何證明判決理由是成立的,最終在何處結束裁決論證的鏈條,是需要法官在具體案件中解決的。因此,法律論證本質上屬于實踐推理的范疇。佩雷爾曼強調證立或說服的標準是“普遍聽眾”的認同;德國學者阿列克西強調法律論證的正確性是因為它能夠在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內被證立是符合理性的;瑞典學者佩策尼克提出了法律論證的“深度證立”(deep justification)和“審慎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標準與要求。
如何走出明希豪森困境是法律論證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明希豪森困境是判決理由的可證立性難題,因而是判決的可證立性難題,也是法律論證的終極之困。在司法裁判中,判決證立最終是對判決理由或前提的證立。應當指出,邏輯難解法律論證的明希豪森困境。邏輯可以用于法律論證與推導,是論證與推導的工具,但它對其前提與理由卻無法作出選擇,不能提供前提或理由的選擇與評價標準,因而不能消除關于前提或理由的分歧與爭議,不能終結對前提證立的追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霍姆斯在《普通法》中開篇說道:“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對時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論,對公共政策的直覺,不管你承認與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見對人們決定是否遵守規則所起的作用都遠遠大于邏輯三段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