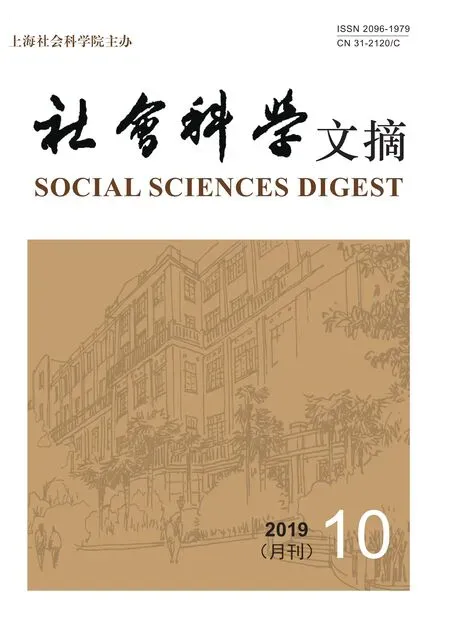如何研究新技術對法律制度提出的問題?
——以研究人工智能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影響為例
文/王遷
任何法律都是基于現實需要而制定的,而任何現實中的問題都有其產生的土壤,其中技術的發展情況尤為重要。如果新技術催生了新的行為方式,改變了社會關系和利益格局,原有法律制度中的部分內容就可能過時,此時研究如何調整現行法律制度,就具有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目前,有可能對現行法律制度造成重大沖擊的新技術莫過于人工智能,它一方面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帶來社會建設的新機遇,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在此背景之下,人工智能對現行法律制度帶來了何種挑戰,以及如何通過修改和完善相應的法律規則予以回應,自然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只是我們應當認識到,不同技術對不同領域法律制度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不同法律規范對新技術的適應程度也有所區別。
新技術對法律制度的不同影響與不同研究方法
法律當然需要順應社會的現實需要,但同時法律也要保持自身的穩定性。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不僅涉及立法理念,更與立法技術有關。法律中有些用語或規范有其特定的技術背景,專門針對與特定技術有關的行為方式。當相關技術改變之后,原有用語和規范如果保持不變,很難再有用武之地。但也有大量的用語或規范雖然也與當時的特定技術有關,但具有相當的包容性,可以直接或經過合理解釋之后適用于新技術帶來的新的行為方式。此時并不需要改變原有用語或增加新的法律規范,至多需要在司法實踐中由法院根據法律解釋方法對現行法作出合理解釋。這兩種情況,在以保護創新成果為已任的知識產權法中體現的特別明顯。
(一)新技術帶來了新問題
1998年通過的美國《版權法》的修正案《千禧年數字版權法》(簡稱“DMCA”)為了防止電視節目中的作品被未經許可復制,規定VHS錄像機等模擬錄制設備必須采用與“自動復制控制技術”或“彩條復制控制技術”相兼容的標準。作品的權利人可以利用這兩種技術控制電視節目的錄制。可以想見,今后數字攝錄設備將完全替代模擬攝錄設備,這兩種特定技術也可能完全過時。同時,適用于數字攝錄設備的新技術也將出現。此時,研究如何修改法律,使之適應新技術的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即使一部法律沒有像DMCA那樣提及如此具體的技術,上述研究的必要性也可能存在。例如,20世紀90年代迎來了如何在網絡環境中保護著作權人利益的新問題。通過互聯網可以實現一種全新的傳播模式——交互式傳播,也就是將作品以上傳等方式置于服務器中,在服務器開放的時間與地域范圍內,供用戶自行選擇時間和地點進行點播或下載。這種傳播模式不同于以往電臺、電視臺通過無線或有線方式進行的傳播,以往公眾只能根據既定的節目時間表收聽或收看的情況。《伯爾尼公約》和各國著作權法中當時并沒有一項權利能夠規制對各類作品的交互式傳播。因為“廣播權”只能控制傳統的無線或有線傳播,也就是非交互式傳播。《伯爾尼公約》在為音樂作品、戲劇作品和文學作品的作者規定表演權和朗誦權時,雖然使用了“授權以任何手段向公眾傳播對其作品(的表演或朗誦)”這樣具有技術中立性質的用語,因而可以將交互式傳播納入“以任何手段向公眾傳播”的范圍之內,但它畢竟只限于傳播對作品的表演或朗誦,而不能及于傳播作品本身。因此,在當時研究《伯爾尼公約》和各國著作權法的不足,討論締結新的國際條約和修改各國著作權法,以使對作品的交互式傳播能受到國際條約和各國著作權法的調整,是非常有意義的。
(二)新技術沒有帶來新問題
在另一種情況下,新技術帶來的新的行為方式可以被現行法所包容,并沒有帶來需要解決的新問題。3D打印技術就是典型實例。人們可以將物品的平面圖紙制作成數據文件輸入3D打印機,再“打印”(即制造)出一個與之相對應的物品。雖然3D打印是全新的技術,但它實現的是對造型從平面到立體的再現,而著作權法的理論、規范和實踐早已對此進行了清晰的界定:如果圖形描繪的造型是卡通形象等美術作品,則根據平面圖形制造立體物品,屬于從平面到立體的復制,未經許可實施就可能侵犯復制權;如果圖形描繪的造型是不構成美術作品的工程或工業品的外觀,則根據平面圖(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制造立體物并不構成從平面到立體的復制,不可能侵犯復制權。只有以復印等方式對該設計圖進行平面到平面的復制才有可能構成侵權。3D打印雖然是新出現的技術,但它只是用“新”技術實施了“老”行為,行為的定性并沒有因此發生任何改變。因此3D打印沒有像互聯網那樣,引發現行著作權法尚無法解決的問題。對于此類情形,只需要澄清這些“問題”在現行著作權法中已有相應的規則即可。
有時新技術雖然沒有引發全新的法律問題,但也可能使原本就存在的爭議更加突出。例如,隨著互聯網網速的提高,許多用戶大量下載未經許可傳播的電影和音樂等作品。那么為個人欣賞而大量下載盜版應當被認定為侵權(侵犯復制權)還是合理使用?應當說,這并非新的法律問題。因為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個人已經可以利用復印機、掃描儀等設備大量復制作品了。是一概將以個人欣賞為目的而未經許可實施的此類行為都定為合理使用,還是在范圍上作出適當限制,是原本就存在的問題。但下載的便利性和低成本使這一問題更具現實性。此時研究該問題,實際上是以互聯網為引子,以大量下載盜版可能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來說明及早解決“老”問題的必要性。
(三)人工智能帶來的新問題與凸顯的老問題
人工智能作為“影響面廣的顛覆性技術”在某些領域引發了新問題,在其他領域則只是使原有爭議更加凸顯,但并未帶來新的問題。
目前,人工智能帶來的新問題之一,在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是否可被認定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即是否具有“可版權性”)。現在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到了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獨立生成內容的階段,且某些內容在表現形式上已與公認的作品幾無差異。如果相同的內容源于人,則其當然可以被認定為作品。但如今這些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能否被現行著作權法中“作品”的定義所包容,特別是其是否符合獨創性的要求,是人工智能為著作權法帶來的新問題。如果認為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并不屬于現行著作權法所規定的作品,那么著作權法是否應當為此進行修改?在實務中甚至已經發生了有關著作權法能否保護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爭議。由此可見,對該問題的研究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但人工智能在另一些領域只是凸顯了原本就存在問題。例如,人工智能提高了數據的收集和處理能力,且在信息時代客觀上存在對個人信息進行收集和共享的需要,這就可能與個人隱私保護產生沖突。但該沖突并不是人工智能帶來的,而是因人工智能而凸顯。在進入網絡時代之后,收集與個人信息有關的數據的渠道被大大拓寬,便利度大大提高,共享的范疇大大增加,與個人隱私保護的沖突也變得更加激烈。歐盟在上20世紀90年代已經有了相應的立法對策,而當時人工智能尚未得到充分的發展。人工智能只是收集和處理包括個人信息在內的各類數據的手段,它并沒有改變個人信息的收集、共享與個人隱私保護之間沖突的本質。之前已經存在的相關立法依然可以適用。當然,在該領域還沒有成熟立法的我國,以人工智能凸顯個人隱私保護問題為引子進行研究是有意義的。但嚴格地說,除非能夠發現人工智能對個人隱私保護帶來的全新問題,相關研究的主題實際上并不是“人工智能法律問題”。
與隱私保護問題類似的是,算法作為人工智能的基礎能否成為專利保護的客體(即是否具有“可專利性”)。但這并不是人工智能對專利制度帶來的挑戰。根據我國《專利法》的規定,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不能被授予專利權,因為它們沒有采用技術手段和自然規律,也未解決技術問題和產生技術效果,不構成專利法意義上的技術方案。算法本質上屬于演繹、推理和運籌的方法,屬于典型的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不能被授予專利權。至于對專利法的這一規定是否需要修改,是否需要將算法剔除出不能授予專利權的客體范圍,當然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但該問題在人工智能發展起來之前就已出現,并不屬于人工智能帶來的新問題。
新技術引發的問題真實存在是研究的前提
技術的進步永遠不會有盡頭,未來出現的諸多新技術當然可能帶來一系列之前人們難以想象的問題。然而,法學研究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即使是前瞻性的研究,也需要建立在技術發展的現實可能性基礎之上。否則,法學研究就可能脫離實際,成為空中樓閣。
目前,在就人工智能引發的知識產權問題中,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可版權性問題具有研究價值。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已經可以在預設的算法與程序的框架下,獨立生成在形式上與人類創作出作品幾無差異的內容。該內容是否可以根據現行著作權法的規定及基本原理被認定為作品,以及是否需要修改現行著作權法使之成為作品或其他受保護的客體,是真實存在的問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人工智能“發明創造”的可專利性問題。展開討論的前提,是人工智能可以獨立生成在形式上符合專利授權實質條件的技術方案。如果該前提并不存在,則圍繞人工智能發明創造可專利性的討論就喪失了意義。
不少有關人工智能發明創造可專利性的研究都提及:目前人工智能的發展僅處于弱人工智能階段,僅能對人類的發明創造起到輔助作用,也就是只能作為人類進行發明創造的工具與手段。既然只是“工具”,無論其計算能力和數據處理能力多么強大,都不可能主動提出新的技術方案,也不可能對只承認人類的發明創造才能獲得專利權的制度造成沖擊。
有研究則將人工智能不再僅為輔助手段,而是可以獨立提出技術方案作為提出相關觀點的基礎。這實際上是在討論強人工智能對專利制度的挑戰了。在強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可以像人類一樣獨立地進行思考并提出技術方案,由此產生的對現行專利制度的沖擊自不待言。
然而問題在于,這種在思想與智慧方面與人類別無二致的強人工智能是會在今后可預期的一段時間內出現的事物么?人工智能從“弱”至“強”絕非一步之遙,而是一種用任何形容詞都難以描述其程度的飛躍。
無論上述強人工智能時代是否真的會到來,在那個時代將要發生之事似并不應當成為法學研究的對象。法學研究者要立足當下,在沒有證據表明人工智能可以獨立思考、自主進行發明創造的情況下,以人工智能飛躍到了可以獨立提出技術方案為假設的前提,討論由此產生的發明創造的可專利性,似為時尚早。
即使強人工智能時代終將到來,那時所謂人工智能發明創造的可專利性,與其他足以撼動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根基的那些問題相比,大概也不值一提了。甚至到時連專利制度都恐不復存在。這是因為強人工智能“不再被人類所支配”,同時又有自主創新能力,且可以突破工作時間、知識儲備、認識偏見和計算錯誤等人類生理與心理的天然限制,其自然會隨“心”所“欲”地進行無窮無盡的創新,且質量將遠超人類的發明創造。由此,人工智能將成為人類“最后的發明”。
可見,以強人工智能的出現作為討論人工智能挑戰專利制度問題的基礎,以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意識、獨立從事發明創造的能力作為研究可專利性問題的起點,似缺乏現實意義。
科學證據是研究的基礎
新技術帶來的新問題當然值得研究,但這些問題的真實存在需要得到證實。目前,在討論人工智能引發的知識產權問題時,對于“人工智能可獨立生成表面上與作品無異的內容”已無爭議。此時討論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該內容是否可構成作品,無論結論如何,都是有意義的。然而,在討論“人工智能發明創造的可專利性”時,部分研究雖然引用了人工智能可獨立完成發明創造的資料,而不是僅以對未來強人工智能的誕生作為研究的基礎,但這些資料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值得質疑。
例如,一篇研究人工智能對專利法的影響的英文論文引用了一些“自20世紀以來計算機一直在獨立地進行發明創造”的例證。第一個實例是計算機科學家Stephen Thaler博士于1994年發明了“創造力機器”,并就該機器申請并獲得了專利權,發明名稱為“自動生成有用信息的設備”。此后Thaler博士又就一種神經網絡獲得了專利權,但他聲稱該發明是由“創造力機器”完成的。
第二個實例是計算機科學家John Koza博士研發的“發明機器”。一篇發表在科普期刊《大眾科學》(Popular Science)的文章稱該“‘發明機器’研發的使工廠更有效率的系統甚至獲得了美國專利”,只是Koza博士在申請時沒有披露該發明是由“發明機器”在沒有人工干預的情況下一次完成的事實。
然而,“創造力機器”是一種“自動生成有用信息的設備”。信息本身不可能成為專利法保護的客體。基于對大量原始數據所進行的精密計算所獲得的信息當然可以成為構建神經網絡的基礎,但生成信息與發明神經網絡之間還有很長的距離。而報道Koza博士的“發明機器”獨立完成發明創造的文章屬于深度新聞報道,且刊登于科普期刊。科研人員對“發明”的理解,與專利法中對可獲得專利權的發明的界定,有時并不一致。兩位博士稱有關其獲得專利的發明創造由智能機器完成,其真實性令人生疑。且這兩項發明創造獲得專利的時間分別為1998年和2005年,自那時至該篇英文論文發表的這段時間內,人工智能的發展突飛猛進,為什么再沒有出現可供法學研究者引用的、在主流科學期刊上發表的智能機器完成更為先進的發明創造的實例?
該篇英文論文引用的第三個實例,是IBM公司名為“Watson”的人工智能系統,其能夠根據用戶的需求而生成新菜譜,使食品具有不同配方和風味。菜譜本身并不構成技術方案,換言之,它并未針對技術問題,利用技術手段并取得技術效果。即使是由人類“發明”的新菜譜,也不具有可專利性。
以筆者淺見,如果人工智能確實可以在沒有科研人員事先設計和事后處理的情況下,自主地提出一項在形式上完全符合專利授權實質條件的技術方案,將是技術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在經過同行驗證為真之后,再研究人工智能的發明創造對專利制度的影響也為時不晚。
總而言之,新技術的產生總會使人們產生現行法律制度需要變革的直觀感受。但究竟是否由此產生了值得研究的真實問題,本身就需要仔細甄別。有些新技術并未帶來現行法無法解決的問題,或者只是凸顯了早已存在的問題。有些新技術在今后的發展狀況難以預測,與其以不可知的未來作為研究基礎,不如立足當下,力求解決更為實際和緊迫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