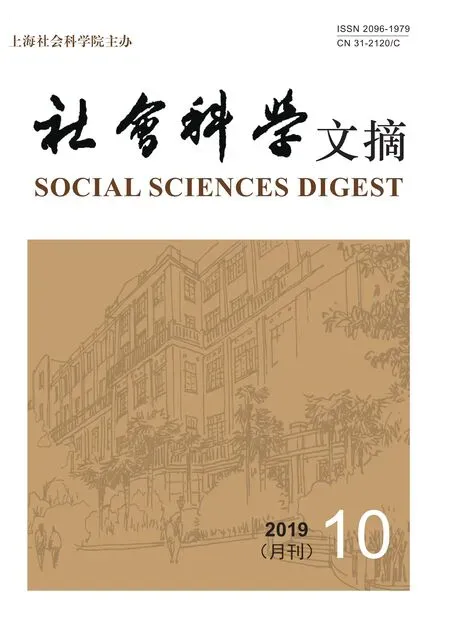“知識產權制度”的哲學反思
文/李石
一種能夠救命的新藥被發明出來,價格卻無比昂貴,搞得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患者們傾家蕩產;一種能大大提高生產效率的新技術被發明出來,而亟需這種技術的生產者卻沒有錢付專利費,延誤了生產力的發展;一首非常優美的歌曲被創作出來,但是,沒有錢買CD、也沒有錢進音樂廳的貧困者卻無緣欣賞到它……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保護創新與普及應用之間的矛盾比比皆是。萌芽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發展于17世紀的英國、20世紀之后被世界各國廣泛接受的知識產權制度,一方面,保護了創新者從自己的作品中獲得足夠的利益,激勵了知識“創新”;但另一方面,卻妨礙了新知識、新藥品、新技術、新作品的迅速傳播。“激勵創新”與“普及應用”之間的矛盾關系,使得人類最新的知識很難得到最高效的應用。
“知識產權制度”是智力成果所有人在一定的期限內依法對其智力成果享有獨占權,并受到保護的法律制度。廣義的知識產權,涵蓋一切人類智力創作成果。1967年成立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中列舉了創作者對于文學、藝術、表演、發明、科學發現、外觀設計、商標等智力成果的各項專屬權利。另外,1994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也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中為知識產權劃定了范圍,包括:版權、領接權、商標權、地理標志權、工業品外觀設計權、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拓撲圖)權、未披露過的信息專有權,等等。不可否認,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及發展對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文明進步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廣泛應用也顯現出越來越多的弊端。本文將從“私有權的解釋困難”、“激勵機制的囚徒困境”、創新活動之“價值與意義的錯位”三個方面深入分析知識產權制度的理論問題,并在這一基礎上,嘗試提出知識產權制度的替代方案——保護創新的“基金激勵機制”。
私有權的解釋困難
知識產權制度的理論基礎是自由主義思想中的私有權理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對私有權的論證根源于“自然權利論”。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基礎上提出了私有權的“勞動獲取理論”。該理論得到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重要經濟學家的認同,成為對私有權的經典論證。
洛克認為,勞動在人們對外在物品的獲取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人們為什么可以通過勞動而使某物歸自己所有,洛克給出了兩個論證:第一個論證是,一個人通過勞動將某物從自然中取出來,在其中摻入了屬于自己的東西,由此確立了此人對此物的專屬權利,這是“勞動摻入說”。第二個論證是,人們的勞動改善了勞動對象,“使一切東西具有不同的價值”,由此確立了人對其勞動成果的專屬權利,這是“勞動價值論”。總之,洛克認為人們的勞動不僅創造了新的價值,還在其勞動對象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因此勞動者有資格獲取其勞動成果并對其享有專屬權利。
支持知識產權制度的學者認為,私有權的“勞動獲取論證”同樣適用于人們的智力勞動及其勞動成果。人們的智力勞動創造了智力勞動成果。在這一過程中,智力勞動不僅創造了新的價值,為人類社會帶來福利,而且也在勞動成果上打上了勞動者的烙印。所以,付出智力勞動的勞動者理應對其勞動成果享有專屬權利。私有權制度強調勞動者對其勞動成果的獨占性,并對勞動者的專屬權利進行法律保護;而知識產權制度則強調智力勞動者對其智力成果的獨占性,對智力勞動者的專屬權利進行保護。
上述平行推導并沒有邏輯問題,知識產權以及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有權理論的延伸和合理應用。然而,這一推導卻掩蓋了傳統私有權理論與知識產權理論之間的一些重要差別。下面我將從“私有權的限制條款”和“公地悲劇”兩條線索切入,揭示智力成果的“非排他性”,以及從傳統私有權理論推導出知識產權理論的不合理之處。
洛克提出私有權的勞動起源論時還提出了私有權的兩個限制條款。第一,人們通過勞動獲取時,要將同樣好和足夠多的土地及其產出留給他人耕種和享用。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盡量多地去占有,但必須留有足夠的土地及產品給其他人享用。第二,通過勞動,一個人只可以占有其有能力耕種的土地和可供利用的產品。也就是說,一個人能耕種多少土地就只能占有多少土地,能享用多少產品就只能占有多少產品,其占有不能超出自己可以利用的范圍。洛克認為,在貨幣產生之后人們便開始想要無限制地擴大自己的財富,因為貨幣并不會腐爛;與此同時,勞動獲取的第二條限制條款就失效了,而對私有權的限制就只剩下第一條限制條款。
洛克之所以要為人們的勞動獲取劃定界限,是因為對于有形的(physical)資源來說,其獲取和享用具有嚴格的排他性。例如,對于一片土地來說,一個人占有,則另一個人就不可能同時占有。然而,智力勞動成果卻不具有這種嚴格的排他性。一本書,一個人占有,另一個人可以通過復印、拷貝等多種方式同時占有。尤其是在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代,多人同時占有同一智力成果的成本極低;而且常常是“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新知識的分享還能促進人們的交流和討論,帶來知識的進一步增長。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知識產權并不像傳統意義上的私有權那樣是必不可少的。對于具有排他性的有形資產,如果不確立人們的專屬權利,就會使社會陷入你爭我搶的爭斗之中,甚至退回到自相殘殺的自然狀態。相反,如果不確立智力成果的專屬權利,也許會降低人們從事創新活動的積極性,但是并不會使人們因權利范圍不明確而陷入紛爭。
在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公地悲劇”通常被用來論證私有權的必要性。1968年英國經濟學家加勒特·哈丁(Garett Hardin)首次闡述了“公地悲劇”的思想。哈丁假設:有一片人們共有的牧場,為了增加收入,每一個牧民都盡量增加自己飼養的羊的數量,最終導致牧場上的草被羊吃光。“公地悲劇”向人們展示了這樣的囚徒困境:每個人出于理性,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但最終公共資源被耗盡,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損害。如果“公地悲劇”是真實存在的,那么,專屬權利的確立就是必須的。然而,對于知識產權來說,由于智識成果的“非排他性”,這種“公地悲劇”卻并不存在。
與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不同,知識生產的原材料不具有“獨占性”。尤其是對于文化創新來說,人們從事文學創作、音樂創作、繪畫創作,除了維持創作者所需的生活資料以及繪畫的顏料等基本條件外,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購買“原材料”。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類社會在千百年間積累起來的大量精神文明成果為創作者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可以說,在某種文化背景的人類社會中,所有人共同擁有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識公有物”(intellectual commons)。人們對于這種“智識公有物”的共同占有,不僅不會帶來“悲劇”,反而會帶來更多思想的碰撞,通過交流和辯論激發靈感,創造出新的“智識公有物”。與此同時,任何人也不可能獨自占有這些歷經千年而沉淀下來的“智識公有物”,無法對其形成專屬權利。“智識公有物”是屬于整個民族,甚至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智識成果的“非排他性”揭示了從私有權理論推導出知識產權理論的不合理之處,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洛克“勞動獲取理論”對于智力勞動成果的有效性。我們可以這樣來分析這個問題——人們在通過腦力勞動創造出智識成果的過程中,有三個因素最終促成了其成果的價值:第一,創作者的自然才能;第二,創作所需的“原材料”;第三,創作者的智力勞動。
對于第一個因素,“創作者的自然才能”,如果我們同意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觀點,則可認為“自然才能”并非屬于創作者專有的財產,而是全人類的共有財產。對于第二個因素,創新活動所需的“原材料”往往是屬于公共資源的各種文獻資料,尤其是對于文化創新來說,在公共領域存在著大量的“智識公有物”,創作者在“智識公有物”的基礎上進行創作。對于許多創新活動來說,創作的“原材料”都不是創作者自己的私有財產,或者不完全是。對于第三個因素——智力勞動,如果我們贊同洛克的觀點:“我的身體所從事的勞動和雙手所進行的工作正當地屬于我的”,那么,可以將“智力勞動”看作是確定屬于創作者的。由此,在上述構成最終的智識成果的三個因素——人的自然才能、原材料、創新性勞動——之中,僅有一個因素確定無疑地屬于創作者自己。這樣就很難確定智力勞動者對其勞動成果的專屬權利。
支持自由經濟的學者通常認為,只有確立了人們對于其勞動成果的專屬權利,人們才可能加倍努力地創造財富。在每個人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時,社會的資源得到了最佳配置,社會整體的利益也實現了最大化。這對于其他社會資源的配置來說,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對于創新性的智識成果,自由市場理論卻不完全正確。因為,人們對智識成果的占有具有“非排他性”,“分享式”的占有不僅不會帶來人們爭權奪利的紛爭,還會增進交流、促進公共利益。因此,將傳統的私有權理論直接應用于具有“非排他性”的智識產品是不合理的。
激勵機制的囚徒困境
在理性選擇理論中,支持知識產權制度的論證被稱為“知識產權激勵說”。該學說的主要觀點是:如果不對人們所創造的智力成果進行權利保護,那么,人們就會失去創新的動力;而長此以往,整個社會的“公共福利”就會受損,以至于人類社會將停滯不前。中國學者楊明進一步指出了這種“激勵機制”的兩層含義:“知識產權制度的設置,蘊含了兩個層面的激勵,對人們投資于創新活動的激勵是第一層次的,對社會公共福利之增長的促進是第二層次的、也才是終極目標,前者可以被看作是后者的前提和手段,而后者是前者的集大成者。也許單個的市場主體并不在意、或許也并沒有意識到第二層次的激勵,但只要第一層次的激勵能夠吸引足夠多的市場主體做出行為選擇,最終必然也會促進社會知識財產的總量增長、從而推動社會進步。”
“知識產權激勵說”的論證邏輯類似于亞當·斯密以“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對自由市場進行的論證:在私有權得到保護的自由市場中,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利益,而在供需關系的調解下,卻能達到人力和資源的最佳配置,實現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以此類推,在知識產權制度的保護下,每位創新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從事創新活動,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推動了“社會利益最大化”。
然而,就像自由市場學說不可避免地要遭遇“經濟危機”的重創一樣,“知識產權制度”掩蓋了“個人激勵”與“社會發展”之間的深刻矛盾,在現實應用中經常漏洞百出。
“知識產權激勵說”的根本問題在于:在知識產權制度中,對“個人發展”和“公共福利”的雙重激勵是不可能同時實現的。因為,在專屬權利保護下,“個人利益”和“公共福利”二者從根本上來說是矛盾的。知識產權制度將人們從事創新活動的根本動力假設為“一己私利”,即使我們暫且贊同這一假設,也很難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推導出“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結論。因為,在知識產權制度的保護下,如果要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就必須以加大創新者的權利范圍、加長權利期限、加高專利轉讓的費用等手段增加人們獲取創新知識的難度,并借此使智識成果所有人獲取盡可能高的經濟回報。然而,給予創新者更大的經濟回報,雖然有可能激勵更多的人、投入更大的精力和時間從事創新工作,卻必然妨礙人們獲取和應用新知識,無助于“公共福利”的增進。所以,在知識產權制度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悖論,專利轉讓費用設得越高,人們購買專利的難度越大,專利擁有者越難獲利,最終使得專利所有人和公共利益都受損。
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機制中,一方面,創新知識被“保護”地越好,金錢“壁壘”越高,其傳播越慢,也就越不利于公共福利的增長;而另一方面,那些得到迅速傳播,并且大大推進公共福利增長的新知識,卻往往沒有得到很好地“保護”,使創新者利益受損。由此看來,在知識產權制度保護之下,創新者和社會的公共福利兩者并不總是“雙贏”,反而時時陷入“雙輸”的囚徒困境。
此外,知識產權制度將人們創新的動力假設為對“一己私利”的追求,也就是將人類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歸結為“私欲”,這必然導致人性中“惡”的因素膨脹,甚至會激發“報復”、“歧視”等“惡劣”的心理機制。這一點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有極為明顯的體現。例如,在美國的貿易法中就有關于“報復”的相關規定。美國國內貿易法中的超級301條款規定:美國將對認為對美實施不公平貿易做法的國家進行報復,其中不公平貿易做法包括美國認為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充分的做法。報復措施包括對進口商品提高關稅或采取進口限制,對有關國家服務征稅或進行限制,直至終止兩國簽訂的貿易條約。還有,美國國內貿易法中的超級337條款也有類似的報復性內容。這些規定完全丑化了人們做出創新的初衷,激化國際矛盾,是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的歧視和不尊重。還有一些專利技術擁有者憑借其專屬權利而與專利技術買方簽訂“不平等協議”:“對技術售方進行種種限制,如強制買方所指定的人購買原材料;對買方在制造、使用或出售與專利技術相競爭的產品或采用與專利技術相競爭的技術方面加以限制,或不合理地限定買房的銷售區域等。此種限制性商業條款會擾亂正常貿易秩序,使合理貿易受到限制。”另外,知識產權制度下的“惡意搶注商標”等行為,也是這一制度過分刺激人們的“私欲”而引發的惡果。2019年4月,“視覺中國”圖片網站在世界各國科學家聯合公布的“黑洞照片”圖片上打上自己網站的水印,并以此敲詐“侵權費”,甚至還將國旗、國徽的圖片都打上自己網站的水印。以如此卑劣的手段,借知識產權制度牟利,簡直是罪大惡極,引發天怒人怨。
價值與意義的錯位
“知識產權激勵說”的癥結在于其基本假設:人們為追求“一己私利”而創新。如果這一假設并沒有準確地描述人類的創新活動,那么人們到底為了什么而創新呢?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許多偉大的創舉都不是在對金錢的追逐中完成的,激勵人們不斷創新的根本動力往往不是“金錢”所代表的利益。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意大利科學家布魯諾,為堅持“日心說”而被教會活活燒死。對于布魯諾來說,他追求的是比生命還要崇高的價值,怎么可能是為了“金錢”?19世紀末,塞爾維亞裔美籍科學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主持設計了現代交流電系統,卻于晚年撕毀專利,將其公之于眾,而他自己卻死于貧困之中。激勵特斯拉不斷創新的動力也絕不會是“金錢”。美國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在《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和平等一辯》一書中提出了基于多元價值的正義理論。他認為,人類的社會合作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而且還創造了豐富的價值和意義。而每一種價值都有其內在的分配邏輯,并非都可以通過金錢而獲得。
“創新的目的和動力不是賺錢”,這個樸實無華的道理得到古今中外許多例子的印證。歷史上那些令人敬佩的創新者們的事跡不斷向人們表明,除了“金錢”之外,各行各業的從業者還有著讓他們全心投入、無怨無悔的價值追求。這些價值追求遠遠高于金錢所代表的“利益”,甚至是超越生命的。
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甚至無孔不入的今天,人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任何行業的終極追求都是“金錢”。或許,人們先是用這樣的邏輯去預設他人,接著自己也陷入這樣的假設之中,最終相應的激勵機制也由此而訂立。同時,制度與人的行為之間又形成相互加強的關系。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在這樣的邏輯預設下形成的激勵機制。這一制度通過刺激人們的“私欲”而促進“創新”,進而推動社會進步。這種激勵機制將各種創造性活動的內在意義和人們從事這一活動的動機割裂開來,造成一種人們為“金錢”而“創新”的假象。這將造成人的價值追求與內在動力的錯位,使人們迷失在對“金錢”的追逐中。
在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上,知識產權制度的癥結正在于將各行各業人們的終極價值追求假設為“金錢”,并以此推斷:如果做出創新的人得不到相應的,或者盡可能大的經濟回報,那么人們就會停止創新,社會就會止步不前。然而,這一假設和推理與事實并不完全相符。不論是在人類社會的實然層面,還是在道德應然層面,各行各業的從業者都有著高于“金錢”的價值追求,而金錢只是當這些價值追求得以實現時,社會給予人們的回報,并不是人們努力工作甚至做出創新的根本動機。換句話說,即使沒有金錢的刺激,在理想的狀態下,人們也會秉承自己的價值追求而做好本職工作,甚至做出創新。
當然,作為具有生物性需要以及各種社會需要的人,在市場經濟中必須借助“金錢”維持自己的生存、體面的生活以及自尊和榮譽。那么,我們應如何處理“金錢”、“創新”以及創新活動的“內在價值追求”三者之間的關系呢?有沒有“知識產權制度”的替代方案呢?
基金激勵機制的提出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了一種區別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激勵機制——“基金激勵機制”,其核心思想是:在某一行業中通過基金獎勵的方式促進創新;同時,該基金會與創新者簽約,將創新知識免費或者以很低價格向公眾開放。“基金激勵制度”的基本構想有五個方面。1.在某行業內,通過稅收和募捐形成該行業的“創新基金”以及基金管理組織“創新基金會”。2.邀請該行業的資深專家組成“創新學術委員會”。3.創新者以自己的作品向該“創新學術委員會”申請認證。認證成功后,創新者將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并被授予相應的榮譽。4.創新者與“創新基金會”簽訂合約,將該作品免費向公眾公布,創新者僅保留署名權。5.該行業的相關運營公司(例如,歌曲創新行業的唱片公司、醫藥創新行業的制藥廠、等等)通過對創新產品的批量化生產而獲得利潤,并上繳稅收,以支持“創新基金會”的運行。
從2003年開始,在藥品的研發和推廣領域,世界各國的知識精英和政界精英一直在推廣一個替代“藥品專利”的“基金激勵”計劃。這一計劃名為“健康影響基金”(Health Impact Fund),是一個國際范圍的新藥發明支持計劃。新藥發明者可以向該基金會申請發明新藥的經濟回報,同時放棄申請專利。“基金激勵機制”不僅可以應用在醫藥創新領域,還可以應用在文化創新、網絡知識創新等更廣泛的人類知識領域。
選擇“基金激勵機制”有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知識創新是屬于全人類的智識財富,理應由人們所共享。當然,“基金激勵機制”將保留創新者的“署名權”,并以“基金激勵”方式給予創新者適當的經濟和名譽回報。第二,“基金激勵機制”能夠最大限度地促進新知識的快速傳播,很好地將創新者的“個人利益”和“公共福利”統一起來。第三,“基金激勵機制”給予創新者的經濟回報相對固定。一方面,保證創新者的生活水平處于社會的中上階層;另一方面,并不以經濟利益的巨大誘惑刺激創新者的創新活動。在這樣的激勵機制中,創新者不會因“私欲”的膨脹而迷失自我。如此看來,“基金激勵機制”將是優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激勵機制。在對創新的“基金激勵機制”的保護下,全社會將共享一個巨大的“(網絡)智識資源”,先前的創新者以自己的智慧不斷豐富這一“共享資源”,并從“基金激勵”中獲得回報;而新的創新者則不斷地從這個“共享資源”中汲取營養。正所謂,“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相反,如果每一種創新都被打上了“專屬”的烙印,不能為更多的人方便獲取,那么,人類文明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