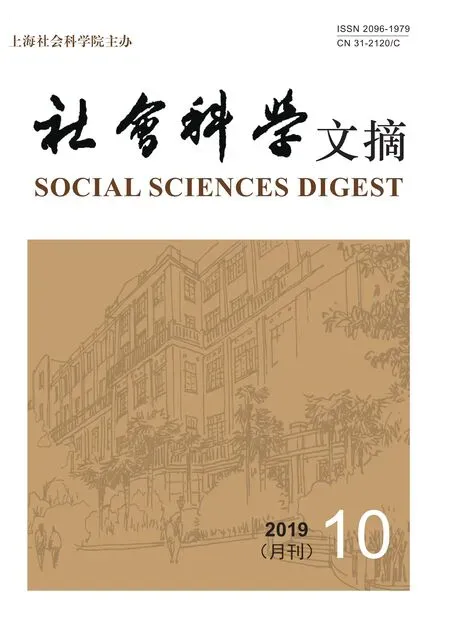“自然規律”概念的歷史演進
文/樊姍姍 劉大椿
當下,科學家一般把他們在自然界中發現的可理解、可測量、可預測的規則(regularity)稱為“自然規律”。毋庸置疑,近代意義上的“自然規律”概念,對于科學的興起意義重大,它的含義也是現代科學的基本信條。現代科學所采用的“自然規律”概念并非一種神啟,但是過往人們在論及其源起時語焉不詳。本文致力于對“自然規律”概念進行語意考釋,評析西方語境下關于“自然規律”概念起源的幾種不同觀點,探討“自然規律”概念在近代中國何以確立,并試圖說明這一概念的建構過程。
“自然規律”概念的考釋
兩千多年來,圍繞自然規律概念而產生的疑惑和歧義,反映了這個詞本身的含糊以及人們對它的不同理解。洛夫喬伊(A.O.Lovejoy)曾成功地區分了“nature”(自然)一詞在古代至少66種用法,艾力克·沃爾夫(Erik Wolf)也曾列出“nature”的12種意義和“law”的10種意義,而將兩者結合就具有了120種意義。所見諸多看法林林總總,莫衷一是,確也能說明“自然規律”這一概念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無疑帶有不確定性、易混性和可塑造性。要弄清這一概念,需要做許多功課。在筆者看來,以下問題首先亟待解決:
其一,中文中的“自然規律”究竟是對應于英文中的“law(s) of nature”,還是“natural law(s)”?關于二者的區分,發生在文藝復興之后。事實上,law(s) of nature中的nature(自然)是為實體,該詞組強調的是“是什么”(如:萬有引力定律、運動三定律等)。natural law(s)中的nature(自然)乃為性質,該詞組強調的是“應當是什么”,如同“natural right”(自然權利),其中“natural”強調“天生的、生來的”。兩者從翻譯的角度來看,前者直譯為“自然中的規律”或“自然規律、自然法則”,后者則為“‘自然的’規律”或“自然法”。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法”并非“自然”(實體)的,而是理性的(自然理性、上帝理性以及人的理性),它有神圣的淵源,源自至高無上的立法者,也可稱之為“道德法”或“法理法”。西方自然法學說在本質上是種正義論。簡而言之:自然規律或是自然界固有的客觀規律,或是人的認識為自然確立的規律。這樣看來,本文討論的“自然規律”應為“law(s) of nature”,而非“natural law(s)”。
其二,近代意義上的“law”源自哪里?是拉丁文“lex”,還是古希臘的“nomia”?“law”一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臘文“nomia”,但在近代“nomia”一詞更多指法律、法規等,直接對應的是“natural law(s)”。盡管西方文明起于古希臘,卻并非直接承繼古希臘。由于古典文本的失傳,中世紀阿拉伯帝國曾經在古希臘羅馬和近現代西方之間起到橋梁作用,它們開展過大規模、有組織的學術活動,將古希臘和東方科學文化典籍翻譯成阿拉伯文,再經文藝復興,又把那些翻譯成阿拉伯文的文本從阿拉伯文重新譯成拉丁文。可以合理推測,英文“law”是從拉丁文“lex”演變過來的。再則,在中世紀的歐洲,拉丁語是研究科學、哲學和神學所通行的語言;直到近代,通曉拉丁語也是研究人文和科學教育的前提條件。因此,討論近代科學中的“自然規律”概念時,我們應當認真分析拉丁語中的“lex”和英語中的“law(s) of nature”的語義。
其三,英文中“regularity”、“rule”和“law”幾個概念的意蘊,在中文的語境下應該如何理解?這三個單詞在漢語語境下之所以極易混淆,除了英譯漢過程中本身內涵被簡化的原因外,還與三者在起源上的相互交織是密切關聯的。盡管它們在使用中無法完全割裂,但是現代科學哲學對待三者是有差別的。當我們談及“regularity”時,更多強調的是自然界現象存在的規則性。至于“rule”,則更多意為治理、實驗過程中的“法則”、“規則”。近代科學意義上的“law”,乃是“規律”之意,較之頗為不同。
總之,科學哲學中談及的“自然規律”一般對應于“law(s) of nature”,源于拉丁文。隨著人們認識的加深,該詞(“law”)與“regularity”、“rule”等詞從初始混用到逐漸分離,最終具有了“實體的自然固有規律或人為之建構的規律”的內涵。盡管后來的實證論、約定論、實在論、建構論者對“law(s) of nature”的詮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內涵可歸結為兩類:自然界固有的規律(客觀規律),以及人的認識為自然確立的規律。換句話說,自然規律不只是對觀察到的規則(regularity)的陳述,也是一種基本規律的形式化表述,也可用來解釋或指稱廣泛的物理現象。科學哲學中各個派別對于自然規律的陳述,無外乎從這兩類基本意義衍生而來,最終又將歸入其中。無論其內涵如何變化、各學說之間論述的差異如何增大,自然規律始終是科學哲學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科學認識的目的所在。
關于“自然規律”概念起源的四種觀點
“自然規律”概念并非自來有之,對其起源的闡釋有利于理解近代科學的興起以及把握科學哲學的基本概念,因此,本文梳理了其中4種比較有特色的起源說法。
第一,“神的立法”說。就“自然規律”的起源問題,在西方學術界,19世紀到20世紀為近代“自然規律”做出解釋的學者幾乎都認為這一概念起源于“神的立法”(divine legislation或God's legislating for nature)隱喻。該觀點代表性的學者如齊爾塞爾(Edgar Zilsel)、李約瑟(Joseph Needham)、奧克利(Francis Oakley)、彌爾頓(John R.Milton)和馮肯斯坦(Amos Funkenstein)等,他們都認為自然規律概念與神的立法相關。盡管這些學者都將源頭指向“神的立法”,但在論述轉變的原因時,陳述各不相同。一種觀點認為,自然規律的概念轉變是伴隨著封建制度的衰落、資本主義的開端和王權專制的出現而進行的。而在筆者看來,“神的立法”不過為近代自然規律概念的出現提供了文字準備和隱喻。換句話說,“自然規律”與“神的立法”有一定的關聯,西方近代以來所使用的“自然規律”術語,是借助于隱喻、模型和類比的途徑,從中世紀“神的立法”觀念中引申而來的。究其緣由,則愈抽象的概念,愈是要通過隱喻的方式來進行說明。可以說隱喻往往是新概念產生的前奏。
第二,“詞源”演變說。即自然規律起源于學者們對拉丁語“regula”、“lex”的使用。“自然規律”并不是隱喻上帝法則,相反,它從一開始就意味著純粹而簡單的規律性(regularity)。在古羅馬和中世紀,“lex”與“regula”常常交替使用。“regula”最初的意思是straightedge或ruler(直尺),羅馬早期使用的第二種意義的“rule”,它是guideline or standard(指導方針與規范)的意思。同樣地,“lex”不僅用于政府或管轄,也用于由當局制定的原則或為各學科實踐而制定的原則。公元二世紀時,“lex”和“regula”在學科上意義幾乎相同。之后,這兩個術語的意義才逐漸變化。由此可見,“自然規律”從產生起就意味著一種秩序與規律性(regularity)。因此,“自然規律”的觀念起源于秩序、規則性,起源于從一系列看似雜亂無章的事物、事件中尋找出有規可循的東西,而這種秩序與規則性的思維傳統,在西方文明的早期就已經存在,并且為“自然規律”概念提供了思維準備。希臘哲學就是一種認為事物具有秩序的哲學。自然界秩序的原始表達即與那個大名鼎鼎的“邏各斯”有關。到了基督教時代,邏各斯又被引申為上帝造物的根源。近代以來,尤其是在文藝復興期間,對于秩序、規則性、理性等的格外強調,最終促成了“自然規律”概念的轉變和確立。
第三,數學啟發說(或自然數學化說)。物理學與數學因其對象的不同,本是兩門不同的學科。然而,在近代科學的產生過程中,除了實驗方法的推廣還有另外一種至關重要的方法,即自然的數學化(或數學化物理)。基于此,有學者認為“自然規律”起源于13世紀到15世紀對于數學知識的的運用。同時,數學定律后來被傳遞到自然哲學中,進而帶來物理定律的產生。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的工作大抵屬于這種情況。哥白尼頻繁論述和諧與對稱,開普勒更是用數學方式來表示行星運動定律。伽利略也沒有說他提出了什么規律,而是使用“比例”(ratio)、“原理”(principium)等字眼,這無疑出于對數學—幾何量度關系的重視和比附。更為重要的是,笛卡爾在1626年到1629年間發現折射定律時,他試圖用網球穿過薄布來解釋幾何行為的原因,其中薄布代表了折射體的表面并且它會改變物體的折射速度。由此可見,這個過程不是把幾何定律變成物理定律,而是尋求物理解釋來說明幾何理論。可見,自然的數學化推廣,為“自然規律”概念的出現與轉變提供了方法論準備。自然數學化意味著自然現象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可以用數學語言進行描述的,或者說自然本身的語言就是數學語言,自然數學化運動并非簡單地將數學表達運用于對自然現象的解釋。“數學化”首先意味著一種全新的自然認識方式,這對于近代意義上“自然規律”概念的提出可以說起到了非常直接的方法論作用。
第四,笛卡爾自然本體說(或自然與上帝分離說)。近代第一個在科學意義上完整使用“自然規律”概念的是笛卡爾。笛卡爾之前,自然規律是對上帝的比喻,而在笛卡爾那里,才將自然規律與上帝分離,并將它外在于上帝。在笛卡爾看來,自然規律就是自然“據以發生變化的那些規律”,并且“神絕對不會在這個新世界里行任何奇跡”。笛卡爾之所以需要“自然規律”這一概念,是因為如果“自然規律”被看作是自然哲學的合理構成,那它就必須具有解釋性而不僅僅是描述性的功能。笛卡爾若要建立新哲學體系,自然規律就必須是解釋性規律,而不僅僅是數學規律。根據笛卡爾的方法和上帝在他思想中的位置,他很可能是通過神的立法思想和圣經中“物理規律(physical regularities)和定量操作規則(quantitative rules of operation)”的理念,重新創造了“自然規律”的概念。事實上,笛卡爾的自然規律是構成這個世界的機械規律。因此,近代意義上的“自然規律”通過笛卡爾的使用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并經過牛頓而被人們廣泛使用。本文認為,與早些時候哥白尼所謂地球運動正是“遵循自然規律產生的效果”,與伽利略的“原理”(如慣性原理)、定量的“比例”關系等相比較,笛卡爾明確指出科學的目標是“自然規律”。笛卡爾的理念對于“自然規律”的起源如此至關重要,更在于他推動了牛頓對于這一概念的使用。
可見,源于拉丁文的“law(s) of nature”,經過中世紀與文藝復興,伴隨著語言、思維、方法和人為的推動,最終導致科學意義上的“自然規律”概念得以確定,并成為近代科學革命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是,這一概念的起源是非常復雜的。“神的立法”從文字和隱喻角度為近代“自然規律”的出現提供了準備,避免這一科學概念空穴來風,有了易于人們理解和接受的對應物。西方文明早期就有的秩序與規則性思維,經過文藝復興進一步被激發,人們迫切地希望從雜亂無章中尋求規則與理性,這無疑為“自然規律”提供了成長的思維土壤,使得這一觀念被人們使用和認可成為可能。自然的數學化推廣,讓自然現象不再高高在上,而可以用數學語言的方式進行書寫,這就從方法論上促成了“自然規律”概念的發展。笛卡爾引入的一個高度人為的概念,將“自然規律”與上帝分離,賦予它新的意義,并最終通過牛頓被人們廣泛使用。可以合理認為,是這些不同起源說協力導致近代科學重要概念“自然規律”的出現。
“自然規律”概念在近代中國的確立
“自然規律”概念在西方文明土壤中是如何孕育出來的,已如上述。那么,它在中國近現代語境中,又是如何引進和確立的呢?過去國人在談論中國“自然規律”概念的時候,往往有意無意將它限定到中國古代“固有”用法中,并將它看作是中國傳統“天”、“理”、“法”、“道”概念的一部分,而對它的由來語焉不詳。
中國傳統文化中原無“自然規律”這一概念,但有類似指稱。受李約瑟的影響,許多西方的學者認為,“自然規律”這一術語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的;甚至認為,因為自身沒有在“神的立法”隱喻下誕生近代自然規律概念,終致近代科學也未能誕生在中國。確實,“自然規律”一詞在古代中國是沒有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相應的概念。西方意義上的“自然規律”,類似于中國古人的“道法自然”和“理法”、“天”、“格物窮理”、“道”等概念,中西方這些概念表達的都是一種宇宙觀和秩序觀。然而,“天”、“道”、“理法”等概念,不同于西方蘊含至高無上的立法者意蘊的“自然規律”概念。中國的“道法自然”概念中的“自然”,是自動、自發、不帶人的痕跡、不含造物主的觀念。
事實上,“自然規律”概念在清末作為科學概念為人所知,是從日本引進的。甲午戰爭之后,學習日本的熱情高漲。這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界,使得“law of nature”經歷了從中式譯詞“理法”到日式譯詞“自然”、“法則”的演變。通過留日學生和西學的傳播,“自然規律”一詞最終在中國學者筆下得以確立。
近代日本學者在翻譯歐美術語時,會用古漢語固有字詞去新造相應的意譯詞匯。西周在《尚白札記》中,提出將東方哲學中的“理法”對應于英文詞匯中的“law of nature”。此外,現代漢語中的“自然”、“法則”、“規則”這幾個詞也都源自日本。此后,留日學者通過學習與傳播西學,將日本的新學、新知等進行翻譯,并在關鍵術語的使用上或保留或重組了日本學者們的譯法。1906年,嚴復在《〈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中,主張人們要面向“自然”去求知,他使用的“自然”已非古代中國老子意義上的“自然”,而是從客體和對象實體意義上來談論了。更重要的是,嚴復還使用了“自然規律”、“自然規則”、“自然律令”、“自然公例”等概念,這與他原先習慣于聯系傳統中國文化術語,從英語直接翻譯、移植西文于漢語不同,而改用“自然規律”這一術語來代替先前所使用的“理法”、“天行”等譯詞了。
“自然規律”一詞的出現,對近代中國科學發展具有非凡的意義。近代國人用“自然規律”代替詞意生澀、復雜的“道”、“理”等概念,實有利于人們準確地把握科學概念,也有利于人們將科學知識與儒家倫理進行區分,便于西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與普及。
從古拉丁語“lex”到英語中的“law of nature”,再到日語中的“自然”、“法則”,之后漢語吸收日譯術語,在近代西學傳播的過程中將“自然規律”一詞確定下來,最終成為世界性的科學研究的核心術語,這就是自然規律概念的歷史演進概要。作為近現代科學基本概念的“自然規律”,其起源和演進不是一個突變過程,也不是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確有語言、思維、方法等方面的積累和準備。每個時代對于這一概念理解上的差異,都會激發對該概念的重新詮釋與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