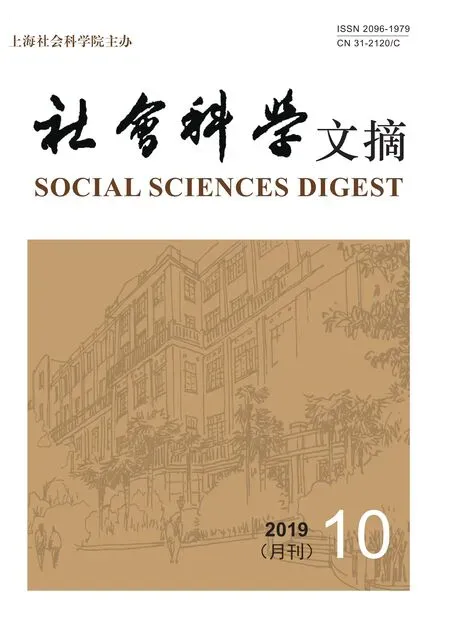重新省思政治傳播的價值旨歸
文/荊學民
政治傳播以“重要變量”融入時代大變局
該怎樣描述和認知當下我們所置身于其中的“時代大變局”?我覺得至少應從世界歷史演進和中國社會進步兩個視野,把人類歷史的縱向前進和時代變遷的橫向延展兩個維度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對“時代大變局”的坐標有一個比清晰和相對準確的把握。
從世界歷史演進即人類歷史的縱向前進這個維度看,我們仍然處于馬克思一生所傾力研究的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進步的“歷史大時代”。盡管很長時期以來社會主義運動似乎有些“式微”,但是,人類歷史必然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邁進這一理論論斷的科學性并沒有被駁倒,也并沒有冒出來任何新的理論能夠取代這一偉大理論論斷。因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區分歷史時代的根本依據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即社會的生產方式。正是生產方式的不斷發展,使人類社會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邁進。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盡管我們所處的“歷史大時代”同馬克思當年所描述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個歷史時代,就是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走上世界歷史舞臺的“歷史大時代”。
從歷史進步的動力系統看,浩浩蕩蕩的共產主義運動,依賴著轟轟烈烈的以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理想為核心的政治傳播。可以說,這個“歷史大時代”的產生與行進過程,也是一個依賴社會主義政治傳播而形成的過程,政治傳播以“主變量”的身份融入“歷史大時代”之中。
當“歷史大時代”在中國這塊肥沃的土地上進入到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便勢不可擋地登上世界舞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引領和示范效應,使世界歷史進入前所未有的“時代大變局”。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人類歷史的縱向前進和時代變遷的橫向延展兩個維度的完美結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政治傳播“恰逢春風勁吹時”。政治的文明,媒介的進步,傳播技術的發展,信息生產的豐饒,新形態的政治傳播日新月異,盡展風采,可謂政治傳播的激情“化作濃墨寫青山”。尤其是,區別于西方政治傳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傳播,擺脫了西方那種為特定競選政治服務的窠臼,跳出了西方那種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媒介中心”的專業化操弄,為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致力于為人類貢獻智慧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現在,誰都難以否認,政治傳播已然成為時代大變局的重要變量。
政治傳播成為時代大變局的重要變量深刻地意味著,在國際政治不確定性日趨增加、國內政治形勢日益復雜的情勢中,政治傳播時時刻刻都可能成為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它既可以為時代的進步作出獨特的貢獻,也可能背離自己的價值本性,阻礙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的進步。因此,時刻警示和喚醒政治傳播“不忘初心”的價值旨歸,應成為政治傳播研究者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社會責任。
政治傳播價值旨歸一:建構和維護政治公共性
政治傳播不是“政治”與“傳播”的機械疊加和拼湊,而是“政治”與“傳播”的有機“同一”。政治與傳播的同一,決定了政治傳播的“元初”的價值旨歸就應基建于政治和傳播的價值品性之上。然而,現實的政治傳播,總是在融合著特定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十分復雜的社會環境之中進行的,因而,要做到不忘本性、不偏不倚是十分困難的。很多時候,政治傳播會偏離甚至背離其本然的價值旨歸。
從理論上講,“政治”與“傳播”并不是一種“等位序列”的范疇。政治傳播中的“政治”總是處于主體和強勢的地位,因此,強調政治傳播不能偏離其本初的價值旨歸時,還需首先進一步明晰“政治”的天然本性。
在古希臘時期,赫拉克利特將政治界定為“城邦”——相對于私人家庭的“社會”;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盧梭將政治設想為“公意”;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將政治表達為“絕對命令”,之后的黑格爾將其改造為“倫理理念的現實”,最后到馬克思這里,政治重新被視為經由國家而又消滅國家之后的“沒有國家”的“新社會”。我們既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那么應該理解并認同,政治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不斷地超越“個人”“家庭”而走向新“社會”的維護公共秩序、捍衛公共利益、實現人類“公共性”的過程。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基本要義,也是政治任何時候都不能背離和脫離的價值本性和使命擔當。
“公共性”意味著對現實的各種個人個體或團體利益的超越,正像盧梭所言,政治著意的是一種超越任何私利的“公意”。正因如此,任何政治都是從一種超越現實的對未來進行設計和規制的理想出發,政治理想和基于這種理想之上的政治目標是政治的“基石”和出發點。而又由于政治掌握著“公權力”,所以任何政治在實現其特定的政治理想和目標時總是“本能”地首先以政治宣傳的形態來實現其政治傳播。政治宣傳的本質和主要特征,就是基于超越現實的理想性政治目標的政治信息“灌輸”和政治權力意志的“推展”過程。政治宣傳最能體現政治傳播中的“政治統攝傳播”。
從學理上講,我們并不否認政治傳播中一定的政治宣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政治宣傳天然性地存在于國家政治之中。國家政治所依賴和使用的主要工具或傳播路徑,正是政治宣傳。政治宣傳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本質特征和強大的國家機器功能,就是因為它是國家政治存在和運行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正如歐根·哈達莫夫斯所言:“事實上,從一開始就沒有純粹的宣傳可言。宣傳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權力,宣傳只有被當成意識形態的工具才算取得勝利。若意識形態的工具被剝奪,將導致權力結構的瓦解。意識形態、宣傳和權力三者不可分。”但是,必須高度警惕的是,當政治被演變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時,政治宣傳就會成為政治權力的工具,就會變成馬克思當年批判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說的,完全成為統治階級用來欺騙人民群眾的手段。而當這樣的政治宣傳成為政治傳播的主軸時,政治傳播中的“政治”就已經背離了政治的元初價值旨歸。
當下,人類社會的政治進入有史以來的“不確定”的新形態之中。傳播的激情借助于傳播技術的革命,導致人類社會同樣進入有史以來的信息迷亂的新形態之中。固然,政治與傳播深度融合的政治傳播,為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和人類社會的政治治理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政治上的種種類型的民粹主義力量花樣翻新,打著“人民”或“平民”的名義“反智識”“反邏輯”“反建制”“反精英”“反中心”“反真相”。民粹主義支配下的政治在“人民至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下,越來越背離人類政治前進的方向。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理想創立的政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依靠政治理想建國的國家。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復興的輝煌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大到強的成長歷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地實現政治理想的歷史。正因如此,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不斷地在政治上開展黨性教育,以保持政治上的先進性。尤其是,當前正在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主題教育,就是讓全黨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不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要求黨的干部理論學習有收獲、思想政治受洗禮、干事創業敢擔當、為民服務解難題、清正廉潔作表率,錘煉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品格、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偉大夢想共同奮斗。毫無疑問,這正是一種期望可以取得實效達到目標的政治回歸其“公共性”價值旨歸的政治傳播實踐活動。
政治傳播價值旨歸二:揭示和呈現事物真相
雖然作為一種“政治統攝傳播”的政治傳播,其政治的運行邏輯制約著整個政治傳播過程,政治的“公共性”價值旨歸牽導著政治傳播的最終目的和效果,但是,政治傳播畢竟不是純粹的政治權力操作過程,“傳播”在其中愈來愈活躍、愈來愈強勁、愈來愈關鍵、愈來愈重要。甚至可以說,傳播技術的革命性變革,作為一種“活躍性變量”,不斷地在刷新著政治傳播的形態。“傳播媒介”的本性和傳播的運行邏輯的深度融合和制約,決定著政治傳播在具有政治的公共性的價值旨歸的同時,具有傳播真實信息、追索事物真相、揭示客觀真理的價值旨歸。
從理論上講,“傳播”本質上只是一種被人使用的中介。傳播作為一種中介,其主要功能是通過“信息的流動過程”,使社會不斷減少“不確定性”。而只有追索和呈現事物真相、揭示客觀真理,才能使社會從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呈現事物真相、揭示客觀真理成為傳播的價值品性和價值旨歸。
然而在現實中,傳播的運行會轉化為一種特殊的“權力”,甚至像曼紐爾·卡斯特爾所言:傳播即權力,傳播作為一種權力是政治權力和其他權力運作的核心,因為權力的實踐總是建立在對信息和傳播的控制之上。控制了信息和傳播,就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如果說,在政治傳播的實踐中,政治傳播要始終堅持基于政治“公共性”的價值旨歸需要反復告誡,那么,政治傳播堅守基于傳播的“揭示真相傳遞真理”的價值旨歸就更應高度警醒。
現實政治傳播的“傳播”容易在幾個方面“失守”。
第一,“屈服”于政治。任何政治均需要通過傳播而實現特定的政治社會化,需要通過傳播培育自己的“政治人”。由于政治擁有強大的公權力,其天然性的總是要求傳播為自己的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務,要求傳播邏輯附著乃至臣服于政治邏輯。因此,當政治乃能堅守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公共性”價值旨歸時,傳播就通過不斷揭示真相傳遞真理展現和釋放出對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正能量;而當政治沒有堅守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公共性”價值旨歸時,傳播本應監督、揭示和批判政治的弊端,矯正政治的偏離和脫軌。但是,現實中傳播往往畏懼政治強權,偏離甚至背叛自己的價值品性,掩蓋政治真相,傳播政治謊言,蠱惑政治野心,成為政治的“幫兇”。歷史上,此等案例并不鮮見。當下,少數西方敵對勢力威脅和顛覆中國與之類似的案例并不乏見,國內政治腐敗分子和勢力把傳播作為自己私利的工具來欺騙民眾瞞天過海的例子也不勝枚舉。
第二,“獻媚”于資本。在人們日常的認識中,權力作用于政治領域,資本作用于經濟領域,其實不然。馬克思一生致力于對資本和資本主義的研究和批判,他的結論是,資本從來到世界,每個毛孔都奔涌著主宰世界的血液。資本和政治權力一樣,已經完全是支配包括生產、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現實世界的整個現代社會的“整體性力量”,而且,二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還應該指出,由于“市場經濟”的“相通性”,這里的“現代社會”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圖,因此,我們這里所說的政治傳播中傳播對資本的“獻媚”,首先就是在利益的誘惑下以獲取利益為最終目標和目的,進而在可以帶來利益的資本力量的威逼利誘之下造謠惑眾掩蓋真相。相信這一點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有更為切身和切近的體會和感悟。
第三,“淪陷”于技術。現代社會,傳播的實現越來越依賴于傳播技術的發展,技術的發展決定著傳播形態的革命。因此,對于傳播而言,除了政治和資本之外,面對的強大的力量就是技術。技術產生于科學,所以,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認為,“在現代社會,絕大多數新興權力是來自科學,不論是什么樣的科學,而不是來自于經典的政治過程”。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技術并不能等同于科學,技術只有被人使用時才具有現實性,而當技術被人選擇和利用時,就以最為隱蔽和柔軟的方式蘊藏著最為尖銳和鮮明的價值觀。這一點,現在最為時髦的傳播技術中的“算法政治”就是對我們的最尖銳的警示。哈貝馬斯就此把技術對人的控制上升到“新的意識形態統治”的高度。當技術中隱含的政治權力內在地左右著技術的使用的時候,越來越依賴于技術的傳播則就深深地淪陷于技術的綁架和約束,其信息傳遞的社會角色和功能,就有可能被綁架在政治或者資本的權力鏈條之中,根本無法實現甚至背離自身的價值旨歸。
“傳播”本應以傳遞、運載、呈現客觀信息為旨歸,以追索事物真相,揭示客觀真理為本性。因此,當受制于技術的傳播附著于政治權力和金錢資本、淪落為政治權力和金錢資本玩弄的工具時,傳播就偏離了本性。而當偏離了本性的政治與傳播合謀,左右了人類社會的信息呈現面貌,進而改變著人類交流和交往方式的時候,就意味人類的政治傳播已經脫軌。歷史上,由于政治傳播脫軌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的教訓,我們是不可以忘記的。
建構合理張力,矯正政治傳播
冷峻地觀察和省思新的時代,全球化的浪潮已經把政治傳播緊緊地捆綁在滾滾向前的車輪上,因此,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激烈博弈,已然把政治傳播的正反張力撕裂到了極致。在不確定性和社會風險性增強的時代,政治傳播中的“政治”,正在建構和維護公共性與強權維護私域性的撕裂中掙扎;政治傳播中的“傳播”,亦在呈現真相引領正義與獻媚政治獲取利益的撕裂中掙扎。我們理論研究者,有義務警示政治傳播回歸本位,以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正能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年大會上講道:“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難而上、挺身而出的擔當精神。”我們認為,這種精神移植到我們眼下的政治傳播上也是很適合的。試想,應對挑戰、抵御風險、克服阻力、解決矛盾,政治傳播都不敢挺身而出,那能靠誰呢?但是,若沒有正確的、正能量的政治傳播,那就相反,會加大挑戰、增加風險、加重阻力、激化矛盾。
政治、傳播(媒介)、資本都具有自己的特質,在具體的運行中,都具有“本能的邏輯”——“政治邏輯”追求權力控制;“媒介邏輯”追求事物真相;“資本邏輯”追求經濟利益。而且,政治邏輯對媒介邏輯和資本邏輯具有一種本能的控制欲和吸納欲,以便不斷強化自己的合法性基礎。而資本擴張到一定階段,也會尋求與政治和媒介的結合,以通過制造社會輿論和或引起政治權力參與達到利潤最大化。
合理的政治傳播機制與形態中,政治當有正義的追求,傳播當有公正的使命,資本當有正當的邊界。就是說,政治當有為傳播和資本確定正義方向的責任,傳播當有監督政治和資本的責任,資本當有服務正義的政治和公正的傳播的責任。幾個重要的變量之間,在各自正當合理的基礎之上和邊界之中,既相互制約,又交叉合力,始終保持適度和良性的張力,以使政治傳播在強化理性深思、傳播真實信息和維護人類正義的軌道上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