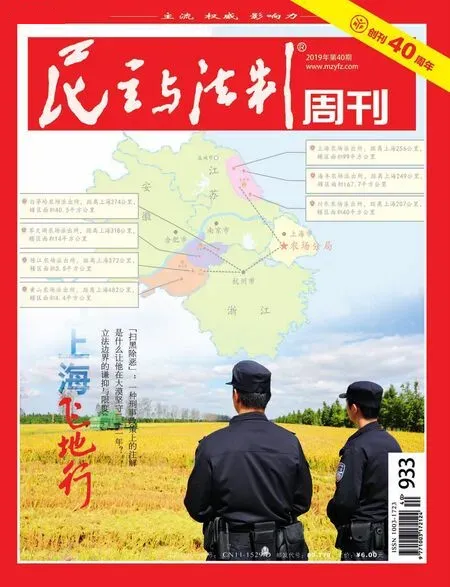立法邊界的謙抑與限度
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草案進行了三審。引人關注的是,此前出現在草案一審稿和二審稿中的有關“隔代探望權”的條款,在三審稿中已經消失了。
所謂隔代探望權,其實是從現行婚姻法所規定的離異父母一方對子女的探望權延伸而來。簡單而言就是,父母離婚后,祖父母、外祖父母對孫子女、外孫子女進行探望的權利。盡管現行婚姻法對于隔代探望權并無明確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已出現了多起相關訴訟,要求在立法上確立這一權利的社會呼聲也一直存在。在此背景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草案一審稿和二審稿中均對隔代探望權作了規定。相對于一審稿的原則規定,二審稿更是對權利行使的條件作出了細化規定,即“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孫子女、外孫子女,如果其盡了撫養義務或者孫子女、外孫子女的父母一方死亡的,可以參照適用父母離婚后探望子女的有關規定”。也正因為隔代探望權一度被視為立法的一大突破,因而三審稿對相關規定的刪除處理,難免引發議論紛紛,贊同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不少人對此難抑失望之情。
那么,似乎符合民意的隔代探望權入法問題,為何要踩剎車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樣的立法設計或沖動,明顯超越了立法的適當邊界,有違謙抑的原則和有限立法的現代法律精神。
立法,固然應當反映社會的訴求。然而,社會訴求本身就千差萬別,民意表達亦非千篇一律。更重要的是,對于立法設計者而言,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注意以下問題:其一,究竟是法律問題還是道德問題,通過立法調整抑或通過道德約束,哪一種效果更好?其二,并非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能夠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問題,也并非都需要以制定法律規則的方式來解決。有時,通過司法的個案裁量或個別處置,反而更具有靈活性。其三,立法資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資源必須用在更為緊迫的社會規范性議題上,因而立法必須保持相當程度的謙抑精神,而不是相反。一旦濫用立法資源,不當或者過當地干預社會生活,很可能引發新的社會問題。
仍以隔代探望權為例,如果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對其作了一般性規定,盡管立法著眼點是為了促進親情關系的和諧,但從客觀效果看,卻很可能引發新的家庭關系矛盾。畢竟,很多夫妻離婚后,都會帶著孩子與他人再婚,重組成新的家庭,這種新的家庭關系本來就復雜而脆弱,如果前段婚姻所生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以行使隔代探望權為由,頻繁打擾新的家庭,很可能干擾新組建家庭的正常生活,引發新的矛盾和沖突。如此,就與立法者良善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了。
當然,隔代探望權不宜入法,并不等于反對隔代探望權本身。在離婚率高居不下的當下,作為親權的延伸,隔代探望權的行使,在很多情況下可以有效慰藉祖輩和孫輩的心靈和情感,符合我國傳統的家庭倫理乃至社會公德。但這一問題的解決,完全可以由當事人通過協商達成共識。如果無法達成共識,也可以通過司法途徑,由法官在個案中自由裁量。
換言之,隔代探望的權利問題,既然可以通過私人協商或司法訴訟解決,立法就沒必要跟進和過度干預。隔代探望權可以有,對于合情合理要求行使隔代探望權的訴求,司法機關在實踐中也應給予支持,但為了防止隔代探望權的濫用及其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立法上并不宜對其作出一般性的硬性規定。
在社會生活日益復雜化和新事物層出不窮的當下,法律的滯后性日益凸顯,立法的活躍幾乎是必然的。但越是在這樣的境況下,就越要有“分際”的意識,時刻謹記謙抑立法和有限立法的現代法律精神,以此遏制不合理的立法沖動。不僅要做到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還要做到立法的歸立法、司法的歸司法。
一言以蔽之,比立法者的雄心壯志更重要的,是洞見立法的邊界,并謹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