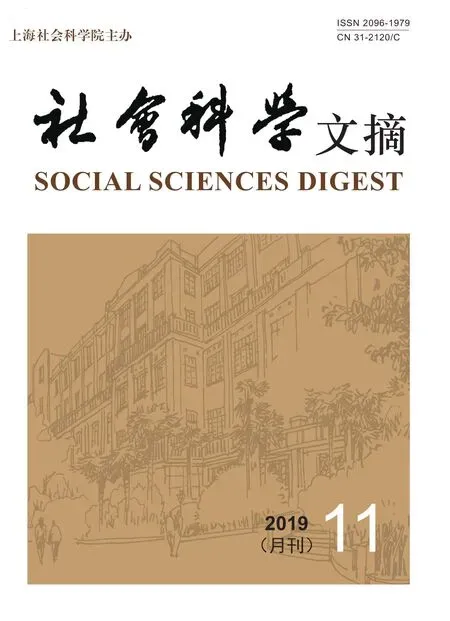話語權力與情感密碼:網絡政治動員的意識形態審思
文/羅佳
近年來,網絡政治動員作為一種新興的政治博弈現象受到學界關注。“身體缺場的行動在場”“無組織的組織”“象征性聚集”等相關學術概念都指認了網絡政治動員與現實政治動員不同的特征和發生機制。可以看到,政治動員從來離不開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網絡政治動員對意識形態或者說話語的依賴性在增強而不是削弱。于是,學界對于網絡政治動員的理論闡述從宏觀視角轉向微觀視角,從社會結構分析轉向話語文本分析。本文嘗試從意識形態的視角切入,從宏觀的意識形態圖景、中觀的社會心理和微觀的價值取向三個維度,對網絡政治動員的本質及其特征做出理論上的剖析。
話語權力:網絡政治動員研究的視角轉向
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催生了網絡動員這一新生現象,其基本的涵義指政治主體在網絡空間內通過信息的發布和傳播來調動政治能量,從而達到其現實政治目的的行為過程。網絡政治動員與傳統的政治動員有何區別和差異?學術界對此爭論不休,未有定論,整體的研究趨勢是從宏觀視角轉向微觀視角,從社會結構分析轉向話語文本分析。
法國思想家福柯的“話語權”概念成為學界分析網絡政治動員經常援用的理論資源。在福柯看來,話語總是指向一種權力關系。后馬克思主義學者拉克勞、墨菲在福柯的基礎上走得更遠,他們認為政治斗爭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話語斗爭”。曼紐爾·卡斯特從新社會形態變革的視角來理解“網絡社會”,斷言網絡社會改變了權力“密碼”,催生了新的信息權力,這種權力的部位是人們的心靈。因此,與以往存在與政治、經濟和軍事生活中的實體權力有很大區別,信息權力是通過對廣大網民的思想觀念、觀點態度和價值選擇施加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思想、文化和精神權力,也就是話語權。這種權力是網絡化的而不是科層制的。
在中國的語境中,政治動員一直是黨和政府的一種傳統優勢。無論是革命時期的“宣傳下鄉”和“軍民動員”,還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發起的政治動員,從來都是有組織、有計劃、自上而下的宏觀政治行動。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網絡政治動員逐漸興起,并形成了一種有學者稱之為“非對稱”的動員態勢:動員主動權開始從黨和政府手中轉移到普通網民手里。一些學者從網絡自由主義的立場研究網絡技術給中國帶來的“賦權效應”,如鄭永年提出“技術賦權”、楊國斌提出“數字公民社會”、彌爾頓·繆勒提出“網絡監管難題”等觀點。但是,這種基于網絡自由主義立場的宏觀理論剖析效度難以檢驗,尤其是對于網絡政治動員的多元性、復雜性和變革性洞察力不足。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轉向微觀政治的視角來分析網絡政治動員的復雜機制,譬如挪威學者格里斯借用了拉克勞、墨菲的話語理論和斯科特的“底層政治”概念,關注中國微博上的話語博弈。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形象化、具象化、景觀化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內涵。譬如網絡儀式、游戲視頻、故事段子、表情符號等,不同的場景生態、視覺技術進步、集體表象導向、個體權力的發揮都會發生價值作用。網絡政治動員研究“話語轉向”的關鍵不在于概念或者話語創新,而在于對意識形態這一結構性要素的指認和理解。網絡空間中的意識形態要素不能拘泥于傳統的理性化、系統化觀念系統的抽象理解,而要關注意識形態感性化、碎片化、流變化的存在方式,即“感性意識形態”。
宏觀語境:網絡政治動員的意識形態背景
網絡政治動員既是一種政治行為的現實動員,也是一種價值理念的思想動員,一定社會的意識形態及其內在結構關系,決定了網絡政治動員能夠提取到何種資源,形成何種性質的動員,以及這種動員的發展空間和水平。形象地說,一定社會所存在的、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影響的意識形態就是網絡政治動員的“資源庫”,網絡政治動員只能在既有的資源庫中選擇“武器”,同時在網絡政治動員的過程中進行新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創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正值中國革命處于迷惘、探索之時,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帶來了極為重要的思想理論資源,毛澤東形象地將其比喻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倘若沒有這種新的思想武器的輸入及其中國化的普及過程,中國共產黨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就無法開啟。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同樣充滿了各種矛盾,這些矛盾必然在意識形態領域里表現出來,從而使得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成為一個具有復雜結構關系的觀念總體。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馬克思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儒家思想、民族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多種思潮,正是這種豐富多樣的意識形態資源為網絡政治動員提供了多樣化的資源選擇,從而塑造了性質各異、形式多樣的網絡政治動員。
如果說存在哪些種類的意識形態為網絡政治動員提供了可以選擇的資源,那么,意識形態的內在結構則決定了網絡政治動員的發展可能及其水平。這種內在結構,主要體現為主流意識形態、非主流意識形態和敵對意識形態復雜互動形成的整體形態和結構。在當代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意識形態領域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革:主流意識形態、非主流意識形態與敵對意識形態之間呈現相互影響、相互競爭、沖突融合的復雜格局。意識形態的復雜格局與網絡政治動員的復雜圖景形成了相互呼應、相互影響之勢。一方面,意識形態領域多樣思潮的涌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開放和包容,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宣傳教育路徑以及對待其他意識形態的整合方式上發生了重要變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積極主動變革,是網絡政治動員興起的重要前提性條件之一。另一方面,網絡政治動員作為一種重要的新的變量作用于意識形態領域,也對當前的意識形態發展態勢施加影響,并推動著意識形態生態環境的變化,帶來復雜多樣的意識形態后果。
從網絡政治動員所憑借的平臺來看,媒介變革與意識形態嬗變的互動關系,提供了網絡政治動員的重要前提。網絡政治動員必須以網絡信息傳播作為其平臺和基礎,而網絡信息傳播與意識形態的嬗變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動關系,這就使得網絡政治動員不僅受到技術平臺的制約,也受到意識形態的前提性制約。這種互動關系可以從兩個相互關聯的維度來具體把握:一是作為生產工具的媒介變革推動了社會變革,并進而推動意識形態變遷;二是媒介信息傳播方式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一方面,信息傳播方式會影響意識形態的傳播方式及其效果。意識形態只有通過宣傳教育才能從理論形態轉變為實踐形態,從官方話語轉變為民眾心理認同,傳播的理念、方式和策略要與媒介傳播技術相適應,否則就會影響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實效。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意識形態的性質、內容及其變革決定了信息傳播方式的發展水平。出于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考慮,執政者一般都會對信息傳播采取一定的審查、限制和篩選措施,這種措施的嚴厲與否、執行方式往往是由政權性質和意識形態的性質共同決定的,因此,媒介傳播的相關制度要受到意識形態的決定性影響。
中觀動因:網絡政治動員的群體心理發酵
由于在網絡空間中主體往往以符號化、象征化的方式存在,這種“身體不在場”的分散個體何以能夠被動員起來?答案就在于網絡政治動員的成功發起高度依賴于網民在心理上的“共意”、情感上的“共鳴”和價值上的“共享”,是共同的心理狀態、價值觀念和情感感染將分散的個體凝聚起來、將缺場的主體團結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網民的社會心理可以視為網絡政治動員的一種結構性要素。顯然,網絡群體的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無意識不可能僅僅在網絡上策略性地建構出來,而要受到現實生活中人們業已存在的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無意識的制約和影響。換言之,網絡政治動員只能“點燃”而不能“制造”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無意識,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無意識提供了孕育網絡政治動員的有機土壤,準備了引爆網絡政治動員所需要的“火藥”。承認這一點,就承認了一個社會所存在的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無意識為網絡政治動員提供了基礎和前提。
意識形態并不是漂浮在社會上空、脫離于人們生活實踐的思想、觀念體系,而是根植于人們的日常生活,滲透于人們的社會心理、社會性格乃至于社會無意識之中。因此,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無意識是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重要媒介,是意識形態從總體的階級意識到群體意識形態、從理論形態向實踐形態轉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首先,社會心理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如果說意識形態具有系統化的理論形式的話,那么,社會心理則是一種零星的、粗糙的、不成熟的反映。社會心理可以視為意識形態的“素材”和“原料”,意識形態則是社會心理的“成品”。其次,意識形態與社會性格息息相關。所謂社會性格是指在同一社會文化背景下絕大多數成員所共有的性格特征。社會性格是由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的宣傳教化共同決定的。最后,社會無意識與意識形態也存在密切的關系。弗洛姆提出了“社會無意識”的概念,強調“社會無意識”是由“社會的過濾器”(語言、邏輯、社會的禁忌)造成的,而“社會的禁忌”的標準又是由意識形態所確立的。也就是說,通過語言和邏輯等的加工,意識形態所不允許的表象和觀念統統都被驅趕到“社會無意識”的領域中去了。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無意識是由意識形態孕育出來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意識形態功能發揮的實踐樣態。
正是這種在現實中業已存在的社會心理、社會性格和社會無意識,在某一個偶然因素的引爆下成為網絡政治動員的重要思想根源和心理基礎。當前我國諸多的所謂“非利益相關”網絡政治動員的發生,盡管沒有共同的利益因素作為牽引力量,但必然會有意識形態所孕育的社會心理、社會性格或社會無意識作為其心理基礎和推動力量。即便是利益緊密相關的維權式網絡政治動員,如果不能調動廣大網民的心理能量、爭取到廣大網民的支持而形成足夠大的輿論力量,其社會影響和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因此,每一次政治動員,都可以視為某種社會心理、社會無意識的集中發酵和突然引爆,光有點火線而沒有社會心理所儲備的足夠火藥,顯然是行不通的。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通過網絡空間中群體心理、群體意識的分析,來預判、把握網絡政治動員發生的規律和趨勢。
微觀要素:網絡政治動員的主體價值取向
從網絡政治動員所發起的主體來看,網絡政治動員的主體——人,既是意識形態的動物,又具有突破意識形態的可能,這就為網絡政治動員的發生及其限度提出了主體維度的前提和限度。一方面,人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動物,正是意識形態創造了主體并使他們行動。一個試圖逃避意識形態教化的人只能是自然存在物,而不可能是社會存在物。作為公民和網民雙重身份的動員主體,只能在他的頭腦業已存在的意識形態圖景的前提下發起動員,他以為自己是完全自主的,但實際上已經被某種意識形態俘獲了。這種意識形態的俘獲,是通過教化、習俗和長期熏陶的影響,使得主體對于某種意識形態的認同成為其順利進入社會、與他人進行交往的一種“實用證書”和必備技能,是成為合格社會成員、順利融入社會文化氛圍必不可少的資格。而人被這種意識形態俘獲之后,就往往會以此作為自己的價值標準來發動、采取和選擇相應的行為,甚至在不自覺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正是意識形態發揮其功能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人既戴著意識形態的鐐銬跳舞,又能夠在一定程度跳出意識形態牢籠,具有重新闡釋、整合乃至創造意識形態的可能。人能夠基于社會實踐而改變、改造新的意識形態;人被意識形態塑造,又具有突破意識形態的可能,這才是現實的人與意識形態的辨證關系。網絡空間中以符號化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主體是這種現實人的延伸,這種延伸并不會消除人與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而只會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我們分析網絡政治動員必須承認的基本前提。
作為網絡政治動員的發起者和參與者,受到意識形態影響和制約的主體既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既投射了個體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又不免受到群體心理的感染和裹挾,呈現出主體性與被動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現實性與虛擬性的復雜臉譜。也就是說,從現實生活到網絡空間、從個體身份到群體一員、從冷靜的旁觀者到積極的行動者,主體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之間受動性和主動性的交織特征以更為復雜的方式呈現出來,并體現出巨大的個體差異和群體共性,單純強調某一單一維度都是片面和有失偏頗的。就其受動性而言,網絡政治動員的參與者是在具有先入為主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的前提下,對一種意識形態或另一種意識形態的選擇和判斷,他們頭腦中的“意識形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將選擇哪一種意識形態,以及對這種意識形態認同的程度。主體在網絡空間中能夠以其興趣、利益和價值觀加入到某一社區,從而實現了網絡社區中主體聲音的同質化聚集和螺旋式擴大,從而使得意識形態和文化圖式對于主體的影響和決定功能在網絡空間中進一步加劇。勒龐曾經在《烏合之眾》中描繪了個體變為集體行動中群體一員時,就會喪失其主體性、客觀冷靜性,變得非理性、情緒化和從眾性,桑斯坦則更為明確地提出了“從眾心理”和“群體極化”等主體淹沒在集體聲音中的觀點,媒介學者也提出過“沉默的螺旋”效應,這種效應在網絡政治動員中都有充分的體現,進而反映了在網絡政治動員中意識形態要素對于個體的俘獲能力更為突出。就其主動性層面而言,主體也不完全是意識形態的俘虜,虛擬交往與現實交往是相互聯系的,人們總能在網絡政治動員中發現其現實生活中的利益訴求、心理需要和價值選擇,只是這種現實的因素經由網絡政治動員而變得復雜多變,但其來源于社會現實的本質并未改變。同時,主體在網絡政治動員中的主體性呈現出巨大的差距,網絡意見領袖往往具有相當大的意識形態創造、選擇和引領能力,而沉默的大多數則更多成為接受某種意識形態的受動者,但這種受動也不完全是被動的,網絡意見領袖也只有充分理解并尊重沉默大多數已經存在的意識形態圖式進行宣傳、鼓動,才能夠將大多數網民動員起來。因此,作為價值主體的人或者網民是如何在政治動員中展現其社會關系的多個維度,他所投身和傾注的究竟是利益訴求、政治觀點抑或是情感表達,都需要在具體的案例中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洞察,而不能簡單地用“決定論”或者“被動論”的理論框架來武斷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