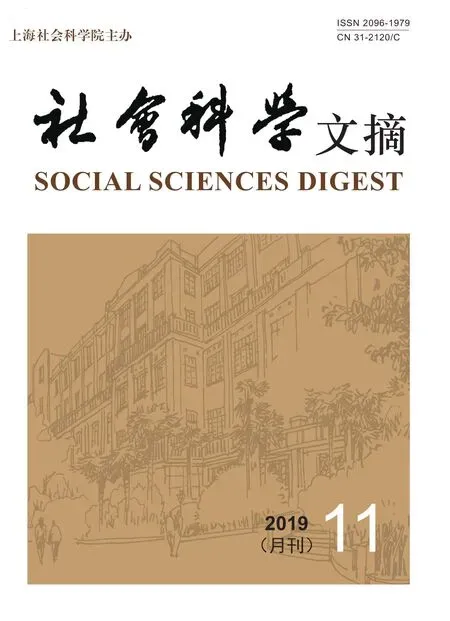“長老的二向箔”與馬克思的“幽靈”
——新世紀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
文/陳舒劼
一
……歌者沒有從倉庫里取二向箔的權限,要向長老申請。
“我需要一塊二向箔,清理用。”歌者對長老說。
“給。”長老立刻給了歌者一塊。
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Ⅲ·死神永生》里,太陽系的二維化坍縮就緣起于這次漫不經心的日常對話。文明層次遠高于人類社會的外星智慧,用二向箔隨手抹去了整個太陽系,幾乎將人類徹底滅絕。相比于《三體》前兩部中呈現出的“面壁計劃”“黑暗森林”“思想鋼印”等構思,歌者與其長老對話的關鍵情節顯得過于平淡,但對于包括《三體》三部曲在內的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來說,它卻是個意味深長的癥候。
歌者與其長老的對話,涉及科幻敘述如何把握社會形態想象與科技能力想象之間的關系問題。結合其他情節所攜帶的信息,讀者能大致從這些描述和“長老”攜帶的身份信息中勾勒出歌者文明的社會形態輪廓:科技超常發達,成員間等級森嚴,權力不來自選舉,有權者能進入下級的思想并任意改變其狀態,存在的基本活動形態為剿滅其他智慧生命。強烈的錯位感,在以宇宙規律作為武器原理的“二向箔”與專制色彩濃烈的“長老”式社會形態之間出現了。若把“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放回人類歷史經驗的河床上,就可以還原出一幅部落長老命令奴隸發射巡航導彈式的圖景。當然,這幅圖景及其所包含的社會形態與科技水平的邏輯關系,從未轉變為人類歷史的真實存在。
歌者文明的社會形態絕非孤證。或許是想象的特權能給予某些寬容,當代科幻小說對“長老的二向箔”式的社會形態想象總是津津樂道。《三體》里同樣遠超人類文明的三體文明,也遵循了這種高等科技與專制社會的配置想象。認同“長老的二向箔”式社會形態想象的,顯然不止劉慈欣的“三體”系列,王晉康的《與吾同在》也是表現標準意義上“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的作品。恩戈星的科技能輕而易舉地降低人類智能并將人類作為家畜馴養,但它的社會形態卻因獨裁、設軍妓、扣人質而散發出濃郁的專制,甚至是法西斯的氣質。恩戈星的高科技文明就孕育于這種社會形態,并長時間維持其科技的高水平狀態。生存危機的無限擴大、以摧毀其他文明為生存常態、對人類科技擁有壓倒性優勢、以獨裁專制為社會形態的底色,《三體》和《與吾同在》在外星文明的社會形態想象上有太多的相似之處。龍智慧的《后土記》讓母系社會與高科技文明相配套。小說對外星文明“MACU”社會形態的描繪因其猜想性質而顯得模糊,但不妨礙作者將母系社會與高科技水平強行縫合,并將有沖突之嫌的細節裸露在外。
“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足以引發追問:以專制為底色的文明可能自主發展出使用“二向箔”這樣的高科技手段嗎?將宇宙規律作為武器使用的文明,是否可能以專制色彩出現?應該怎樣想象未來科技與社會形態的關系?總之,低層級的社會形態能否孕育、發展、維持高層次的科技水平?社會形態及其所發展出的科技文明之間,其相關聯的彈性是否有一定的限度?“長老的二向箔”只是科幻社會形態想象的一種,結合郝景芳的《流浪蒼穹》、何夕的《異域》、龍一的《地球省》、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釗的《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寶樹的《黑暗的終結》和《關于地球的那些往事》以及韓松的《地鐵》《高鐵》和《火星照耀美國》等文本對社會形態的多種描繪,更應該考慮“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所引發的當代科幻小說社會形態想象的整體性問題:當代科幻敘述還展示了哪些社會形態想象圖景?這些想象圖景的認知機制面臨著怎樣的知識挑戰?當代科幻文學的社會形態想象是否已經陷入隱形的終結?這一想象的未來空間和生機又在何處?應當怎樣想象未來的社會形態?
二
上述對當代科幻文學社會形態想象的系列追問,已經隱含著某些前提的默認。這些前提的核心是:無論當代科幻小說展示出怎樣的想象,它都無法逃離人類經驗或隱或現的制約,只能敘述可被敘述之物。
讀者能從晚清以來的中國科幻小說中看到怎樣社會形態想象呢?梁啟超于1902年發表的《新中國未來記》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科幻小說,作者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傾注到這部未竟之作中,希望通過改良實現中國的共和制。老舍的《貓城記》延續了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對國家獨立和民族富強的渴望,小說以反諷的方式表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種種病態。1949年之后,科幻小說的科普性質鮮明,關于國家未來的想象比晚清民國時明亮了許多。在鄭文光的《飛向人馬座》《鯊魚偵察兵》、童恩正的《珊瑚島上的死光》等小說里,國家情懷和革命斗爭意識還聯系緊密,可在葉永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三部曲中,科技主導下的便捷舒適就成為未來生活的底色。“未來市”里的人壽命較長、少有小偷、秉持勞動創造價值的觀念,知識化、城市化乃至趣味化的生活場景替代了社會形態的描摹,嶄新的國家面貌隱約就在眼前。
與國家命運前景緊密相關的想象貫穿于新世紀之前的中國科幻小說之中,當然這種梳理也可以有另外的線索。考慮到科幻小說在構建理想社會形態上與烏托邦小說的相似性,許多科幻小說往往被視為烏托邦敘述的成員。無論是以國家想象還是以烏托邦想象來梳理新世紀之前的中國科幻小說,社會形態在小說文本中扮演的角色,似乎總像高空的氣流之于翱翔的飛禽一般重要卻又隱形。更多的時候,社會形態隱隱綽綽地潛伏在科幻小說想象的字里行間,似乎理所當然地默默配合著想象開展的需求。可是,這并不意味著怎樣擺弄它都是合適的。
三
科技發展的水平和社會形態之間,多數情況下并未呈現直接而清晰可見的關系,毋寧說,兩者之間的關系牢固而復雜。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研究認為,“一定的生產關系是構成一定社會形態的骨骼”,“社會形態除骨骼外,還包括使骨骼有血有肉的上層建筑以及其他一切社會現象”,這“其他一切社會現象”中就包括自然科學在內。雖然機器大工業創造的體系“使得科學在直接生產應用上的本身就成為科學具有決定性和推動作用的著眼點”,可從科學技術發展的動態過程來看,社會形態的作用力極為巨大。“技術從來不是獨立和自主的存在。從技術研發到應用,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即社會權力參與其中為實現自身的意圖展開斗爭的過程”,“技術既非現代化社會問題的‘替罪羊’,亦非解決問題的‘萬靈藥’。真正原因是應用技術背后具體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在任何時空中,組成科學的要素必定反映了那時那刻特定社會文化中的世界觀和政治結構”。問題的關鍵是,科幻小說中科技發展水平和社會形態之間既然有必然的關聯,那這種關聯是否也有特定的限度?
到了必須以《三體》為例回應“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合法性的時候:《三體》既是中國當代科幻的經典之作,也標示著中國當代科幻想象社會形態的水準。“宇宙社會學”等構想占據了《三體》思想體系的核心地位,“長老的二向箔”既能概括《三體》的社會形態想象,也能代表《與吾同在》和《后土記》等一批同樣描繪未來社會形態的小說的想象方式。如果能清理“長老的二向箔”癥候中存在的問題,那么相關思考對其他科幻作品中的社會形態想象也同樣適用。
《三體》的“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實際上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獨裁專制色彩極為濃烈、約處于人類奴隸制社會形態中的歌者文明是否可能出現?人類的歷史經驗表明,盡管社會形態歸結到底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處在同一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地區的國家和民族,社會制度可以迥然不同,而同一社會形態也可以經歷不同發展水平的生產力”,但這并不能推導出人類歷史上的奴隸能使用核武器的結論。包括科技水平在內的生產力與社會形態之間的關聯并非隨意匹配。現代科學技術的大規模、可持續發展,需要相對寬松的社會條件所提供的自由思考、交流便利與經濟回報。這不是連藝術、文學和愛都已經絕跡,對內動不動就要大規模連坐屠殺、對外將所有他者文明視為寇仇的歌者文明和三體文明所能具備的。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經驗,已經無聲而堅定地駁斥關于歌者文明和三體文明的科幻想象。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開放、交流、包容是公認的優選。無論如何,社會形態總是與一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匹配,奴隸制或法西斯制從來沒有孕育出穩定而長久的高科技文明形態,這或許是科幻小說區別于奇幻小說的社會學鐵律之一。
“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甚至在《三體》敘事中也無法自洽。令人好奇的是,在殘暴嚴苛的專制統治下,1379號監聽員關于“美”和“愛”的種種向往是如何產生的呢?如果“美”和“愛”是三體人的本性,那三體文明如何能長時間壓抑這種本性并在壓抑之上發展高科技?自由體制與計劃體制對科技發展的影響是科技思想史上的大命題,深入討論會涉及諸多變量,至少要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特定社會形態甚至是民族文化等。它會像一個旋渦般而將許多可能并不直接相關的問題最終卷入,但如果僅是在與奴隸制和法西斯式社會形態相比較的意義上理解自由的概念,思想自由的確是科技發展的增量。然而,《三體》對科技發展的社會形態依托,又始終在自由與專制之間搖擺不定。
四
“長老的二向箔”式的社會想象雖然典型,但不可能覆蓋所有的新世紀以來的科幻小說社會想象。郝景芳的《流浪蒼穹》、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釗的《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以及韓松的《地鐵》,都有自己的社會形態想象的側重點。
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已經深嵌當今生活的科技技術,其未來發展在《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對社會形態的想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智能計算機的語法成為這些小說社會形態的深層結構和內在主宰。郝景芳的《流浪蒼穹》中,未來社會形態的缺陷被分置于地球和火星之上——這暗示著某種價值選擇的猶疑。大體而言,火星的人類社會是周密計劃與部署的產物,地球的社會形態則顯得寬松而雜亂。《流浪蒼穹》留給讀者的啟示是,與其在地球和火星兩種社會形態中擇一而從,不如思考如何融合兩者的優長而形成新的社會形態,或至少應該避免出現兩者負面因素融匯的惡果。這種最壞的可能似乎出現在了韓松的筆下。自由總是被濫用而充滿癲狂的氣息,計劃總是殘缺且陰暗詭譎,韓松在地鐵或高鐵中建構出的社會形態,有著獨特的詭異氣氛。韓松刻意營造這種似是而非以刺激閱讀過程中的不適感,目的或許是顯影科技發展所可能帶來的身心壓迫,對人類文明走向和未來社會形態保留某種必要的警惕。
檢視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會發現眾多想象之間的差異,也必然感受到對社會形態進行科幻想象的難度和限度。社會形態想象相對于科技想象,其難度要高出不止一個層級。成功的社會形態想象意味著對整體結構、內在元素及其關系的恰當理解和處置,若在此之上還要進行想象的科幻創新,其難度無疑遠超具體的、功能性的科技想象。
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想象社會形態的難度大致有兩種表現。一是如“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雖大體較為詳細地呈現了未來社會形態的面目,但這種未來社會形態難以承受細致的追問。另外,《三體》所提出“宇宙社會學”等囊括而不止于社會形態想象的概念,同樣無法避免不同學科話語的質疑。想象社會形態的難度,還直接表現在敘述社會形態想象的篇幅上——較為詳細地呈現對于未來社會形態的想象本身就已非易事。許多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需要批評者的概括和提煉,差別只在于提煉的程度不同。如《三體》《與吾同在》所含有的社會形態信息量,就比《黑暗的終結》《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要豐富很多。大多數科幻小說若有直接涉及社會形態的想象話語,也常常語焉不詳。
科幻小說想象社會形態的難處,最終都匯流朝向想象的無力與終結。科幻想象中的社會形態無法擺脫既有的人類經驗和理念的隱性掌控,包括今天在內的所有歷史,已經成為決定未來的過去。詹姆遜在《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指出:“我們現在必須回到科幻小說和未來歷史的關系上,并將對這種體裁的陳舊描述顛倒過來:關于它的正確描述實際上應該是,作為一種敘事的方式和知識的形式,它并不能使未來具有生命力,哪怕是在想象中。相反,它最深層的功能是一再地證明和渲染,盡管我們具有表面上看起來很充分的表現,但實際上對于想象和象征化地描述未來我們還是無能為力。”詹姆遜的論述中,飽含著對科幻想象無力開拓出他性和差異性的不甘,潛伏著對跳出泥潭、沖破極限的渴望。無論如何體恤科幻小說想象未來社會形態的難度,都必須意識到這種想象的風險:如果科幻想象不能提供未來社會形態的更多合理性可能,那么想象的終結就已經降臨。
五
“想象的終結”,意味著科幻小說沒有能力從現今的政治經濟體系中推演出未來的圖景,所有的想象都是歷史中社會形態的改裝。然而,我們面對的現實是歷史并未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科幻小說要如何走出想象的困境?
迄今為止,馬克思所闡明的社會發展規律依然有效。對熱衷討論未來人類社會發展前景的科幻小說而言,離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形態想象可能無所適從;要科學地呈現未來的社會形態,就無法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想象的錯位、無力與終結等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中社會形態想象所出現的種種癥候,都出于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診斷。
按照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一般理解,共產主義出現在資本主義之后,資本主義孕育著新社會形態的因素。然而,共產主義理論沒有提供未來社會形態建構的清晰指南,小說家要做的遠不止于空洞地復述理論概念,或簡單地描繪某個科技發明的細節。當今時代發展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當年的想象,馬克思所希望的是其后繼者接力向前,而非終老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內的尋章摘句。未來的社會形態沒有毫發畢現的理論面貌,清晰甚至意味著風險,小說家進行小說創作不等同于有能力完成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敘事。要想敘述一種并非具體形態或周密計劃的未來社會,馬克思的啟示是保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批判的思想氣質。有時候,不滿和批判就孕育著新質。科學的技術形態日新月異,但若馬克思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依然是不刊之論,那么科幻敘事就應該保持思想的緊張和批判的銳氣,保持科技細節建構之上的、對未來社會形態的好奇。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路徑上尋找科幻小說想象未來社會形態的可能,是未來科幻小說文學實踐所應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