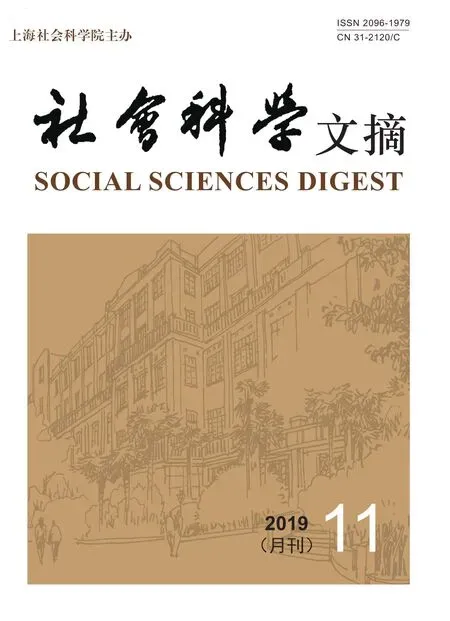明朝公主和親馬六甲:馬來西亞華人文學書寫、文化記憶及身份認同
文/毛睿
明朝公主和親馬六甲的事跡未見于中國的任何一本史籍,它卻在馬來西亞家喻戶曉。故事講述的是明朝的漢麗寶公主帶著五百名中國官家小姐前往馬六甲和親。漢麗寶公主嫁給馬六甲蘇丹芒速沙(Sultan Mansur Shah)為妻,五百名官家小姐也和當地土著通婚,他們的后代都成了馬六甲子民。蘇丹芒速沙為漢麗寶公主在中國山(Bukit Cina)修筑了輝煌的宮殿,并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據馬來語學者孔遠志的記載,南洋地區甚至還有鄭和護送漢麗寶公主遠嫁馬六甲國王的說法。因為這個和親故事本身具有中馬兩國親善、馬來西亞華巫兩族親善的意義,所以漢麗寶和親故事時常會出現在馬來西亞各種官方和民間的敘述中,以漢麗寶故事為核心的藝術作品數量相當可觀。
漢麗寶的故事在南洋地區的影響巨大,可與之相關的學術研究卻始終駐足不前。20世紀40年代,南洋歷史學者張禮千就對漢麗寶故事的歷史真實性提出懷疑。他認為漢麗寶的故事史料不足征,不過是道聽途說而已。東南亞史學者基本上認同張禮千的觀點。除了歷史研究,也有一部分學者嘗試從民間文學的角度來詮釋漢麗寶故事:中國學者大都認為故事表達了馬來西亞華人對華巫兩族親善的期望。東南亞本土的學者則認為這個故事反映了馬來西亞土生華人對于自我身份的想象。可是,前人的研究都忽略了一個客觀事實:漢麗寶故事并不僅是一個文本。對于馬來西亞華人而言,它是一段累積形成的文化記憶。漢麗寶故事早已超越了歷史、文學的層面,它是能夠增強集體身份認同的文化記憶,是加強族際溝通的文化符號。本文將以漢麗寶故事為個案,梳理漢麗寶故事由民間傳說上升到文化記憶的過程,并探究這個過程背后馬來西亞華人是如何去構建本族群文化和集體身份認同的。
從民間故事到文化記憶
關于漢麗寶故事的起源,大多數學者都會將其追溯到成書于1621年的《馬來紀年》。這種先入為主的觀點,直接影響了學者對漢麗寶故事的深入研究。實際上,《馬來紀年》中的漢麗寶故事并不可能直接對華人產生影響。在華人族群中,漢麗寶故事的流傳有另外一種傳統:它經歷了從民間故事到文學文本,再由文學文本上升到文化記憶的過程。
馬來學者研究發現,在《馬來紀年》的成書過程中采錄了大量的民間傳說。因此在《馬來紀年》之前,漢麗寶故事很可能早就以民間傳說的形態在流傳了。此書自1621年由爪夷文(Jawi)寫就后,一直到19世紀前期,它都是以手鈔本的形態藏于馬來皇宮之內。1820年萊頓(John Leyden)將其翻譯成英文并在英國出版。20世紀50年代,許云樵根據萊頓的英譯本將《馬來紀年》轉譯成中文。可以說,在許云樵的譯本出現之前,由于語言文化的隔閡,華人基本上不可能接觸到《馬來紀年》一書。漢麗寶的故事在華人社會主要以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形態存在。
據歌劇《漢麗寶》作者白垚的回憶:1958年他前往馬六甲出差,在游覽古城時,同行給自己講了漢麗寶公主的故事。這是白垚第一次知道漢麗寶的傳說。之后,他根據華人社會中流傳的漢麗寶故事,以及《馬來紀年》的記載,創作歌劇《漢麗寶》。劇本于1969年發表在馬來西亞最重要的華文文藝刊物《蕉風》上。1971年11月20日,歌劇《漢麗寶》在吉隆坡首演,首演9天。此后,該劇多次在馬來西亞及臺灣巡回演出。
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三保山事件”,又讓漢麗寶故事從一個華人社會家喻戶的文學文本已經變成了一種文化記憶。根據揚·阿斯曼的理論,文化記憶與普通的神話傳說、歷史書寫或者文學文本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文化記憶擁有者強大的產生和鞏固集體認同的潛力,它的內容及意義是能夠對某一個族群的心理產生直接的影響。漢麗寶故事在“三保山事件”這次政治事件中就表現出了強大的集體凝聚力。
“三保山事件”起于1983年底,持續發酵了2年左右的時間。這是馬來西亞建國后影響范圍極大的一次政治事件。事件起因于1983年10月5日馬六甲州首席部長致函青云亭機構表示有意鏟平三保山,并將三保山作為商業用地進行開發。三保山是華人在馬來西亞歷史最悠久的墳山,該地由青云亭機構管理。馬六甲州政府想要進行商業化開發,這本來是政府與青云亭機構之間的矛盾。出人意料的是,這件土地開發預案很快就演變成全國性的族群矛盾。在馬來西亞華人看來,對三保山的開發就是主體族群想要消滅華人在大馬的歷史根基。
從1983年至1985年,為了抵制甲州政府對三保山的開發,華人社會不斷地通過傳媒為三保山賦意。漢麗寶故事象征了華巫友好,三保山成為漢麗寶故事的實體象征,如果政府意圖鏟平三保山,那就是在消滅華巫友好的證據。此時的漢麗寶故事成為凝聚華人力量的旗幟,它有效地激起馬來西亞華人對自己祖先光輝歷史的遐想,激發華人對破壞兩族友誼之行徑的同仇敵愾。
仔細分析漢麗寶故事由民間傳說生成為文化記憶的過程,可以發現其中有三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文學文本的創作、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的需求、馬來西亞華人精英的宣揚。
歌劇《漢麗寶》與漢麗寶記憶
歌劇《漢麗寶》為“漢麗寶記憶”創造了一個宏大的意義世界。它讓漢麗寶從一個遙遠的傳說,變成真實可感的昨日之事,從而激發了馬來西亞華人對本族群歷史的無限遐想和自我身份的體認。
1.真實歷史時空的構建
神話傳說在中華文化中一直處于邊緣地位,它很早就被歷史傳記所取代。長久的史傳傳統讓炎黃子孫養成了用歷史理性來審視世界的習慣。因此,即使像《馬來紀年》這種被馬來民族奉為歷史經典的文本,在華人眼中亦是滿紙荒唐言。作為一種記憶,它可能與現實存在出入,但在當事人認知中卻必須是絕對的真實。歌劇《漢麗寶》就為漢麗寶故事構建了一套真實的歷史時空。
歌劇讓漢麗寶和親故事完全融入中國的歷史敘事之中,為漢麗寶在中國清晰的歷史序列中找到一個明確的坐標。劇中漢麗寶被設置成化帝的妹妹。時間、地點和人物身份這些敘事要素的歷史真實化,讓漢麗寶公主褪去了傳奇的色彩。大量華人熟知的歷史細節在劇作中不停地出現。這些都使得漢麗寶故事有著巨大的歷史真實感。這是漢麗寶故事能夠成為記憶的第一重可能性。
2.豐滿可感的人物塑造
歌劇《漢麗寶》塑造了一個具有馬來西亞華人屬性的漢麗寶公主。《馬來紀年》中的漢麗寶公主不過是蘇丹芒速沙眾多妻子中的一個。對于華人而言,這樣的漢麗寶是他者。經過白垚的創作加工,漢麗寶公主這個人物脫胎換骨:她的身份不再只是中國公主或者蘇丹王妃,她是一個下南洋的華人,是無數下南洋謀生的馬來西亞華人的縮影。正是漢麗寶公主身上的這種馬來西亞華人屬性,讓其與每個華人的個體記憶產生聯結,甚至對個體記憶進行替換。這是歌劇文本為漢麗寶記憶的形成提供的第二重可能性。
3.強情節的設置
由漢麗寶故事改編的文學作品在馬來西亞數量并不少,但這些文本都是以漢麗寶和蘇丹結為夫婦繁衍后代為結局。只有歌劇《漢麗寶》創造性地改變了故事的結尾。作者在歌劇最后一幕加入漢麗寶為芒速沙而死的情節。歌劇在情感最高潮處戛然而止,這也使劇情能夠在觀劇結束之后更長久地停留在受眾的腦海中。漢麗寶之死又體現了她對中華文化中忠義貞節的堅守。漢麗寶公主的死亡在華人受眾的心目中完成了情感和道德的雙重偉岸。這樣的結尾有著強大的象征意義和感染力,客觀上延長了受眾對劇本的記憶。
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的迫切性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馬來西亞華人迫切的族群身份認同需求,也是漢麗寶故事能夠成為文化記憶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馬來西亞學者何國忠所說:“華人雖然和中國斷絕了政治關系,但是他們知道華人的身份是靠文化的傳承才可以維持的。”20世紀60年代后期,馬來西亞主體族群從國家層面對少數族群實施了一系列文化同化政策,其目的是消滅包括華人在內的少數族群的文化屬性。對此,包括華人在內的少數族群,他們要么構建本族群文化認同去對抗主體族群的文化同化,要么將自己融入到主體族群的文化之中,喪失自身的族群身份。
1957年,馬來亞聯邦宣布獨立以后,華巫兩族在經歷了短暫的蜜月期。不久,兩族在文化方面的沖突凸顯出來。比如官方層面上,主題族群提議用舞虎取代舞獅,招牌上馬來語與中文字體大小比例有著明確的要求,將吉隆坡的開埠者葉亞來從官方歷史教科書中去除,尤其是關閉英校強迫華校改制等。這種文化同化的政策在1971年的“國家文化大會”達到頂峰。“國家文化大會”提出了文化“三大原則”,即:(1)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區原有文化為基礎;(2)其他適當和恰當的文化元素可以成為國家文化之元素;(3)回教是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元素。同時強調,唯有在第一及第三原則被接受之后才考慮接受第二原則。
這次會議的成果代表了馬來西亞政府之后的文化政策走向。從三大原則的內容來看,作為華人族群屬性的中華文化將被邊緣化,并且是在發展伊斯蘭文化的過程中可以被犧牲掉的。
華人面對主體族群的文化政策,反應相當復雜。一方面,他們拒絕文化同化,堅持本族群文化的態度是十分清晰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本族群文化的認知并不清晰。這直接導致華人在構建本族文化時往往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
早在馬來亞建國之前,生活在馬來亞的華人對本族群的獨立性就有著高度的認同。不過馬來亞建國后,華人在國家認同層面上普遍接受了自己是馬來亞的公民這一身份。可是早期中國流亡南洋的革命黨人帶去的民族主義思潮又讓他們拒絕融入主體族群,始終強調自己的華人身份。于是,中華文化成了他們緊抓不放的區別他族的身份屬性。然而,華人在建構本族群的核心文化、增強族群內部的文化向心力上的努力又是盲目的。華人在這方面做過諸多嘗試,不過收效甚微。往往是一小部分華人在“狂歡”,而大部分人“視而不見”。其根本原因是大多數華人并不了解本族群的文化土壤。事實上,馬來西亞華人假想出了一個所謂的“中華文化”的容器,于是所有來自中國的東西,都被放入這個容器之中:多如牛毛的民間信仰,來自華南地區的民風民俗,宗族文化推崇的忠貞、禮義、孝悌,等等。馬來西亞華人基本上是由華南沿海幾個省的移民構成。伴隨著大規模移民,他們對外輸出的文化核心是民間信仰、血源性及地緣性的宗親鄉團相融合的文化。直到現在,馬來西亞華人活動的策劃者和組織者還是各種民間宗教團體、商會、宗親鄉團組織,文化活動也不外乎此。于是形形色色的團體各自搬演,你方唱罷我登場,各自為政。這才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活動多半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的根本性原因。
面對主體族群以伊斯蘭信仰為核心的文化同化,華人需要形成的是明確、強有力的文化認同。各自為政的文化生態,顯然是以卵擊石。要形成文化認同,就需要構建強有力的文化記憶。這種文化記憶必須是在整個華人族群中取到最大公約數的記憶。毫無疑問,最符合這個條件的莫過于華人在南洋的記憶了。南洋記憶對整個馬來西亞華人族群而言是具有超越性的。它打破了民間信仰、血緣、地緣等文化隔閡,和每個華人的個體記憶相呼應。漢麗寶的故事經歷過藝術加工之后,正好具備了提供這樣一種記憶的能力。
馬來西亞華人政治精英的文化選擇
歌劇創作使得漢麗寶故事成為了一個豐富的意義系統。馬來西亞華人為了對抗主體族群的文化同化,迫切需要通過文化記憶來構建文化認同。此二者都只是必要條件,使得漢麗寶故事能夠成為文化記憶的充分條件是馬來西亞華人精英的主動選擇。具體來說,能夠被塑造成為文化記憶的素材眾多:口述、文字、圖片、建筑物等。其中的文字媒介又有著多種符號系統,例如編年史、法律文本、宗教文字、神話故事等。馬來西亞華人精英主動選擇了漢麗寶這個素材。
在“三保山事件”順利解決之后,華人精英憑借在族群中擁有的話語權,仍然在進一步強化漢麗寶記憶。1991年將歌劇《漢麗寶》改編成舞劇,這個事件反映出了華人精英的良苦用心。這一次由歌劇改編成舞劇的文化創作,由馬來西亞影響力最大的三個全國性華團(中華大會堂、董總、教總)主持,由全國華團文化咨詢委員會具體落實。舞劇在馬來西亞全國巡回演出時,又受到了全國15個華團的鼎力支持。就在舞劇《漢麗寶》上演期間,馬來西亞著名歷史學者李業霖也在報刊上發聲:漢麗寶是明英宗或憲宗時人,本姓朱,只是不見于正史記載。舞劇《漢麗寶》的改編背后是華人精英的野心:他們企圖將漢麗寶故事歷史化,使其能夠在華人的文化記憶中停留的時間更久,其影響力和凝聚力變得更強。除此之外,華文報刊、書籍頻繁地刊載這個故事;華人精英在公開場合反復言說漢麗寶故事背后華巫親善的大義;這些都是在反復強化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漢麗寶記憶。
而華人精英之所以會選擇將漢麗寶的故事變成文化記憶,是因為馬來西亞華人歷史書寫存在著極大的缺陷。首先,在東南亞的自然環境中的史料、文物較難保存,想要書寫歷史,但史料不足征。其次,據實書寫的近代史,往往是缺乏傳奇性和典型性的。以“三保山事件”為例,漢麗寶故事比之真實的三保山歷史更加符號化、抽象化,同時也更具有文化意義和族群凝聚力的。
余論
縱觀漢麗寶故事由傳說到記憶的過程,有兩個問題值得深思:
其一,文學文本與文化記憶、文化認同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研究集體文本的書寫方式、傳播路徑以及接受情況,是了解一個族群集體記憶、文化認同、身份認同很好的路徑。
其二,以馬來西亞華人的漢麗寶記憶為出發點,可以幫助思考海外華人構建文化認同、維護族群身份。海外華人在面對族群身份問題時,往往都會假想一種中華記憶,以此來區分自我和他者。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華人很難在中華文化這個空洞概念之下形成強有力的文化認同。過分強調中華文化的身份屬性,反而更多地會造成了華人和本土族群之間的隔閡。因此,海外華人在構建本族群的集體記憶、身份認同時,既應該堅持中華屬性,但也不可忽略華人在當地的生存狀態、文化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