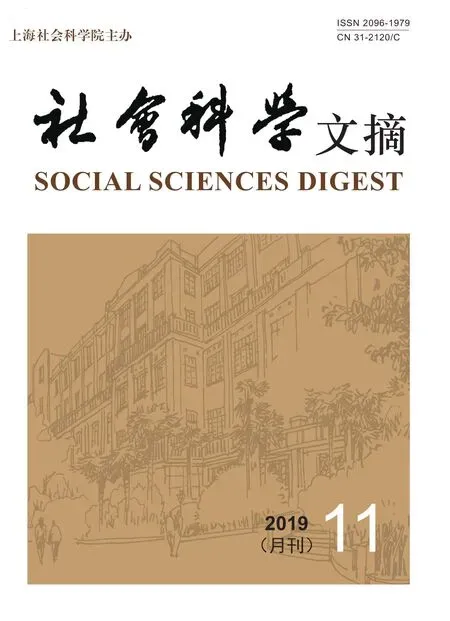2008—2018全球智庫發展變遷及對中國媒體智庫的啟示
文/韋路 李佳瑞
隨著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不斷推進以及媒體轉型的日益深化,媒體智庫研究作為媒體轉型的一個可能方向日益受到業界與學界的共同關注。然而,在媒體智庫化發展和智庫媒體化呼聲越來越高的今天,媒體智庫的表現卻差強人意。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18全球智庫指數報告》顯示,全世界一流的177家智庫中,沒有一家是媒體智庫。雖然當前國內外不乏有關媒體智庫的優秀實踐樣本和理論研究,然而“法乎其上,則得其中;法乎其中,則得其下”。既然在全球頂級智庫中暫無媒體智庫的席位,而且有學者認為相較于智庫,媒體主要發揮的是中介作用,那么本文就試圖暫時放下對于媒體智庫中媒體身份的強調,重新回歸對智庫特別是全球頂級智庫的關注,從一個側面為中國媒體智庫的未來發展提供參考。
研究方法與路徑
“智庫是否真正起到作用”“如何測量智庫的影響力”一直為智庫研究者們所追問。各國研究者在建立各種影響力指標及評價體系的同時,收集了大量智庫的數據,這些數據為我們了解全球智庫發展提供了可能。在本文中,我們以當前智庫評價體系中較為權威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和公民社會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簡稱:TTCSP)在2008—2018年間發布的全球媒體智庫指數報告作為篩選依據,統計該報告2008—2018年的全球智庫排名情況,采用內容分析和文本挖掘的方法,分析全球Top20智庫的表現。首先,我們以該報告為數據來源,對11年來全球各區域的智庫數量,來源地區,以及全球排名Top20的智庫進行統計。其次,我們檢索出歷年全球Top20智庫所對應的官網,并對這些官方網站的機構介紹頁文本及報告進行采集,并通過詞頻分析和內容分析識別其主要研究議題及研究方法。最后,我們從全球Top20智庫在產品、服務、經營管理等方面的經驗出發,結合傳媒智庫特點,進行綜合案例分析。
全球智庫的近年概況
(一)智庫數量穩步增長,非歐美地區占比提升
從智庫數量來看,全球七大地區可被分為四大梯隊:一是數量上領先的歐洲、北美地區;二是快速發展的亞洲地區;三是穩步發展的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及中亞北非地區;四是絕對數量較少且發展穩定的大洋洲地區。其中,歐洲智庫在2017年后從數量上超過了北美地區,成為全球智庫數量最多的地區;亞洲在2008年及2016年前后各有一次快速發展的階段,主要表現為中國和印度的智庫數量快速增長;中南美洲在2016年后也有一次較為明顯的增長,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國增長明顯。在智庫總量總體增加的情況下,歐美智庫數量及占比雖然仍居全球前列,但是總占比在下滑,亞洲、中南美洲等地區在智庫數量及占比方面提升迅速。這一變化,一方面得益于亞洲及拉丁美洲等新興市場國家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需求,另一方面可能同這些國家加大了對智庫研究方面的政策支持以及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密不可分。
(二)智庫發展不平衡,Top20大多來自發達國家
通過分析2008—2018年度全球Top20智庫的國別歸屬的分布及頻次情況,我們發現,美國(113)、英國(34)、德國(23)、比利時(17)等是頂級智庫出現頻次較高的國家。日本(7)、瑞典(7)、法國(6)、巴西(5)、加拿大(5)、中國(2)及韓國(2)也在近11年全球Top20智庫分布中有所展露。總的來說,頂級智庫(曾入選全球Top20的智庫)在全球范圍內分布不均,全球多數國家的智庫從未出現在過去11年的全球Top20榜單中;西方國家在過去11年間,在Top20頂級智庫的分布范圍及強度占據絕對優勢;除巴西、中國外,來自其他非西方國家的頂級智庫則相對較少。
(三)美英智庫在頂級智庫中表現突出
在近10年的全球智庫報告Top20智庫榜單中,至少出現一次的智庫共有34家。具體來看,11家連續10年(2009—2018年)出現在Top20榜單中的智庫有9家來自美國,2家來自英國。這說明,美英特別是美國智庫在全球頂級智庫的表現中位居前列,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更是連續10年位居首位。在美英之外,位列Top20榜單的智庫亦大多來自發達國家,僅有巴西的Fundacao Getulio Vargas(FGV)和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來自發展中國家。前者于2014—2018年期間入圍Top20,后者則曾在2012年和2013年入圍Top20。
頂級智庫的關注領域與研究方法
(一)頂級智庫機構定位的三大特征
通過對曾入選2009—2018年度全球Top20智庫的34家智庫官網中涉及機構介紹的“關于”(About Us)頁面的文本詞頻分析,我們發現,頂級智庫的機構介紹呈現出三大特征:一是關注議題所涉及的空間層次豐富,這些智庫關注著從國際(International 33)、全球(Global 31)、世界(World 23)到地區(Regions 25)和國家(Nation 20)等多個地緣層次的議題;二是關鍵研究領域集中,重點對于經濟貿易(Economy 25、Economic 21、Market 19、Trade 18)、政府治理(Governance 24)、社會與公民(Society 24、Civil 22)等領域進行探討;三是聚焦問題廣泛,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之外,還對于安全(Secure 19)、防衛(Defense 19)、福利(Welfare 18)、教育(Education 17)及權利(Rights 16)自由(Freedom 16)等諸方面有較多的關注。結合詞頻,我們重新回到文本中,發現上述關注的議題和領域在其智庫機構描述的話語中表現為對各類政策(Policy 41)和問題(Issue 35)的研究。
(二)頂級智庫機構關注的四大議題
通過對34份智庫介紹中的研究議題(問題)逐一進行編碼,繼而采用內容分析,并結合具體的詞頻分析,我們對不同智庫間共有的高頻詞及共同議題進行了聚類,并根據關注領域和關注重點,區分了四大議題:一是國家性議題,關注的主題是與國家相關的政策與問題,其中經濟政策、公共政策、外交關系、國防安全、國家治理等是該類議題聚焦的重點;二是地區性議題,關注的主題是國際地區性的發展與沖突問題,其中地緣政治、區域經貿發展是該類議題關注的焦點;三是國際性議題,關注的主題是全球性的國家間共同面對的問題,其中全球化、國際事務、軍備裁軍、核武等問題是該類議題側重之處;四是專門性議題,這類議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包括腐敗問題、環境問題、能源問題、人權問題等。
大體而言,34家智庫呈現出對綜合性議題和專門性議題關注分野的態勢。納入統計的34家智庫中,有17家智庫涉及的議題在2個及以上,余下17家智庫圍繞專門性的議題進行研究。在綜合排名前10的頂級智庫中,有9家關注的議題都大于2個,甚至有7家關注的議題多于3個,而聚焦專門性議題的智庫則排名相對靠后。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綜合性智庫和專門性智庫都是智庫發展的重要定位和方向;二是相對于關注專門性議題的智庫,關注綜合性議題的智庫在整體表現上更加突出,影響力更大。這或許同綜合性議題能夠得到更廣泛的關注等因素有關。
(三)頂級智庫機構常用的研究方法
在了解頂級智庫所關注的議題及問題后,為了更為細致地反映全球頂級智庫是如何圍繞相關問題開展研究的,我們對其研究成果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我們選取34個智庫官網中公布的3份最新文檔(總計102份文檔),進行研究方法的統計,并按照常用的研究方法對其進行分類。
總的來看,大部分智庫出版物(含電子版)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根據問題類型靈活多變,過程規范,使用了至少一種以上的研究方法,以實證的研究方法為主導,主要是訪問座談和問卷調查。具體來說,在公共政策、經濟發展等問題的研究較多采用了多種方法結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研究多邊關系對于地區政經政策影響時,問卷調查和訪談是比較常用的方法,同時還會結合比較分析;在涉及國際、地區或者國家某類問題的印象、評價(如腐敗問題)時,多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輔以座談訪問;涉及歷史問題的研究時(如冷戰國際史),多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此外,也有一小部分文檔未說明研究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他方法”中,還有一些智庫試圖運用大數據的研究方法和數據可視化工具輔助其觀點呈現,這些智庫認為上述方法將會是未來重要的研究方法。
頂級智庫的發展經驗與啟示
(一)把握時代脈搏,保持寬廣視野
視野大小影響了思想產品的格局,也影響著智庫的發展。作為智囊團的智庫絕不能脫離歷史與時代而存在,與之相反的是,智庫應該擁有寬廣的視野,關注重點領域發展,緊隨時代,甚至超前于時代。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等之所以成為國際頂級智庫就在于其能把握時代脈搏,用宏大的視野來審視世界,發現問題。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在其涉及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傳統議題領域外,它還發布了大量緊隨時代發展的相關報告。例如,該學會于2018年4月24日發布《人工智能改變世界》報告;同年6月23日,該學會又發布了一項有關人類對機器人態度的報告,該報告稱多數受訪者并不太愿意接受機器人的幫助,并發現“人們很難接受涉及情感與社交的機器人產品”。這些報告有助于人們反思機器人發展的現狀,并能夠幫助政府、企業以及社會提前重視這些可能出現的問題。
我們認為,媒體智庫一方面要積極發揮媒體廣泛接受新信息的渠道優勢,向全球頂級智庫那樣保持寬廣的視野;另一方面可以借鑒頂級智庫及時發布相關報告的經驗,關注時代問題,進行深度剖析,提供多角度的思考。
(二)優化人員配置,健全人才管理
生產有洞見的思想產品需要人才,實現資政諫言、擴大智庫影響力也需要人才。正所謂建“庫”易、蓄“智”難,智庫運營歸根到底還是人才運營。從全球Top20的頂級智庫中,我們發現良好的人員流動機制、多元的人才合作途徑、高效的輔助人員協助是促進智庫不斷創新的三大重要因素。美國智庫所形成的“旋轉門”制度已廣受國內外研究人員的關注和剖析,雖然“旋轉門”可能會帶來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沖突,但總的來看,這一機制利大于弊。與此同時,以項目為基本結構,將學科知識與研究課題相結合,從而形成矩陣研究機制。這一機制為多國家、多學科、多渠道的人才合作提供了途徑,也為智庫的創新發展助力。此外,高效協作的行政人員和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實習人員,為智庫在人才儲備及基礎研究上提供了可靠支持。
從頂級智庫反觀我國的媒體智庫,雖然媒體人具有傳播資源優勢,但是媒體智庫媒體人才有余而研究人才不足,這實際上制約了智庫服務能力。此外,部分媒體智庫在人才管理、編制薪酬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問題,影響了智庫運轉的效率。因此,媒體智庫要明確自己的優勢和劣勢,揚長避短,以多渠道引進多元人才,通過“發揮傳媒機構采編人員的調研優勢”等方式,結合實際情況完善自身的人才管理體制。
(三)堅持科學方法,確保研究質量
在本文納入統計的102項Top20智庫的出版物中,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與手段。大部分出版物使用了不少于一種的研究方法,這是生產有價值思想的方法保障,也是形成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環節。以連續10年入選全球Top20智庫的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為例,如學者安淑新所觀察的那樣:蘭德公司制定了反映研究質量的“高質量研究標準”和反映蘭德特征的“蘭德特殊研究標準”,并以此進行內部及外部考核。在嚴格的內部考核之外,該智庫還邀請了來自其他部門以及蘭德公司以外的專業人士作為外部考核人員,從而保證研究質量。頂級智庫對于科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質量的追求可見一斑。
就媒體智庫而言,堅持科學的研究方法,產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是十分重要的。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產出高質量的智庫產品,是媒體智庫獲得認可的重要保障,也是智庫核心競爭力所在。由于一部分媒體智庫的從業者來自新聞采編一線,雖然真實性和準確性是新聞的重要特性,但是在實踐中難免有從業者將時效性放在了更為突出的位置,這樣的工作習慣可能會影響其在媒體智庫的工作狀態。因此,媒體智庫相比于一般智庫在智庫產品和服務上更應該穩扎穩打,在追逐熱點和研究重點間做好平衡,在方法選取上做好權衡,在成果產出上嚴把質量,這樣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四)樹立“品牌”形象,創新成果轉化
智庫的最終目標不僅僅在于“思想生產”,更在于讓其產品與服務輔助決策,產生影響。在對Top20的頂級智庫分析中,我們發現,這些智庫的影響力不是來源于某一次優質的產品或服務,而是通過持續深耕某一領域,輸出高質量的、可靠的“思想產品與服務”而實現的,并由此樹立自身的“品牌”形象。在“品牌”形象樹立后,這些智庫還會通過各類方式促成其成果轉化。這些方式包括積極接近政府、媒體、社會組織及廣大公眾,以便在提升自身曝光度的同時獲得資助;包括舉辦各類國際性、區域性、行業性的學術會議、研討會等活動;還包括運營期刊雜志(含電子版)、網站及各類新媒體平臺賬號等。這些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活動和出版物(如布魯金斯學會的《布魯金斯評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借助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實現了線上線下多次傳播,不但構成了其“品牌”下種類多樣的產品與服務,更為增強智庫的國內外影響力和話語權奠定了基礎。此外,頂級智庫還會通過設立研究中心、子公司或專門部門等方式積極拓展海外合作以擴大國際影響力。
在“品牌”樹立方面,媒體智庫其實擁有一定優勢。一方面,媒體對于新技術、新業態的成熟掌控與運用有助于實現智庫產品的多樣化;另一方面,媒體的傳播優勢則能助力媒體智庫的品牌樹立。然而,在成果轉化上,媒體智庫由于業務模式模糊,可能會形成成果轉化困難的局面。正如劉培所提到的,如果媒體智庫不能在運營模式上打通“產學研”的一體化發展體系,構建成果推介機制和平臺,必然會影響智庫產品的服務能力和盈利目標。對此,頂級智庫則沒有太多顧慮。如蘭德公司與美國政府諸多部門簽訂了服務合同,擁有數千萬的合同數額。其他的頂級智庫則擁有包括政府、基金會、企業及個人在內的各類資助。因而,媒體智庫若能憑借優質的智庫產品和口碑拓展資金來源,將能更加有效地實現成果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