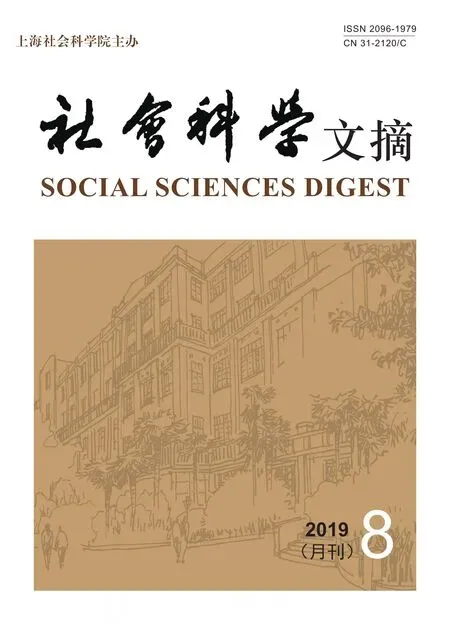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三權分置”中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功能定位
文/趙紅梅
“三權分置”中集體土地所有權功能定位的基本思路
(一)做虛論
本文對該論的總體概括是:在農地“三權分置”中,做虛集體土地所有權+做實土地承包經營權+做實土地經營權。
1.做虛集體土地所有權。我國法學界大多數研究者基于“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制度存在缺陷”論述做虛集體土地所有權實屬一種無奈的制度選擇。有不少研究者進一步對做虛集體土地所有權(主要表現為弱化其限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處分權能)提出了具體的立法建議。如陳小君指出:“現行《農村土地承包法》有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須經發包人同意的規定,明顯忽視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屬性,抬高了放活農地經營權的制度成本,物權法修訂時應予以糾正。”前述意見有些具有一定合理性,也有限度地被修正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納入了一部分。
2.做實土地承包經營權。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塑造為權能充分、內容飽滿的用益物權甚至自物權,以使其在三權中居于核心地位。即不僅僅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身份性,更強調其主要具有用益物權的財產性,并借此派生出土地經營權,故可謂做實土地承包經營權。但其實,我國“兩權分置”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因具有身份性,離民法理想狀態下的可自由處分的真正的用益物權尚有不小差距,爭議較大的問題還包括限制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法律規定。故主張做實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研究者,也有部分主張先行縮小此差距,以為進一步做實借此派生出的土地經營權奠定扎實基礎。修正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較之前述修正前的相關規定,使土地承包經營權離民法理想狀態下的可自由處分的真正的用益物權的差距有一定縮小,但沒有明顯縮小。
其實,早在將近20年前,我國就有研究不滿足于僅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塑造為獨立用益物權。如葉華明確指出:“從產權的一般理論看,承包權具有所有權性質。”李鳳章認為:對集體土地所有權“弱權利”“反權利”“空權利”最根本的消解,正是強化土地承包經營權等農戶手上的土地權利。當土地承包經營權等土地權利被強化到無期限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流轉,并且在用途上獲得了法律限制之外的所有使用權利,其就成了類似于大陸法系所有權的權利。孫憲忠則沿著這一思路將做實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理論推向了極致。他認為,不是農民家庭或者個人的權利來源于集體,恰恰相反,而是集體的權利來源于農民家庭或者個人。實際上,我們應該承認農民集體是一個個具體的單一農民共同的資格形成的,農民本身享有最終所有權。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恰恰是他們行使自身權利的一種方式。所以農民家庭或者個人對于土地的權利,本質上是一種“自物權”。修正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沒有受到該理論的影響。
3.做實土地經營權。我國法學界針對“三權分置”中土地經營權基本屬性的研究,民法學者貢獻了一些法律技術方面(不涉及價值判斷)的智慧。代表性學說包括“用益物權”說、“債權”說,“債權”說又派生出“租賃權物權化”說、“特殊效力債權”說。就滿足做實土地經營權的要求而言,毫無疑問“用益物權”說和“權利用益物權”說較之“債權”說更令人滿意,然“債權”說派生出的“租賃權物權化”說和“特殊效力債權”說又大為縮小了它們之間實際的差距。確實,土地經營權的定性是一個政策選擇問題,定性為物權性土地利用權(用益物權)或債權性土地利用權均無不可。“物權和債權的區分并非絕對,其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
就本文研究而言,更為重要的是,是否有必要將土地經營權徹底做實,并非是一個無需深入思考就可以斷然下結論的問題。
(二)名為做實實為異化論
本文對該論的總體概括是:在農地“三權分置”中,名為做實實為異化集體土地所有權+做虛土地承包經營權+做實土地經營權。
1.名為做實實為異化集體土地所有權。高富平認為:“三權分置”并不是簡單地將土地承包經營權拆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并加以重新配置,而是對農民集體所有權及其所支撐的農民集體經濟實現方式的重構。他對“三權分置”的理解近似于廣東南海的土地股權化模式:農民集體保留土地所有權,并把土地從農戶手中收回統一經營,發包、出租給專業農戶、農業公司經營,經營者直接向農民集體支付土地使用費;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被改造為集體土地的份額權利;農民集體在扣除集體提留等項目后,把土地經營費按份分配給農民。他認為:如此一來,在農地“三權分置”模式下,土地所有權由農民集體所有變成一種特殊的共有,土地所有權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修正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總體上與前述理論不相一致。
2.做虛土地承包經營權。高富平認為:“三權分置”的核心是原來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價值化,將其轉變為農民集體所有權的份額,將土地的實際占有使用權交給專業農業經營者。農民集體成員在集體所有權中的“份額”真正體現為財產份額(所有權收益),而不是“實物”。前述高富平的理論徹底做虛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因為土地已被從農戶手中收回而由農民集體統一經營(含對外發包、出租派生土地經營權),而農戶享有的土地權利不再具有用益物權的基本屬性,而純化為農民集體成員全體作為共有人(名義上的“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人”)對共有財產(名義上的“集體財產”)的收益權和處分權。修正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與前述理論不相一致:依據該法第5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依據該法第17條,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權利,有權自主組織生產經營和處置產品;依據該法第36條,承包方可以自主決定依法采取出租(轉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轉土地經營權,并向發包方備案。
3.做實土地經營權。高富平認為:在“三權分置”體制下,不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讓渡了土地的經營權,而是農民集體出讓或設定土地經營權(土地使用權)。農民集體一旦設定土地經營權并經登記,土地經營權就成為真正的用益物權,成為可以自由流轉的土地權利。由此,真正實現了農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修正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總體上也與前述理論不相一致,未使土地經營權成為真正的用益物權,其也并非可以自由流轉,如依據該法第46條,土地經營權流轉需經承包方書面同意。
(三)實虛相間論
這是本文秉持的觀點,其核心主張是:在農地“三權分置”中,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宜實虛相間(此實彼虛),土地經營權宜做虛,不應弱化集體土地所有權對土地經營權的影響。
1.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宜實虛相間(此實彼虛)
“落實集體土地所有權、穩定農戶土地承包權”,并不意味著將兩權都徹底做實,或者走向另一個極端——將其中的一權徹底做虛。兩權關系非常密切,相互影響很大,可謂此實彼虛。兩權關系最理想的狀態是兩權均實虛相間。至于具體其中哪權實得多一些、虛得少一些,哪權反之,則主要取決于價值判斷——是追求賦予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和集體共同利益價值目標多一些,還是追求實現農戶個體利益多一些。前述做虛論和名為做實實為異化論主張追求實現后者利益多一些,本文主張實現前者利益與后者利益的兼顧與平衡,故認為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宜實虛相間。
集體土地所有權主要承載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和集體共同利益的價值目標,而土地承包經營權主要承載實現農戶個體利益目標。實現兩大價值目標的兼顧與平衡,這必然要求農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宜如同有研究者主張的那樣是“永久不變的”,最多只是“長久不變的”;不是“自物權”,最多只是較長期限的受一定限制的用益物權;不是絕對不能被集體土地所有權調整或收回的,但也不是可以隨意被調整或收回的;流轉既不能太過于受制于集體土地所有權,但也不能完全放開自由流轉。如依據該法第21條,耕地的承包期為30年,承包期屆滿后再延長30年。可見,土地承包經營權相對修法前的規定又做實了一些,但依然不是“永久不變的”,沒有完全做實。又如依據該法第28條,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調整承包地。承包期內,因特殊情形矛盾突出,需要對個別農戶之間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適當調整的,必須堅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不得打亂重分的原則,必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2/3以上成員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和縣級人民政府農業農村、林業和草原等主管部門批準。承包合同中約定不得調整的,按照其約定。可見,承包期內,發包方并非不可以調整承包地,只是延續舊法繼續受到嚴格限制,在這一點上,土地承包經營權做虛而集體土地所有權做實。
2.土地經營權宜做虛,不應弱化集體土地所有權對土地經營權的影響
(1)土地經營權宜做虛
“放活土地經營權”并不意味著一定做實土地經營權,兩者沒有必然關系。是否有必要將土地經營權做實,并非是一個無需深入思考就可以斷然下結論的問題,這同樣涉及價值判斷。如依據該法第43條,因投資改良土壤等需經承包方同意而非土地經營權人自主決定,且按照合同約定而非現值評估對其投資部分進行合理補償。又如依據該法第46條,土地經營權流轉,需經承包方書面同意并向本集體經濟組織備案。這些都屬于做虛土地經營權。
(2)不應弱化集體土地所有權對土地經營權的影響
本文認為:在“三權分置”中,集體土地所有權不但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對土地經營權產生間接影響,還對土地經營權產生直接影響,這種影響不應被弱化。這是由法律賦予集體土地所有權擔負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和集體共同利益的使命所決定的。如依據該法第45條第2款:工商企業等社會資本通過流轉取得土地經營權的,本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收取適量管理費用。其實這旨在促使集體經濟組織對此加強實施管理。又如依據該法第46條和第47條,受讓方通過流轉取得的土地經營權,再流轉和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的土地經營權流轉,需經承包方書面同意并向本集體經濟組織備案。備案雖屬于弱管理手段,但在及時掌握管理信息方面是至關重要的。
農地“三權分置”中集體土地所有權功能定位的研究視角與理論基礎
有關農地“三權分置”中集體土地所有權功能定位的基本思路的前述三論,進一步探究其各自的研究視角和依托的理論基礎,有助于加深對本主題研究的深度。
(一)做虛論和名為做實實為異化論的研究視角與理論基礎
1.研究視角:私法。做虛論倡導做虛集體土地所有權,使其成為“名義上的保留”;與此同時,做實與集體成員即農戶個體利益密切相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甚至將其視為“自物權”。名為做實實為異化論則直接言說集體土地所有權系共有權。做虛論和名為做實實為異化論倡導者或許忘記了“無論是按份共有還是共同共有,都可能導致集體財產完全私有化以及集體財產的不穩定性”。因為共有財產的基礎是先有單獨的私人所有,權利人才能就其所有的財產結為共有。
做虛論和名為做實實為異化論的前述言說實際是單純從私法的研究視角來對集體土地所有權作理論認知。前述言說對集體土地所有權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分析之所以存在偏誤,是因為其選擇作為分析框架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制度,是以私法上的私人所有權為主導的,這個分析模板旨在保障財產的個人支配,并因此強調權利具有個體性。其實,“農地的集體所有權缺乏私法所有權的基本屬性,僅保留所有權很少的權能”。本文認為,不僅不得妨害社會公共利益,而且積極促進實現社會公共利益本身正是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兩大法律使命之一。
2.理論基礎:個人主義思想。私法對人的認知受個人(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觀影響。在做虛論和名為做實實為異化論者看來,集體這個小型社會就是農戶的聯合體,除了每個農戶自己的利益之外,集體沒有自身獨特的利益;“集體的利益”只是“集體成員——農戶的共同利益”的一個縮寫。但集體以及集體的利益真的應當如上所述嗎?
在個人主義者看來,個體成立法人等這些人的聯合體是其實現個體利益的手段。因此,這樣的利益結合聯合體的出發點是單個人的物質利益愿望。在做虛論和名為做實實為異化論者看來,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存在可以使農戶無償分配到承包地,而這只是農戶維持生計甚至賺錢的一個還算不錯的法律工具而已。在此,我們只看到農戶從集體可以得到什么好處利益,但沒有看到農戶應當為集體付出什么情感心力。這樣一種法律上的人的新類型是按照商人的形象來塑造的,它是一種完全逐利的、精于算計的形象。
(二)實虛相間論的研究視角與理論基礎
1.研究視角:社會法。實虛相間論者秉持集體土地所有權“總有”說而非“共有”說。孟勤國就“總有”說認為:集體公有的這些特征與以中世紀日耳曼村落共同體土地所有形態為典型的“總有”具有高度相似性。以總有解釋和規制集體所有權對于集體財產的保護、加強集體財產管理、維護集體成員合法權益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集體土地所有權“總有”說與“共有”說的最大本質不同是:前者關注的重點是集體本身的利益,而后者關注的重點則是集體成員的利益。“總有”說會認為,先有集體后有集體成員,脫離集體的成員將不再是集體成員;而如前以述,“共有”說的闡述則完全反過來。“如果集體所有權發揮一種銜接公權和私權關系的作用,那么其功能定位應該是準確的。”而這其實正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間的社會法的研究視角。
2.理論基礎:集體主義兼受個人主義思想。社會法對人的認知深受集體(反自由)主義思想影響。在實虛相間論者看來,集體這個小型社會不是農戶的聯合體而是其共同體,從而具有遠超于聯合體的價值意義。同時,在集體主義者看來,集體利益派生且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利益產生且服從于集體利益。因集體主義過于理想化,且被本土鄉村實踐證明是缺乏效率的,故實虛相間論的理論基礎深受集體主義兼受個人主義思想影響。
在實虛相間論者看來,集體土地所有權不僅僅是農戶維持生計甚至賺錢的一個還算不錯的法律工具,因此,農戶不但可以從集體得到好處利益,更應當為集體付出情感心力。
結論
在農地“三權分置”中,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宜實虛相間(此實彼虛),土地經營權宜做虛,不應弱化集體土地所有權對土地經營權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