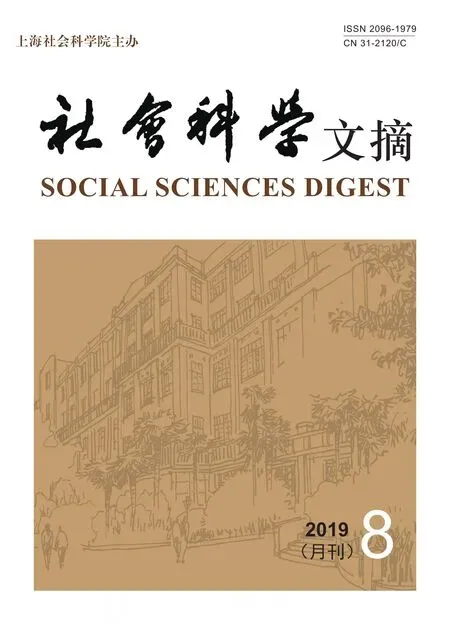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鄉村形象譜系
文/南帆
小引
在當代文學史內部,眾多鄉村分別組織在不同的主題脈絡之中,顯現出不同的形象層面,同時還隱含了遠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涵義。多義的鄉村可能與形形色色的社會話題相互銜接。如果說,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鄉村敘事相對單薄,那么,當代文學的鄉村顯現出多維的豐富形象。考察當代文學史的鄉村形象譜系,人們可以看到鄉村與現代性之間一波三折的歷史博弈,察覺鄉村置身于現代文化網絡承擔的多種涵義。
一
鄉村是糧食生產基地,諸多鄉村的組成因素構成了糧食生產工具,這個樸素的觀念很遲才被文學真正接受。這種狀況甚至無聲地改變了鄉村敘事的文學修辭。對于中國古代文人說來,鄉村通常僅僅是局外人眼中的一幅寫意水墨畫。鄉村作為糧食生產工具進入當代作家視野,鄉村各種景象的比例、遠近發生了重大的調整。文學開始不厭其煩地再現“糧食”范疇之內的莊稼和農產品。土地和田野無可置疑地占據了文學視野中心。根據不同農作物的生長特征,水田、旱地、黃土地、黑土地、沙包地、梯田、林地等各種類型的田地陸續出現在當代文學之中。圍繞糧食生產功能,田地的另一些組成部分以及基礎設施得到了近景呈現,例如水渠、田埂、肥料以及泥土的肥沃程度。從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柳青的《創業史》、趙樹理的《三里灣》、浩然的《艷陽天》到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張煒的《古船》以及高曉聲或者賈平凹的一系列短篇小說,40年左右的時間里,當代文學之中鄉村、土地、糧食生產的固定關系幾乎沒有什么改變。
正如許多作家意識到的那樣,現今土地與糧食的關系面臨深刻的轉折,鄉村的歷史似乎正在與農耕文化告別。賈平凹的《秦腔》之中,偌大的七里溝只剩下夏天義老人與一個瘋子、一個殘疾人在田野里忙碌;鄉村的土地要么一文不值,要么鏈接到另一個系統,轉換為另一種財富——房地產。賈平凹的《一塊土地》簡練地寫出了土地意象的反復變化:“收了,分了,又收了,又分了,這就是社會在變化。”
某些特殊的年份,熾烈的戰火可能摧毀日常景象,當代文學史曾經屢屢出現戰火燃燒的鄉村。當代文學再現的某些戰爭場景顯現出強烈的地域特征,例如《平原槍聲》和《敵后武工隊》之中頻繁出現的青紗帳,或者莫言《紅高粱》《豐乳肥臀》之中的高密鄉。梁斌的《紅旗譜》之中,家族世仇終于釀成了貧農階級與地主階級的殊死大搏斗。對于當代文學史說來,這是鄉村譜系的重要一章:鄉村的土地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鄉村成為戰場。
二
鄉村的精神生產是當代文學的另一個引人矚目的主題。《紅旗譜》之中,朱老忠已經完全顛覆了阿Q式的農民形象。歷史已經賦予他們擔任革命主角的機遇。新型的農民形象已經誕生。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與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均是以20世紀40年代下半葉的土改運動為背景。土改運動叩醒了農民性格之中的潛能,促使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破土而出。促成這個重大的現代性事件,革命產生的功效遠遠超過了啟蒙。
大半個世紀之后,當代文學進一步察覺到歷史的復雜性:叩醒農民性格之中的潛能,那些蟄伏的沖動是否可能同時隱含了某些負面能量?通常的觀念之中,積極進取的精神帶來的正面能量被賦予革命階級,兇悍、殘忍、心狠手辣被賦予反動階級。然而,賈平凹的《老生》顯示了問題之中深藏的一面。當階級的標簽不像以往那么有效的時候,一種奇特的現象逐漸浮現:一些鄉村革命者的為人處世竟然與他們的階級對手彼此相似。革命贏得勝利之后,粗暴、蠻橫、狹隘、江湖幫派乃至挾私報復仍然作為某種習氣或明或暗地承傳,甚至在革命辭句的掩護之下頻繁露面。這種文化性格可能嚴重地挫傷多數農民的積極性,損害鄉村的革命愿景。這種文化性格不僅遺傳到霸槽(賈平凹《古爐》之中一個畸形的鄉村叛逆分子),甚至還可以在后來許多帶有草莽氣息的農民企業家身上發現,例如莫言的《蛙》之中牛蛙養殖場的總裁袁腮。
土改之后,農業合作化運動再度給鄉村的農民帶來了深刻的精神震撼。不論現今如何評價這一場運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農民之中出現了某些嶄新的精神氣質。改變農民的真實原因毋寧是集體生活——集體勞動以及集體經濟。農業合作化運動締造了新型的鄉村社會關系。分散的農民開始聚集在一起,形成互助組、生產隊、大隊、人民公社等各級集體組織,共同參與、規劃勞動生產。密集的社會交往重塑了農民的精神結構。鄉村社會的急劇變革促使每一個農民站出來,不僅跨出家庭的狹小范圍,而且以一個社會角色進入集體生活。作為鄉村的新型人物,一批集體勞動生產的領頭人出現在文學舞臺,例如趙樹理《三里灣》的王金生,柳青《創業史》的梁生寶,浩然《艷陽天》的蕭長春。當代文學的另一個收獲是展示了鄉村女性的迅速崛起。許多潑辣型的鄉村女性絡繹不絕。李準的《李雙雙小傳》名噪一時,小說的主題已經從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背景聚焦為婦女解放。相對于魯迅《祝福》之中的祥林嫂,可以察覺鄉村女性走得多遠。
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再度點燃了沉悶的鄉村。許多批評家共同提到了何士光的《鄉場上》與張一弓的《黑娃照相》。經濟復蘇塑造了農民的獨立人格。20世紀60年代,浮夸的風尚借助行政權力在鄉村彌漫。春荒來臨之際,一個村支書大膽開倉借糧,拯救饑餓的農民。他愿意為心目中的正義付出代價,這即是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李銅鐘這種超前的覺醒讓人聯想到日后的“小崗村精神”。
三
鄉村是相對于城市而言的。由于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傳統,這種“相對”隱含了階級文化的對抗。20世紀50年代初期,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造成了巨大的風波。許多革命者熟悉的是如火如荼的鄉村,城市如同另一種危險的叢林。《霓虹燈下的哨兵》——從話劇到電影——高度警惕城市各個角落發射出來的糖衣炮彈。這時,鄉村與城市的二元對立很大程度上可以置換為革命與腐朽。
鄉村文化充滿了泥土氣息,后者顯然為眾多的農民喜聞樂見。鄉村文化的美學風格同時顯現了清晰的政治方位。趙樹理顯然是從鄉村文化之中脫穎而出的。“趙樹理方向”之所以贏得了廣泛的肯定,一個重要原因是成功展示了鄉村文化的美學魅力。《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地板》《邪不壓正》等一批作品不僅勾畫了一批生動的農民形象,同時還創造了評書體的小說形式。趙樹理的風格遠遠超出了個人的成功,而是作為民族的、鄉村的美學范本回應乃至抵抗現代城市文化。
盡管鄉村對于城市的批判幾乎構成了某一個時期的文化慣例,但是,鄉村與城市的競爭資本只能是獨特的社會吸引力。因此,50年代末期馬烽編劇的電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批年輕人相聚鄉村生活、創業,他們收獲了事業與愛情。然而,電影之中明朗歡快的氣氛是歷史的再現還是美學的幻覺?
當代文學的許多作品可以參與這個問題的爭論。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展現了城市對于鄉村生活的強烈沖擊。《平凡的世界》開啟了一幅宏大的生活畫卷,空間遼闊,人物眾多,但是,這個空間的鄉村與城市處于強烈的失衡狀態。鄉村顯得貧瘠、干涸、窮困、無奈,《紅旗譜》的革命氣勢與《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的樂觀已經消褪殆盡。
與《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相反,許多年輕的農民拔寨而起,進入城市務工——他們被稱為“農民工”。城市始終是一個異質的空間。某些時候,他們可能遇到莫大的敵意,例如王安憶的《悲慟之地》。面對不斷擴大的城市,孤軍深入的鄉村再也無法維持傳統的精神優越。
四
20世紀80年代中期,鄉村作為文化根系的沃土再度成為當代文學的青睞對象。這即是“尋根文學”的興起。耐人尋味的是,描述民族文化根系的時候,作家紛紛從城市文化面前掉頭而去,返回鄉村追根溯源。
無論是韓少功、阿城、李杭育,還是王安憶、賈平凹、鄭萬隆,這些“尋根”作家旨趣不一,風格相異,但是,他們不約而同地聚集到了鄉村。從老莊佛禪、儒學義理到民間的奇風異俗或者傳奇人物,“尋根文學”之中的鄉村遠比城市活躍。阿城的《棋王》和《遍地風流》、賈平凹的《商州初錄》和《商州又錄》、鄭萬隆的《老棒子酒館》和《異鄉異聞三題》以及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都從鄉村發現了某種本真的自由人生。血性豪邁也罷,散淡達觀也罷,天真無邪也罷,鄉村天地廣闊、月朗風清,生活在那里的人們可以卸下了城市文化堆積的功利、世俗、纖弱和斤斤計較。鄉村并非僅僅是一日三餐、春耕秋收的簡單循環,而是充滿了悠遠、神秘乃至形而上的啟示,例如來自韓少功《爸爸爸》之中不死的丙崽和王安憶《小鮑莊》之中慈祥如菩薩的撈渣。神話、傳說、歌謠、祈禳、巫術、咒語——只有天人合一氣氛之中的鄉村才能恢復這一切。
陳忠實于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白鹿原》可以視為“尋根文學”的回響,也可以視為“尋根文學”的終結。《白鹿原》推崇的是儒家觀念,朱先生是儒學導師,白嘉軒是儒學的鄉村實踐者。白嘉軒與鹿三的主仆關系猶如兄弟,白嘉軒與鹿三對于田小娥共同的仇視顯示了儒家道德觀念對于女性的輕蔑。白嘉軒引為自豪的是坦蕩的襟懷與正直的人格,這是“修身”與“齊家”的準則。可是,《白鹿原》后半部分的“治國”“平天下”摧毀了儒家的道德標準。白、鹿兩個家族的后代分別卷入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白嘉軒乃至朱先生無法理解各種政治口號和階級觀念,他們只能隔岸觀火。事實上,這也是“尋根文學”再現的很大一部分鄉村的命運。由于現代政治文化的覆蓋,鄉村逐漸被納入現代性體系。這個意義上,“尋根文學”的鄉村帶有很大程度的挽歌意味。鐵凝的《笨花》之中,不慌不忙的鄉村節奏漸漸被種種新生事物打破,向喜這種固守傳統的老派人物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無論是“尋根文學”、《白鹿原》或者《笨花》,這一批作品或許共同隱含了一個問題:難道這些鄉村僅僅是現代性尚未分解的殘留物,而不是保存了某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嗎?
當然,當代文學的鄉村從未放棄沁人心脾的田園風光。沈從文的《邊城》是一曲悠揚的牧歌,但是,這一曲悠揚的牧歌遲遲無法被妥帖地編輯在激蕩的現代文學之中。孫犁的《荷花淀》意味了一個成功的范例——月光下的鄉村院落、蘆花飄飛的白洋淀終于和一場伏擊戰詩意而巧妙地銜接在一起。當代文學之中,相對于巨大的歷史轟鳴,單純的田園風光顯得有些“輕”,盡管沒有人可以否認劉紹棠或者汪曾祺的奇特魅力。劉紹棠或者汪曾祺擅長描繪水鄉景象,使波光粼粼的河流、湖泊與水鄉的人情世故渾然一體。相對地說,劉亮程展現的是大西北風沙之中的鄉村。某些時刻,鄉村的田園風光可能與環境生態的主題聯系起來,卷入工業污染、經濟暴利制造的嚴峻問題。鄉村作為一個受虐對象,其與城市的不平等可能突如其來地爆發出來。閻連科的《日光流年》之中,耙耬山脈皺折之中偏僻的三姓村千辛萬苦地修建了一條水渠,然而,他們引來的是一渠遭受嚴重污染的廢水。這個村莊從未享受工業的恩惠,卻必須承擔工業污染的后果。
五
20世紀80年代,鄉村形象曾經集中出現于兩批作家的作品之中。一批作家以王蒙、張賢亮、李國文等人為主,他們的共同經歷是50年代被劃定為“右派”,繼而下放到鄉村20余年。另一批作家的共同經歷是下鄉插隊,“知青”標明了他們的共同身份。80年代是知青文學成熟期。這一批作家為數眾多,佼佼者有史鐵生、韓少功、王安憶、梁曉聲、孔捷生,等等。某一個視角看來,兩批作家心目中的鄉村涵義清晰,意旨明確;另一個視角看來,這些鄉村涵義曖昧,甚至相互矛盾。
王蒙的《蝴蝶》《雜色》和張賢亮的《靈與肉》《綠化樹》以及李國文的《月食》均把鄉村視為主人公獲得救贖的驛站。猝不及防的政治襲擊之后,他們被強制遣送鄉村,然而,鄉村并未虧待他們。農民的忠厚、善良以及博大的同情心逐漸愈合了他們內心的創口,甚至賦予純樸無私的愛情。這不啻于提前在精神上解放了他們。鄉村完美地組織在情節之中,成為主體完成的一個必然環節。
強制遣送的鄉村令人聯想到“流放”——事實上,張賢亮的《靈與肉》即是使用“流放”一詞。然而,當農民——貧下中農——被形容為革命階級不得不踞守鄉村的時候,“流放地”是一個令人難堪的稱謂。也許,鄉村的貧瘠不言而喻,只不過這個事實被眾多華麗的辭令壓縮為不可表述的無意識。主人公落難、復出與“大團圓”,鄉村與農民作為背景完成情節賦予的使命,作家似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鄉村的這種涵義。
主體的完成曾經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知青文學之中。知青抵達鄉村之后,他們對于困苦的生活條件、貧乏的文化環境和農民的日常表現大失所望,謀求返城成為多數知青不懈的訴求。多年之后他們如愿以償,然而,對鄉村生活的回望卻帶來了一個重要的人生感悟:知青突然意識到曾經相處的農民如此質樸、善良,曾經寄居的土地如此開闊、美麗。這隱喻了主體的一個嶄新的精神高度。顯然,這種感悟將持久地貯存于知青的內心,無形地左右他們對于未來的設想和塑造。
然而,分析知青文學的情節構成,鄉村的涵義再度閃爍不定。一種觀點認為,鄉村的基本形象是革命大熔爐。知青來到鄉村的主要任務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繁重的生產勞動往往轉換為戰天斗地的豪言壯語給予表述。另一種相對隱蔽的觀點仍然將鄉村設定為貧窮落后的區域,知青的職責是運用從學校獲取的文化知識建設新型的鄉村。事實上,兩種涵義的鄉村相互交織,二者的內在沖突構成了情節內部的緊張性。
賈平凹對于鄉村不是那么樂觀。他的眾多小說始終如一地續寫當代文學的鄉村譜系。然而,從《秦腔》《帶燈》到《極花》,賈平凹的憂慮清晰可見:鄉村的活力正在急劇衰減;這種狀況已經滲透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鄉村如同一個喪失水分的蘋果正在逐漸干癟。
當代文學史的鄉村譜系表明,文學視野之中的鄉村分量急劇增加。柳青曾經在皇甫村落戶14年。他的心目中,鄉村無疑是文學的富礦,深入開采,必有所獲。然而,人們可以從現今的許多作品之中察覺,文學的鄉村愈來愈荒涼,田園荒蕪、人去樓空,留守鄉村的農民幾乎無法構筑激動人心的宏大情節。鄉村敘事不再波瀾壯闊、縱橫捭闔。鄉村還能為作家的想象洪流提供強大的動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