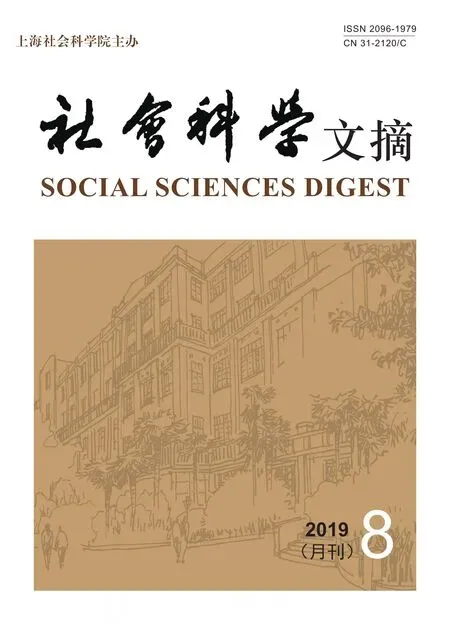從北美“中國研究”發(fā)展歷程看智庫研究范式之轉(zhuǎn)變
文/袁曦臨 吳瓊
智庫研究方法層面的發(fā)展態(tài)勢
隨著現(xiàn)代社會問題復(fù)雜性的增強,智庫研究已經(jīng)不再可能僅僅通過資料的收集整理、描述闡釋得以完成,雖然資料和數(shù)據(jù)的收集、發(fā)掘和整理極其重要,但這僅僅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第一步,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從資料和數(shù)據(jù)中發(fā)現(xiàn)、歸納并提煉出對于當(dāng)下或未來政治、經(jīng)濟、軍事、社會等有價值的規(guī)律和普遍經(jīng)驗。現(xiàn)代決策理論越來越強調(diào)基于證據(jù)循證的科學(xué)決策,多學(xué)科合作交融已經(jīng)成為智庫研究的主流。
1.量化的實證研究趨向
歐洲自19世紀(jì)末開始,就已經(jīng)注重將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學(xué)方式引入史學(xué)研究。通過收集并統(tǒng)計某地區(qū)一定時期內(nèi)社會各階層的人數(shù)及其收入狀況,可以計算出該地區(qū)居民的人均收入(即平均數(shù)),以及中產(chǎn)階級的收入(即中數(shù)),發(fā)現(xiàn)該地區(qū)各階層人口的收入集中趨勢;再通過標(biāo)準(zhǔn)差計算,推演出個人收入與人均收入的差異,即離中趨勢;而后將中數(shù)和平均數(shù)進行比較,得出該地區(qū)經(jīng)濟收入是否呈偏態(tài)分布及偏態(tài)的正負(fù)。在此基礎(chǔ)上政府出臺各類型政策等,調(diào)整政府決策與社會現(xiàn)實需求之間的聯(lián)系。著名經(jīng)濟史學(xué)家Robert William Fogel所著《鐵路和美國經(jīng)濟增長》一書的出版即標(biāo)志著“歷史計量學(xué)”的誕生。采用數(shù)學(xué)和統(tǒng)計方法對研究資料進行定量分析,以事實和數(shù)據(jù)為論據(jù)支撐,能夠有效避免基于個人認(rèn)知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及價值取向?qū)е碌难芯拷Y(jié)論的偏差。
現(xiàn)階段我國智庫研究主要圍繞歷史與現(xiàn)實的對話展開,為工業(yè)化、城市化、人口、一帶一路、社會福利、環(huán)境保護、政治經(jīng)濟制度建設(shè)、社會轉(zhuǎn)型等當(dāng)代中國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提供資政經(jīng)驗,因此對于實證研究方法有著深度需求和廣泛呼喚。
2.整體與區(qū)域并舉的研究趨向
整體主義研究范式是從整體性的角度考察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和人的行為,在20世紀(jì)60年代之后漸成趨勢。費爾南德·布羅代爾1958年發(fā)表了重要論文《歷史與社會科學(xué):長時段》,認(rèn)為歷史時間有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之分:短時段主要是突發(fā)的歷史現(xiàn)象、事件,如革命、戰(zhàn)爭、地震等;中時段是指具有一定周期和結(jié)構(gòu)的局勢或社會時間,如人口消長、生產(chǎn)增減;長時段屬于歷史的深層結(jié)構(gòu)和基礎(chǔ),如地理氣候、生態(tài)環(huán)境、思想傳統(tǒng)等,而長時段對歷史進程起著決定性和根本性作用。智庫研究面向的是國際國內(nèi)的政策制定和決策支持,如果沒有宏觀的視野,從整體予以考慮,而僅僅從一個學(xué)科的知識來分析,難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過于細(xì)致的研究容易扭曲問題本身,帶來認(rèn)識和理解上的偏差,對于現(xiàn)實問題難以給出合理的解釋和有效的政策建議。因此,整體研究符合智庫研究的要求特點。
與此同時,智庫研究所要解決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社會現(xiàn)實問題,而不是一個邊界清晰的學(xué)科內(nèi)部問題,故智庫研究同樣也需要具體而微的國別研究、區(qū)域研究和專題研究。2012年南海中心獲批為首批國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下設(shè)若干協(xié)同創(chuàng)新平臺,包括南海環(huán)境資源研究平臺、南海法律研究平臺、國際關(guān)系研究平臺、南海史地與文化研究平臺、南海周邊國家政治經(jīng)濟社會研究平臺、南海動態(tài)監(jiān)測與形勢推演平臺、南海地區(qū)航行自由與安全合作研究平臺、南海輿情監(jiān)測與國際交流對話平臺、南海問題政策與戰(zhàn)略決策支持平臺等,以期通過問題導(dǎo)向和任務(wù)驅(qū)動,為國家有關(guān)部門提供基礎(chǔ)信息與決策支持服務(wù)。
北美“中國研究”范式轉(zhuǎn)變的路徑分析
“中國研究”是美國“區(qū)域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哈佛大學(xué)成立“國際與區(qū)域性研究委員會”伊始,有關(guān)中國文化演變、社會流動、經(jīng)濟體制、稅收政策、政治制度以及共產(chǎn)主義運動等方面的課題越來越多。“中國研究”有著相當(dāng)明顯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
1.“中國研究”問題的多元化
北美“中國研究”至少歷經(jīng)過3次研究問題域的轉(zhuǎn)變和調(diào)整。
最初的“中國研究”以費正清及其同輩研究者為主,主要考察19世紀(jì)末東亞世界與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碰撞,尤其是中國在世界事務(wù)中的地位、角色和意向,以及中國傳統(tǒng)社會價值和全球秩序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等。如費正清早期的研究《中國沿海的貿(mào)易與外交》、芮瑪麗的《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一戰(zhàn):同治中興,1862—1874》、魏斐德的《大門口的陌生人》、史華慈的《追求富強:嚴(yán)復(fù)與西方》等,都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研究。當(dāng)然,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視角和認(rèn)識切入點發(fā)生變化,早期費正清等研究者多從“沖擊—回應(yīng)”這一角度來認(rèn)識中國,而孔飛力等的研究則轉(zhuǎn)向保羅·柯文提出的“中國中心論”,從中國人自身的立場來研究中國的近代發(fā)展變遷,作為對“沖擊一回應(yīng)”模式的反思和修正。孔飛力于1970年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即是“中國中心論”的突出代表,該書集中考察了華南與華中地區(qū)的社會基層組織團練在遭遇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自身所發(fā)生的變化。相關(guān)研究還有:樓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1895到1913年間的廣東省》、凱普的《四川與共和中國:地方軍閥與中央政府,1911—1938》、舍登的《地方軍閥與共和中國:云南軍1905—1925年》和周錫瑞的《中國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這些研究都是從中國的地方省份出發(fā),觀察和分析傳統(tǒng)中國的改良和革命路徑。
與此同時,研究主題日益從政治生活層面擴展到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馬若孟所著《中國農(nóng)民經(jīng)濟:河北和山東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1890—1949》是關(guān)于晚清和近代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對新中國前的華北農(nóng)村進行了深入考察,探討了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步入近代化的問題;而包德威的《中國城市變遷:1890—1949年山東濟南的政治和發(fā)展》則關(guān)注了相同時期城市的社會發(fā)展問題。
第二次轉(zhuǎn)變,主要關(guān)涉“二戰(zhàn)”結(jié)束后冷戰(zhàn)背景下東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形態(tài)、利益與社會關(guān)系的探討。該領(lǐng)域的研究涉及領(lǐng)域十分寬廣,著名的研究有斐宜理的《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該書力圖以城市生活的變動來詮釋中國的革命運動,揭示近代上海工人運動與中國政治的關(guān)系。誠如斐宜理自述的那樣,從20世紀(jì)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書《華北的造反者與革命者,1845—1945》到《巡邏革命:工人糾察隊,公民性與近代中國國家》,她一直在試圖解釋中國革命的淵源和意義。
第三次轉(zhuǎn)變,瞄準(zhǔn)的是20世紀(jì)末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后中國的經(jīng)濟轉(zhuǎn)型階段。西方特別關(guān)注的問題是:隨著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日益強大的中國會成為怎樣的國家?這個國家對世界的意義何在?中國的現(xiàn)代性和西方的現(xiàn)代性有什么區(qū)別?未來中國會選擇怎樣的發(fā)展道路,會發(fā)展出一個具有何種示范意義的文明?此范疇內(nèi)研究內(nèi)容豐富而廣闊。諸如黃宗智1985年出版的《華北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與社會變遷》和1990年出版的《長江三角洲的小農(nóng)家庭和鄉(xiāng)村發(fā)展,1350—1988》;陳佩華的《陳村:革命到全球化》,通過跟蹤一個村莊從最初的毛澤東時代如何進入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最后面對全球化的過程及其內(nèi)部調(diào)整;顧林的《中國經(jīng)濟革命:20世紀(jì)鄉(xiāng)村企業(yè)》,則通過對湖北地區(qū)自民國初年一直到1978年以后的農(nóng)村紡織業(yè)的對照研究,探索市場經(jīng)濟與鄉(xiāng)村社會變動的聯(lián)系。
近年來,中國研究領(lǐng)域由宏觀到具體,研究的主題愈加寬廣。論文集《中國親屬關(guān)系:當(dāng)代人類學(xué)視角》從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國社會的各種關(guān)系;閻云翔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和親密關(guān)系,1949—1999》和《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和社會網(wǎng)絡(luò)》都是從人類學(xué)實地考察出發(fā),展示中國社會的變遷。在法律建設(shè)方面,陸思禮1996年的成名作《中國司法改革》、1999年的《籠中之鳥:后毛澤東時代的司法改革》、2005年的《法律在中國的應(yīng)用:國家、社會和實現(xiàn)正義的可能性》等側(cè)重關(guān)注中國的司法改革進程。
2.“中國研究”方法的實證化
費正清創(chuàng)辦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之初,即奠定了開放多元的跨學(xué)科研究和多學(xué)科合作的風(fēng)格,強調(diào)對于中國的研究需要通過細(xì)致入微地對基層社會生活圖景的復(fù)原,來了解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脈絡(luò)和特質(zhì)。擔(dān)任過斯坦福大學(xué)東亞圖書館館長的邵東方曾經(jīng)開過一門漢學(xué)研究方法課程,在研究方法和證據(jù)使用方面提出非常具有指導(dǎo)意義的三原則,即識別古今之異、尋找發(fā)現(xiàn)證據(jù)和探究歷史因果。斯坦福大學(xué)施堅雅教授所做的中國區(qū)域社會結(jié)構(gòu)與變遷研究就充分體現(xiàn)了上述三原則。其著作《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是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對中國經(jīng)濟史、中國城市史研究影響最大的理論著作之一。施堅雅認(rèn)為,把中國的鄉(xiāng)村理解為自然村落,并不符合中國農(nóng)村實際的社會結(jié)構(gòu),周期性的廟會集市才是農(nóng)村的基層市場社區(qū)。由此,施堅雅計算出19世紀(jì)90年代全廣東省的村莊數(shù)與市場數(shù)之比,提出形成中國鄉(xiāng)村市場區(qū)域的正六邊形模式。而后,他使用這一模型分析了四川、浙江等地的農(nóng)村社會,發(fā)現(xiàn)“十八村莊一市場”的結(jié)構(gòu)模式,從而形成了觀察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施堅雅模式”。施堅雅模式的突出貢獻在于將地理空間概念引入經(jīng)濟歷史學(xué)研究中,為經(jīng)濟學(xué)和歷史學(xué)研究開辟了新的思路和視野。盡管后來的研究者對此理論模式有諸多非議,但從方法層面看,施堅雅模式是非常成功的。
3.“中國研究”資源的系統(tǒng)化
對于智庫研究而言,研究資料和研究數(shù)據(jù)的獲取、收集和組織、整理,不僅僅是工具準(zhǔn)備,甚至就是研究本身。北美的中國研究非常重視實地調(diào)查報告和訪問記錄,重視統(tǒng)計資料、地方志、地方檔案、報刊雜志、案件記錄、回憶錄、私人信件、宣傳品、照片等資料的收集。比如,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收集的《杰德·斯諾·王私人檔案》包括了大量20世紀(jì)70年度初期訪問廣東基層社會的筆記,以英文記錄了當(dāng)時的廣東農(nóng)村的教育、經(jīng)濟、文化狀態(tài),是難得的基層社會報告。加州大學(xué)洛杉磯校區(qū)東亞館收藏的《譚良所藏康有為保皇會資料》,主要是300多封20世紀(jì)北美保皇會成員之間及與中國國內(nèi)的往來信件,對于研究華裔社團、廣東一帶的基層社會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胡佛研究所則側(cè)重中國檔案文獻的收藏,涵蓋20世紀(jì)以來大量珍貴歷史和政治史料,包括蔣氏父子日記在內(nèi)的特殊人物的回憶錄和個人收藏。2005年,該所還獲得加州大學(xué)洛杉磯校區(qū)歷史系黃宗智及其妻子多年收集的中國歷史檔案資料,其中包括2500件法律案件,時間跨度自晚清、民國政府到新中國時期。這些歷史檔案成為胡佛研究所進行智庫研究的重要文獻基礎(chǔ)。伴隨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發(fā)展,研究資料的收集和組織愈加注重分析資料背后的邏輯聯(lián)系,倡導(dǎo)將量化數(shù)據(jù)庫應(yīng)用于歷史研究。美籍華裔歷史學(xué)家、曾任密歇根大學(xué)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中清,已建立了18世紀(jì)至今的中國歷史數(shù)據(jù)資料庫。
我國智庫研究范式的轉(zhuǎn)型思考
一個世紀(jì)以來的北美“中國研究”不僅拓展了中國史研究的時空范疇和研究視野,也帶來了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北美的中國研究無疑為我國智庫研究和發(fā)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jīng)驗。
1.在研究思維層面強調(diào)全球化的研究視角
需要將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放到國際和區(qū)域發(fā)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從而完成中國地方性知識和歷史經(jīng)驗轉(zhuǎn)化成具有全球意義話題的轉(zhuǎn)變。例如黃宗智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明清商品化的研究,通過對“過密化”理論的引入和修正,提出明清時期的商品化之所以無法近代化,根本原因在于長江三角洲的過密化,或稱內(nèi)卷化。由此,過密化理論受到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的廣泛重視,在認(rèn)識視角和研究方法層面都對我國社會經(jīng)濟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2.在方法層面強調(diào)定量化的實證研究
對于智庫研究而言,方法論和歷史觀其實是統(tǒng)一的。不存在孤立的方法論,方法和工具就決定了觀察世界的立場和眼界。實證研究強調(diào)研究是建立在事實數(shù)據(jù)基礎(chǔ)之上的,尤其重視一手資料的發(fā)掘、整理,強調(diào)研究結(jié)果的可驗證性。對于智庫研究而言,這將避免研究預(yù)設(shè)的偏頗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先入為主。長久以來,對于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jīng)濟的巨大成就,如何從理論和模式層面進行解釋一直是學(xué)界也是全世界矚目的問題,但僅僅闡述觀點、描述過程和個案分析顯然是不夠的,只有通過合乎規(guī)范的數(shù)據(jù)和論證范式,才能減少模糊不清的爭論,為不同學(xué)科和研究領(lǐng)域之間的討論和交流提供事實基礎(chǔ),為科學(xué)決策提供扎實的事實依據(jù)。
3.在研究合作層面更多倡導(dǎo)跨學(xué)科協(xié)同研究
注重借鑒不同學(xué)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圍繞現(xiàn)實問題展開多維度研究。一般理解中,研究模式似乎只關(guān)乎研究路徑的具體展開與研究方法的應(yīng)用,但實際上每一個新的研究概念的提出,都標(biāo)志著新的問題和切入問題的新起點,都拓寬了新的研究資源的來源。南海研究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示范,中國南海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開展了一系列南海維權(quán)證據(jù)鏈及基礎(chǔ)數(shù)據(jù)庫建設(shè),包括監(jiān)測、提供海域和關(guān)鍵島礁的動態(tài)變化,南海斷續(xù)線的法理與歷史依據(jù)專項,南海檔案的系統(tǒng)整理與使用專項等跨學(xué)科研究;由此推動了交通史、文化交流史以及邊疆史的研究,也拓展了海洋史的研究范疇。
結(jié)語
在一般理解中,研究模式似乎只關(guān)乎研究路徑的具體展開與研究方法的應(yīng)用與實現(xiàn),但實際上,研究領(lǐng)域的拓展、研究主題的轉(zhuǎn)變,甚至研究資源的發(fā)掘整理同樣也是研究范式轉(zhuǎn)變的一種標(biāo)示。一個世紀(jì)以來的北美“中國研究”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研究范式的轉(zhuǎn)換,研究主題領(lǐng)域幾乎涉及了中國社會急劇轉(zhuǎn)型過程的方方面面;研究方法層面,則不斷探索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研究框架和理論模型;在研究資源的收藏和建設(shè)中,不僅重視一手資料的有針對性采集,而且注重采用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以保證傳統(tǒng)研究跟上數(shù)字化步伐。
中國的崛起是近半個世紀(jì)最重要的國際現(xiàn)象之一,如何在夯實研究的同時,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發(fā)展經(jīng)驗和建設(shè)成就,需要更為客觀、科學(xué)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式層面調(diào)整研究視角,采用全球化思維,拓寬研究領(lǐng)域,把中國問題放置在全球框架下去認(rèn)識研究,提出新的概念和觀點是極為重要的;北美中國研究不僅拓展了中國史研究的時空范疇和研究視野,也帶來了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基于量化數(shù)據(jù)進行扎實的實證研究,可以讓智庫研究更為純粹,也更能為國際所接受,事實上,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探究新型智庫的研究路徑和方法,將會是智庫研究面臨的歷久彌新的長期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