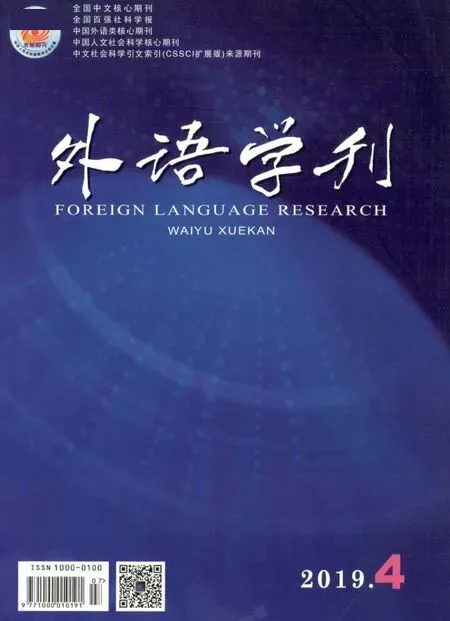譯介學:理念創新與學術前景?
謝天振
(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200083/廣西民族大學,南寧 530006)
提 要:譯介學是為數不多的中國學者原創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翻譯學理論,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推出后在國內和海外學界產生較大的影響,進入新世紀后,譯介學研究被列入2006年國家外國文學研究八大課題指南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2006—2010)。然而,國內學界對譯介學的學科定位、理論指向及其術語內涵等存在誤讀、誤釋的學者也大有人在。為此,筆者作為譯介學理論的創導者現身說法,對譯介學的關鍵術語和核心理念,如創造性叛逆、翻譯文學和文學翻譯、翻譯文學史等概念,以及譯介學研究的學術前景進行深入淺出的闡釋和辨析。
長期以來,我國國內的翻譯研究極大多數局限在對語言文字轉換的層面上。香港翻譯理論家王宏志指出,“充其量只不過是有關翻譯技巧的討論”,“對于提高翻譯研究的學科地位沒有多大幫助”(王宏志1999:6)。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我們開始探索并倡導的譯介學理論①也許是國內最早把翻譯研究的視角轉到翻譯作為人類文化的交際行為層面上予以審視和研究的中國大陸學者首創的翻譯理論。正是借助這個理論,筆者從1989年起在陸續發表的論文中提出一系列比較引人注目、富于一定創新意義的學術觀點,并在國內學界引起較大的“震撼”(陳德鴻 張南峰2000:185-186),這些觀點首先集中體現在1999年推出的專著《譯介學》里。進入新世紀以來,譯介學研究越來越引起國內學界的關注和重視,繼“2006年國家課題指南(外國文學)”把它列為當年國家的八大外國文學研究課題之一后,“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再次把譯介學列為其中的研究課題之一。
盡管如此,國內譯學界,尤其是翻譯界,對于譯介學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對它的理論內涵、它對翻譯研究的實際價值與意義等問題仍感到疑惑不解,甚至誤解的專家學者大有人在。因此,值此拙著《譯介學》(謝天振1999)出版20周年之際,本人/筆者認為有必要對譯介學理論的核心理念、學術前景等問題做一番闡述。
1 創造性叛逆:譯介學研究的理論基石
自從《譯介學》一書問世以來,“創造性叛逆”這一觀點不脛而走,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碩、博士生們,在寫學位論文時廣泛引用,作為他們展開研究的一個讓人感到富于新意的切入點。在《譯介學》中已經明確提到,“創造性叛逆”這一命題并非首創,而是借用自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的專著《文學社會學》一書中的一段話:“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這一說法的話,那么,翻譯這個帶刺激性的問題也許能獲得解決。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里(指語言);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埃斯卡皮關于“創造性叛逆”的觀點引起我強烈的共鳴,它道出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的本質。不過與此同時,我覺得埃斯卡皮把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僅僅解釋為語言的變化似乎有些簡單。我認為,這里的參照體系不僅應該指語言,還應該包括文化語境。于是,我按照埃斯卡皮的這一觀點,對創造性叛逆作出進一步的闡發,指出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現象特別具有研究價值,因為這種創造性叛逆特別鮮明、集中地反映出不同文化在交流過程中所遇到的阻滯、碰撞、誤解、扭曲等問題。
在《譯介學》和《翻譯研究新視野》(謝天振2003)里,首先對公認的“創造性叛逆”的主體——譯者的創造性叛逆現象進行比較詳細的分析。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在文學翻譯中有4種表現,即個性化翻譯、誤譯與漏譯、節譯與編譯以及轉譯與改編。而且,文學翻譯中創造性叛逆的主體不僅僅是譯者,讀者和接受環境同樣也是文學翻譯創造性叛逆的主體。之所以將接受環境作為創造性叛逆的主體是因為有學者對這一觀點表示質疑,認為媒介者(譯者)或接受者(讀者)的創造性叛逆都可以理解,這兩者都是有行為能力的人,可以實施和完成創造性叛逆這個行為,但接受環境并不是具有行為能力的主體,它如何實施和完成創造性叛逆?這里須說明的是,把接受環境的創造性叛逆與媒介者和接受者的創造性叛逆分開論述是為了讓讀者看到前者的創造性叛逆是一種集體行為,而后兩者多屬于一種個體行為。接受環境自身確實沒有行為能力,但它通過接受者的集體行為完成并反映出它的創造性叛逆。譬如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原作是一部字字隱藏著譏諷的政治小說,如書中擁護“甲黨”和“乙黨”的穿高跟鞋派,吃雞蛋先敲大端的“大端派”和先敲小端的“小端派”,在斯威夫特所處的英國社會里,都有明顯的影射對象。但是,當這部小說被譯介到其他國家以后,人們不再注意小說的政治鋒芒,感興趣的僅是作者以其豐富的想象力所描繪出來的充滿怪誕異趣的大人國、小人國的故事。以中國為例,自1914年林紓開始翻譯起②,這部小說就不斷地被譯介,但大多數譯本僅譯出其第一、二部,即“小人國”“大人國”兩部,有的干脆以“小人國”“大人國”命名,而且明確列入“少年文學故事叢書”或“世界少年文庫”。一部嚴肅的政治諷刺小說就這樣因語言、文化環境的變遷,而變成一本輕松、有趣的兒童讀物。然而這種“變化”或稱“叛逆”是整體接受環境使然,卻不是某一譯者或某一讀者的主觀行為和作用。
“創造性叛逆”這一觀點最主要的意義在于它揭示出翻譯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本質特點。千百年來,翻譯界,無論中西,都一直把交出一份百分之百忠實于原文的譯文視作自己的最高追求,甚至是惟一追求,以為只要交出一份百分之百忠實于原文的譯文,翻譯的任務就完成了,翻譯的目標也就達到了。“創造性叛逆”對此提出新的思考維度,提出“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137),即譯文與原文一定存在某種程度的背離,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所謂百分之百忠實于原文的譯文。如此一來,“創造性叛逆”就把我們的目光引向翻譯以外的因素,讓我們看到決定翻譯效果和翻譯行為的成功與否不僅依賴于譯者個人的主觀努力與追求,而且還要受到語言、讀者、接受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制約。正如一部嚴肅的政治諷刺讀物《格列佛游記》,通過譯者的翻譯傳到另一個國家,卻變成一部輕松、愉快的兒童讀物;而一部在自己國家默默無聞的作品《牛虻》通過翻譯傳到中國,卻成為一部經典性的作品。這其中固然有譯者的努力,但又怎能離開讀者和接受環境(包括文化差異、意識形態等)的作用。“創造性叛逆”的觀點能拓展翻譯研究的視野,讓翻譯界一些聚訟不已的問題得到比較圓滿的解決。
在討論創造性叛逆與文學經典形成之間的關系時,特別是涉及創造性叛逆中與誤譯有關的某些個案時,引起從事文學翻譯的老翻譯家以及在高校從事實踐翻譯教學的教師的疑惑和不解,甚至抨擊。譬如,針對拙著或其他比較文學著作和教材中關于戈蒂耶和龐德誤譯的例子所作的分析,有觀點認為,“這種理論脫離中國翻譯實際,鼓吹一種病態的審美觀,聲稱翻譯可以脫離原作,誤譯、誤讀,甚至更有利于傳播與接受,從而在客觀上助長,甚至是教唆胡譯亂譯,導致翻譯質量的下降”(江楓2009:136)。這種觀點把創造性叛逆簡單地理解為對翻譯實踐的指導,卻不知道創造性叛逆并不是一個用來指導如何進行翻譯的方法和手段。還有些觀點提出要區分“好的創造性叛逆”和“破壞性的創造性叛逆”,提出要把握好創造性叛逆的“度”。這些討論其實是背離創造性叛逆的本旨,因為創造性叛逆是翻譯中的一個客觀存在,是對跨語言、跨文化傳播和接受中一個規律的揭示,它幫助我們更深刻地認識翻譯的實質,但與“該怎么譯”的問題無關。
2 “翻譯文學”:確立翻譯家和翻譯作品在國別文學中的地位
“創造性叛逆”的觀點是整個譯介學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翻譯文學中“創造性叛逆”現象的存在決定翻譯文學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存在,它不可能等同于外國文學,也決定翻譯文學應該在譯入語語境里尋找它的歸宿,譯介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引人注目的“翻譯文學是國別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觀點。對中國的翻譯文學而言,翻譯文學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論文《為“棄兒”尋找歸宿——論翻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謝天振1989)中,筆者首次明確地提出,“翻譯文學應該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這個觀點贏得國內以及海外學界的關注和肯定,但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對此觀點提出質疑:“沒有一部文學史會把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說成是本國文學作品”(施志元 1995:28);“(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論怎樣大,外國文學還是外國文學,怎么可能就成了‘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王樹榮 1995:12)
這是因為長期以來人們對翻譯文學的概念有一種模糊的認識,把翻譯文學混同于、等同于外國文學,而形成這種認識的深層原因則是因為人們只把文學翻譯視作語言層面的純技術性的符碼轉換,看不到翻譯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差異,也就模糊了翻譯文學的性質及其在國別文學史上的意義和地位,并進而抹殺翻譯家的文學貢獻。當然這種質疑也不奇怪,因為在上世紀70年代日本的《比較文學辭典》之前,似乎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本其他文學辭典收入過“翻譯文學”的條目。比較文學譯介學的研究首先揭示翻譯文學的學術價值,并把它確立為一條專門的學術術語。
在傳統的翻譯研究和文學研究中,翻譯文學往往處于一種無所歸屬、非常尷尬的境地。翻譯研究者只注意其中的語言現象,而不關心它的文學地位。而文學研究者一方面承認翻譯文學對民族文學和國別文學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卻又不給它以明確的地位——他們往往認為這是外國文學的影響,而沒有意識到翻譯文學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現象的存在。因此,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里,翻譯文學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在源語國的文學史里,翻譯文學就更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譬如,我們無法設想要讓法國文學史為傅雷、讓英國文學史為朱生豪或梁實秋留出一席之地。這樣,翻譯文學就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棄兒”。
然而,如果從語言學或者從傳統的翻譯學的角度看,我們僅僅發現文學翻譯只是一種語言文字符號的轉換,那么當我們從文學研究和譯介學的角度去審視文學翻譯時,就應該看到它所具有的一個長期以來被人們忽視的十分重要的意義,即:文學翻譯是文學創作的一種形式,也是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具有它相對獨立的藝術價值。
為了論證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相對獨立的藝術價值和意義,我們首先從文學作品可能具有多種不同的存在形式談起。一般而言,一部作品一旦經作家創作問世后,就具有其最初的文學形式。如經莎士比亞創作成功的《哈姆雷特》就具有戲劇的形式;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同時也就賦予這部作品以長篇小說的形式。然而,這些形式都僅僅是這兩部作品的最初形式,而不是它們的唯一形式。譬如,經過蘭姆姐弟的改寫,《哈姆雷特》獲得散文故事的形式;進入20世紀以后,《哈姆雷特》被一次次地搬上銀幕,這樣,它又具有電影的形式;曹雪芹的《紅樓夢》也有同樣的經歷:它被搬上舞臺,取得地方戲曲如越劇、評彈等形式,它也被搬上銀幕和熒屏,于是又取得電影、電視連續劇的形式。
至于比較文學翻譯與改編,如果說改編大多是原作文學樣式的變換(小說變成電影,或劇本變成散文故事等),那么文學翻譯主要是語言文字的變換。此外,它們還有很多的相似之處: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有原作作為依據,而且都有介紹、傳播原作的目的,尤其改編或翻譯的作品是文學經典或文學名著。
但是,翻譯與改編又有實質性的區別:改編是通過文學樣式的變換把原作引入一個新的接受層面,但該接受層面與原作的接受層面大多仍屬于同一個文化圈,僅僅是在文化層次、審美趣味或受眾對象等方面有差異。譬如長篇小說《紅樓夢》的讀者與越劇《紅樓夢》的觀眾或聽眾就屬于相同的漢文化圈;而翻譯卻是通過語言文字的轉換把原作引入一個新的文化圈,在這個文化圈里有與原作所在文化圈相異甚至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有相異甚至相去甚遠的審美趣味和文學欣賞習慣,譬如莎劇在中國的譯介。翻譯的這一功能意義是巨大的,它使翻譯遠遠超過改編。埃斯卡皮指出,“翻譯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里”(指語言),“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它不僅延長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138)。
回顧人類的文明歷史,世界上各個民族的許多優秀文學作品正是通過翻譯才得以世代相傳,也正是通過翻譯才得以走向世界,為各國人民所接受。古希臘羅馬文學中的荷馬史詩《奧德賽》《伊利亞特》,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喜劇,亞里士多德、維吉爾等人的作品,這些舉世公認、然而卻是用已經“死去的語言”——拉丁語寫成的杰作,假如沒有英語等其他語種的譯本,也許它們早就被湮沒無聞了。當今世界上有很多的文學經典作品主要就是以譯作的形式在世上存在、流傳,在世界各國被認識、被接受、被研究。古希臘羅馬的文學作品如此,非通用語種文學家的作品,如易卜生的戲劇、安徒生的童話如此,有時甚至連本國、本民族歷史上的一些作品也如此。如托馬斯·莫爾的名作《烏托邦》,它的主要存在形式就是英譯本,因為原作是拉丁文。芬蘭文學的奠基人魯內貝格的詩是以芬蘭文譯作的形式存于芬蘭,因為原作是瑞典文。如果在把譯作視為與原作改編后的其他文學樣式一樣是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的問題上,人們比較容易達成共識,那么在涉及到這些無數以譯作形式存在的文學作品的總體——翻譯文學的國別歸屬問題時,人們的意見卻開始出現分歧。分歧的焦點在于:翻譯文學究竟是屬于本國文學還是外國文學;或者更確切地說,翻譯文學能不能視作國別(民族)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我們中國文學來說,也就是翻譯文學能不能視作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翻譯文學存在的這些分歧,在某種程度上完全可以理解,這是由于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對翻譯文學相對獨立的地位尚未有足夠的認識。在譯介學提出翻譯文學的國別歸屬問題之前,國內學術界還從來沒有把翻譯文學的定義、范疇、歸屬等作為學術問題提出來討論過,人們從來就沒有意識到在外國文學與國別(民族)文學之間還存在一個“翻譯文學”。在不少人(包括相當一部分的專家、學者)的眼中,翻譯文學實際上就是外國文學的代名詞。
譯介學對翻譯文學概念的闡釋為解決學界對翻譯文學的一系列困惑和質疑提供理論依據:首先是深入分析文學翻譯與非文學翻譯之間的差別,其次是提出確定文學作品國籍歸屬的依據。
文學翻譯與非文學翻譯有實質性的差異:文學翻譯屬于藝術范疇,而非文學翻譯屬于非藝術范疇。非藝術范疇的哲學、經濟學等學科著作的翻譯,也包括佛經等宗教典籍的翻譯,其主要價值在于對原作中信息(理論、觀點、學說、思想等)的傳遞,譯作把這些信息正確、忠實地傳達出來就達到它的目的。這里有必要特別強調的是,當譯作把這些非藝術范疇的哲學、經濟學、佛學等著作所包含的信息傳達出來后,這些信息,具體地說,也就是這些著作中的理論、觀點、學說、思想等,它們的歸屬并沒有發生改變。
然而,藝術范疇的文學作品的翻譯則不然,它不僅要傳達原作的基本信息,而且還要傳達原作的審美信息。如果說屬于非藝術范疇作品中的基本信息(理論、觀點、學說、思想,以及事實、數據等)是一個具有相對界限也相對穩定的“定量”,那么屬于藝術范疇的文學作品中的基本信息(故事、情節等)之外的審美信息卻是一個相對無限的、有時甚至是難以捉摸的“變量”。而且,越優秀的文學作品,其審美信息越豐富,譯者對它的理解和傳遞也就越難以窮盡(在詩歌翻譯中這一點尤其突出),需要譯者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各顯神通對它們進行“開采”。在這個意義上,翻譯家對文學作品中審美信息的“傳遞”與作家、詩人對生活中信息的“傳遞”稱得上異曲同工。譬如,一個普通人可以說,“昨天晚上雨很大,風很大,把室外的海棠花吹打掉不少,但葉子倒長大了”,以此完成對生活中一個信息的傳達。但詩人就不然,他(她)要用另一種語言來傳遞信息:“昨晚雨疏風驟。……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從而使他(她)的傳遞不僅包含一般的信息,而且還有一種審美信息,給人以藝術的享受。文學翻譯也如此,如果它僅僅停留在對原作一般信息的傳遞,而不調動譯者的藝術再創造,這樣的文學翻譯作品不可能有藝術魅力,當然也不可能給人以藝術的享受。因此,如果說藝術創作是作家、詩人對生活現實的“藝術加工”,那么文學翻譯就是對外國文學原作的“藝術加工”。
譯介學對確定文學作品國籍的依據進行探索,這個問題是一個新問題,因為傳統的文學研究者通常是在國別文學的框架內進行他們的研究,作品的國籍歸屬很清楚。然而問題是:你為何在編寫中國文學史時選擇魯迅、茅盾,而不選高爾基、賽珍珠呢?是寫作時所用的語言文字嗎?顯然不是,否則世界上凡是用英文寫作的作家豈不全成了英美作家?是作品的題材內容嗎?也不是,否則賽珍珠就可視作中國作家了,我認為唯一的依據就是作家的國籍。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展開對翻譯文學作品的作者這一問題的探討。當我們手捧一本中文版長篇小說《高老頭》時,我們往往會脫口而出它的作者是巴爾扎克,但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因為這忽視譯者的存在。須知巴爾扎克不會用中文寫作,所以嚴格而言,我們此時所讀的作品是翻譯家傅雷(或其他譯者)在巴爾扎克法文原作的基礎上再創造出來的作品。由此可見,翻譯文學作品的作者應該是翻譯家,而根據翻譯家的國籍,我們也就不難判定翻譯文學作品的國籍歸屬了。
3 “翻譯文學史”:開拓中外文學關系的新領域
根據翻譯家的國籍,為翻譯文學在國別文學內找到一席之地,但這并不意味著翻譯文學與本國、本族創作文學就是一回事。譯介學研究指出,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是中國文學內相對獨立的一部分。這樣,既肯定翻譯文學在國別文學中的地位,同時還指出翻譯文學在國別文學中相對獨立的地位,進而引出如何編撰翻譯文學史的問題。
在譯介學對“翻譯文學史”概念進行深入分析和闡釋之前,國內學界對翻譯文學史的理念及其編撰基本上沒有給予過特別的關注,在實際的編撰中還經常把文學翻譯史與翻譯文學史相混淆,即書名為“翻譯文學史”,實質為文學翻譯史。譯介學分析兩者的本質差異:文學翻譯史以翻譯事件為核心,關注翻譯事件和歷史過程歷時性的線索;而翻譯文學史不僅注重歷時性的翻譯活動,更關注翻譯事件發生的文化空間、譯者翻譯行為的文學文化目的以及進入譯入國文學視野的外國作家作品的接受、傳播和影響等問題。翻譯文學史將翻譯文學納入特定時代的文化時空中進行考察,闡釋文學翻譯的文化目的、翻譯形態、為達到某種文化目的翻譯上的處理以及翻譯的效果等,探討翻譯文學與民族文學在特定時代的關系和意義。這樣,翻譯文學史實際上還是一部文學關系史、文學接受史、文學影響史,從而為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展現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針對翻譯文學史如何編撰的具體問題,譯介學指出,翻譯文學史實質也是一部文學史,因此在編撰翻譯文學史時應該把一般文學史都有的3個基本要素,即作家、作品和事件納入視野。對翻譯文學史來說,這3個基本要素又體現為:作家——翻譯家和原作家(是“披上譯入國外衣”的原作家);作品——譯作;事件——文學翻譯事件及翻譯文學在譯入國的傳播、接受和影響等。這3者是翻譯文學史的核心,而由此所展開的歷史敘述和分析就是翻譯文學史的任務,它不僅要描述文學翻譯在譯入國的基本面貌、發展歷程和特點,還要在譯入國文學自身發展的圖景中對翻譯文學的形成和意義作出明確的界定和闡釋。
對中國翻譯文學史來說,認定和承認翻譯家在翻譯文學史里的主體性和地位很重要。20世紀中國出現一批卓有成就的翻譯家,如林紓、嚴復、蘇曼殊、馬君武、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傅東華、朱生豪、傅雷、梁實秋,等等,他們的翻譯活動不僅豐富了中國翻譯文學史的內容,同是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內容,影響并改變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和面貌,他們的貢獻在翻譯文學史里應該得到充分的展示。
“披上譯入國外衣的外國作家”是另一個須要關注的對象,他們是翻譯文學的本和源,要全面展示翻譯文學史的進程和成就離不開對這些“披上譯入國外衣的外國作家”在譯入國的譯介和接受情況的介紹和分析。從最初的譯介到他們的作品在各個時期的翻譯出版情況、接受的特點等,尤其是某具體作家或作品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譯介情況,都應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描述和闡釋。以中國翻譯文學史為例,如有些作家作品是作為世界文學遺產被譯入到中國,而有些則是契合當時的文化、文學需求,作為一種聲援和支持,促使特定時代的文學觀念或創作方式的轉變,如新時期外國現代文學的翻譯等。另外,有些外國作家進入中國的形象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如拜倫開始是以反抗封建專制的“大豪俠”形象進入中國;莎士比亞是以“名優”和“曲本小說家”的形象與中國讀者結識;盧梭進入中國的身份是“名賢先哲”“才智之士”“名儒”;尼采進入中國的身份是“個人主義之至雄杰者”“大文豪”“極端破壞偶像者”,等等。
毫無疑問,作為完整形態的翻譯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翻譯文學史必須關注翻譯文學在譯入國文化語境中的傳播、接受、影響、研究的特點等問題,從而為日益頻繁的國際文化交流提供深刻的借鑒和歷史參照。正如歌德所說:“原作和譯作之間的關系,最能反映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Goethe 1973:10)。可見,翻譯文學史的這種性質決定它實際上也是一部文學交流史、文學影響史和文學接受史。
4 “譯入”與“譯出”:換一個方向看翻譯
在譯介學理論之初,其關注的焦點基本局限在譯入語語境內,尤其是對翻譯文學和翻譯文學史的研究。近年來隨著文化外譯命題的提出,譯介學研究的視野也發生相應的拓展。由于譯介學理論本來就關注文學文化跨語言、跨國界傳播的本質,也特別關注制約文學文化在譯入國語境中的接受、傳播、影響的各種因素,因此譯介學對文化外譯的理解與闡釋比傳統的翻譯研究顯得更加深入。如討論中國文學文化的外譯,我們都知道,新中國建國將近七十年來,我們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中國文學、文化典籍的外譯,希望以此推動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然而卻收效甚微,一直未能取得較為理想的預期效果。原因何在?傳統的翻譯研究把它歸罪于譯者,認為是譯者的外語能力太差,沒能把作品翻譯好。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觸及其中的根本原因。其實我們有相當數量的譯作其質量(從對原文的忠實度、譯文的語言水平等角度看)很好,但并沒有很理想地“走出去”,即被譯入語國家的讀者廣泛接受并在譯入語國家產生影響。譯介學認為,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1)對文學、文化跨語言傳播與交流的基本譯介規律缺乏應有的認識;(2)不了解“譯入”與“譯出”這兩種翻譯行為之間的實質差別。
譯介學指出,在一般情況下,文化交流總是由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譯介,而且總是由弱勢文化語境里的譯者主動把強勢文化譯入自己的文化語境里。法國學者葛岱克指出:“當一個國家在技術、經濟和文化上屬于強國時,其語言和文化的譯出量一定很大;而當一個國家在技術、經濟和文化上屬于弱國時,語言和文化的譯入量一定很大。在第一種情況下,這個國家屬于語言和文化的出口國,而在第二種情況下,它則變為語言和文化的進口國”(葛岱克2011:10)。在歷史上,當中華文化處于強勢地位時,我們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就曾紛紛主動地把中華文化譯入他們各自的國家,當時我國語言和文化的譯出量確實很大。然而,當西方文化處于強勢地位、中華文化處于弱勢地位時,譬如在我國的晚清時期,我國的知識分子則積極地把西方文化譯介給我國的讀者,于是我國語言和文化的譯入量變得很大。今天在整個世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仍然處于強勢地位,這從各自國家翻譯出版物的數量中可見一斑:數年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統計資料表明,翻譯出版物僅占美國全部出版物總數的百分之三,占英國全部出版物總數的百分之五。而在我們國家,我雖然沒有看到具體的數據,但粗略地估計一下,說翻譯出版物占我國出版物總數將近一半恐怕不算太過。
翻譯出版物占一個國家總出版物數量比例的高低還從另一個方面折射出這個國家對外來文學文化的態度和立場。翻譯出版物在英美兩國及其他英語國家總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很低,這反映出英語世界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文學文化)的那種強勢文化國家的心態和立場。可見,要讓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其實質首先是希望走進英語世界)實際上是一種“逆勢”譯介行為,這樣的譯介行為要取得成功就不能僅僅停留在把中國文學、文化典籍翻譯成外文、交出一份所謂的“合格的譯文”就算完事,而必須從譯介學規律的高度全面審時度勢并對之進行合理的調整。
譯介學指出,譯入(in?coming translation)與譯出(out?going translation)這兩種翻譯行為并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只是翻譯方向不同,而是兩者之間有實質性的差別:前者(譯入)是建立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內在的對異族、他國文學、文化強烈需求基礎上的翻譯行為,而后者(譯出)在多數情況下則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廂情愿地向異族、他國譯介自己的文學和文化,對方對你的文學、文化不一定有強烈的主動需求。由于譯入行為所處的語境對外來文學、文化已經具有一種強烈的內在需求,因此譯入活動的發起者和具體從事譯入活動的譯介者考慮的問題就只是如何把外來的文學作品、文化典籍譯得忠實、準確和流暢,也就是傳統譯學理念中的交出一份“合格的譯作”,而基本不用考慮譯入語環境中制約或影響翻譯行為的諸多因素。譯者只要能交出“合格的譯作”,他們的翻譯行為及其翻譯成果就自然而然地能夠贏得讀者,贏得市場,甚至在譯入語環境里產生一定的影響。過去兩千多年來,我們國家的翻譯活動基本上是以外譯中為主的譯入行為。無論是歷史上長達千年之久的佛經翻譯,還是清末民初以來這一百多年間的文學名著和社科經典翻譯,莫不如此。
但譯出行為則不然,由于譯出行為的目的語方對你的文學、文化尚未產生強烈的內在需求,更遑論形成一個比較成熟的接受群體和接受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譯出行為的發起者和譯介者如果也像譯入行為的發起者和譯介者一樣,只考慮譯得忠實、準確、流暢,而不考慮、不關注其他許多制約和影響翻譯活動成敗得失的因素,包括目的語國家讀者的閱讀習慣、審美趣味、目的語國家的意識形態、詩學觀念,以及譯介者自己的譯介方式、方法、策略等因素,那么這樣的譯介行為恐怕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兩千多年來的譯入翻譯實踐(從古代的佛經翻譯到清末民初以來的文學名著、社科經典翻譯)中形成的譯學理念——奉“忠實原文”為翻譯的唯一標準、拜“原文至上”為圭臬等——其影響太深,他們以建立在譯入翻譯實踐基礎上的這些翻譯理念、標準、方法論來看待并指導今天中國文學、文化典籍的譯出行為,于是繼續只關心語言文字轉換層面“怎么譯”的問題,而甚少考慮翻譯行為以外的諸種因素,如傳播手段、接受環境、譯出行為目的語國家的意識形態、詩學觀念,等等。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建國以來我們在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一事上投入那么多的人力、財力、物力,而收效甚微的原因了。“簡單地用建立在‘譯入’翻譯實踐基礎上的翻譯理論(更遑論經驗)來指導當今的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譯出’翻譯實踐,那就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成功。”(謝天振2014:13)
5 譯介學:當代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發展的必然趨勢之一
從以上所述不難發現,譯介學研究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翻譯研究,它關注的對象已經超出傳統翻譯研究關心的對象——兩種語言文字轉換這樣一些具體的問題。譯介學研究已經具有文學研究、文化研究的實質,它大大地拓展我們研究者的學術視野。而一旦跳出傳統翻譯研究的框框,也即局限在文本以內的語言文字的轉換,我們就會進入文化研究的層面上,翻譯研究也會與當前國際學術界的兩大轉向——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不謀而合。
譯介學研究為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打開一個新的、更加廣闊的研究空間,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課題得到比以前更深刻、更具體、更清晰的闡釋。譬如,文學關系歷來是傳統比較文學研究中最主要的一個課題,但以前的文學關系研究要么致力于尋求兩個民族或國家文學影響與被影響的“事實聯系”,要么比較兩個民族或國家文學的異同,然后從中推測它們相互間的關系。譯介學研究則不然,它以多元系統論為基礎,提出一系列原來一直被學術界忽視的問題,如為什么有些國家的文化更重視翻譯,翻譯進來的東西多,而有些國家的文化則相反?哪些類型的作品會被翻譯?這些作品在譯入語系統中居何地位?與其在源語系統中相比又有何差異?我們對每個時期的翻譯傳統和翻譯規范有何認識?我們如何評估翻譯作為革新力量的作用?蓬勃開展的翻譯活動與被奉作經典的作品,兩者在文學史上是何關系?譯者對自己的翻譯工作作何感想,他們的感想又通過何種方式傳達出來?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對于我們深入思考文學關系和譯介的規律性等問題極富啟迪意義。
譯介學研究經常提到的“意識形態、贊助人、詩學”三因素理論,同樣揭開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和翻譯研究的新層面。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外國文學界曾經圍繞英國通俗長篇小說《尼羅河上的慘案》的譯介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從而對我國新時期國外通俗文學的譯介產生很大的影響,而這場風波的背后就是我國特有的贊助人機制在起作用。而“詩學”(或譯“文學觀念”)因素的引入,對于解釋為什么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大量譯介現實主義文學作品,而進入80年代后又開始大量譯介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顯然提供一個很好的富有說服力的理論視角,同時也是一個饒有趣味的研究課題。
當前,國際比較文學研究已經出現翻譯轉向的明顯發展趨勢,而國內比較文學界的譯介學研究也同樣方興未艾。實踐證明,無論是國際比較文學研究的翻譯轉向還是國內比較文學界的譯介學研究都給當代國內外的比較文學研究帶來勃勃生機。在這樣的形勢下可以預期,隨著譯介學研究的進一步展開,隨著國內譯學界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推進和完善,我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必將迎來一個新的、深入發展的契機,并展示出廣闊的發展前景。
注釋
①筆者對譯介學理論的探索與倡導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先是在學術會議上和在相關院校講學時進行闡述,后整理成文,于1989年起陸續發表,有《為“棄兒”尋找歸宿——論翻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1989)、《翻譯文學史:挑戰與前景》(1990)、《論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1992)、《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1992)等。
②實際上在林譯之前已經有相關譯本,但影響沒有林譯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