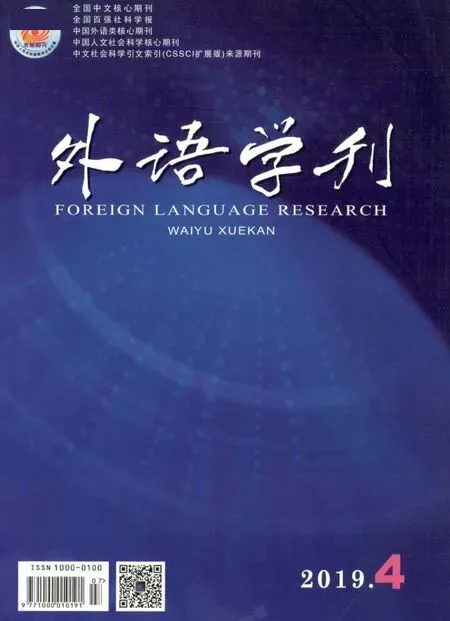《在語言中的盤旋》簡介
劉利民
(四川大學,成都 610064)
本書重新審視先秦名家的思想,對名家的“詭辯”命題進行全新的詮釋,為名家“專決于名”的思辨理性正名,進而闡明思辨理性不是西方語言、乃至西方文化的專利,它完全可能在漢語語言條件下產生。
全書從現代認知語言學和西方語言哲學的交叉學科視角,構建出“語言性認知操作三模式論”,以論證思辨理性作為一種思維闡釋:任何民族,無論其語言形態是什么樣,只要進入關于語言表達式意義本身的反思,就可能產生理性思辨性的哲學。基于這一認識,本書探討西方哲學產生的語言根源,同時對先秦主要思想流派關于語言的哲理思考進行分析,最后產生對名家“詭辯”命題理性主義實質的新解讀。
作者認為,中國古代哲學的確從未提出西方哲學那樣的“ontology”問題,沒有出現伴隨著關于“being as being”的追問而產生的嚴格的思辨理性。在這方面,西方語言的形態特征,如其重形式的句法、系詞的多重意義功能等確實有助于西方思想家由句法進入形而上學的思考。但沒有理由因此推之,漢語由于缺乏形式化特征而阻礙了中國發展出理性思辨哲學。語言雖然具有民族特點,各不相同,但是思維卻是全人類共同的。漢語與西語雖然不一樣,但是中西方人用語言標志的心靈的經驗以及心靈的經驗所反映的那些東西是共同的。
具體而言,人的認知活動主要體現為認知主體的語言操作,語言操作可以按其問題形態分為3個層面,每一個層面所針對的范疇不一樣,因而產生的問題也不一樣:(1)在具體操作語言層面,人用語言對世界進行經驗和操作,語言的意義以直接感知的事實而確定;(2)在抽象概念化操作語言層面,人用語言對來自感知的材料進行抽象操作,以獲取關于世界事物本質屬性的認識;(3)在形而上語言層面,人用語言就語言本身進行追問,以反思語言意義的確定性;這實質上是對知識的確定性的哲學反思。本書認為哲學是普遍的,因為人類的認知具有普遍性。
西方哲學的ontology本身就是從這種關于語言的結構和意義的操作中盤旋出來的形而上理性思維;古希臘哲學正是從對語言的思辨中形成關于什么是“是”的形而上思想方法。作為關于概念的邏輯分析的理性主義思想模式并不一定只能有從關于“是”的思辨中產生這一種路徑。只要不是囿于經驗性認知操作,而是進入語言抽象性認知操作,那么理性主義思想應該能夠在包括漢語在內的任何語言土壤中產生。事實上,中國哲學家的確曾經通過純語言思辨試圖進入理性思辨。在先秦“名實之辯”運動中獨樹一幟的名家哲學就是很典型的語言邏輯的思辨性哲學思考。
本書對《公孫龍子》的5篇文章以及莊子所記錄的名家“詭辯”命題的分析借用“使用”“提及”的語言哲學分析技術,并加以創新性運用,合理地解釋公孫龍等先秦思想家之所以提出“詭辯”命題的原因:古漢語缺乏標點符號、形式化的詞類、句法標記,使他們不得不以這種方式將自己的思考劃定在概念層面,而不是具體所指層面。本書不僅合理地闡釋名家思想的理性主義思想傾向,而且指出中國古代思想通向關于本體論、認識論問題的哲學思辨的語言路徑。
遺憾的是,由于古漢語缺乏標點符號和西方語言那樣的形式變化,名家的哲學思想不易被人所理解,給人以玩奇辭,以相撓滑的印象;同時,先秦哲學對于人倫、道德、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及其入世的、經世致用的精神使名家的理性思辨傾向頗具另類色彩。雖然名家本身也是從“名”與“實”的關系入手進入抽象思考,但其類似于異端的思維模式卻招來批判與拒斥。這是中國古代沒有能夠在語言中盤旋出以本體論、認識論為核心的理性主義哲學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