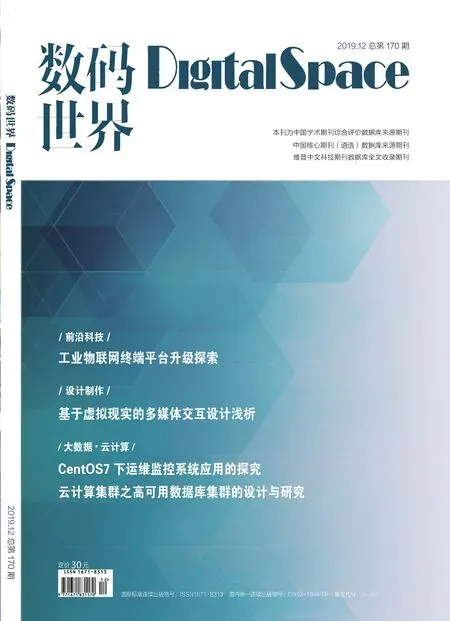錯彩鏤金的美和芙蓉出水的美之間的區別和聯系
房真杰 洛陽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藝術意境的創成,既須得屈原的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的超曠空靈。纏綿悱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萬物的核心,所謂“得其環中”。超曠空靈,才能如鏡中花,水中花,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所謂“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這不但是盛唐人的詩境,也是宋元人的畫境。
一般來說,主張積極入世,重視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儒家思想講究人工雕飾之美,所以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的藝術家大都偏重于“錯彩鏤金”的美。而提倡自然天成,反對人為雕飾之痕的道家思想則更講究“無為而為”的渾然天成之美,所以受老莊以及魏晉以來玄學思想影響較深的藝術家一般反對人工斧鑿而提倡“芙蓉出水”的美。魏晉六朝是一個轉變的關鍵,劃分了兩個階段。在魏晉六朝以后出現了深刻的“轉向”, 是一個轉變的關鍵。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人的美感走到了一個新的方面,表現出一種新的美的境界。那就是認為“初發芙蓉”比之于“錯采鏤金”是一種更高的美的境界。在藝術中,要著重表現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從兩種美并駕齊驅,到將其中一種美視為更高境界,這個轉變也是非常深刻的。這種轉變并不是空穴來風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儒學信仰的動搖和中央集權的削弱,藝術家、思想家們反對漢末腐敗的政治,沖擊虛偽腐朽的守舊觀念,提倡理性和個人的真實情感,并用老莊思想抨擊舊的“禮教”和繁瑣的經學,玄學興起。“玄學”的興起、老莊哲學和佛教的流行改變了文化的面貌,“越名教而任自然”成為普遍追求。它最重要的價值在于顯示認得自覺意識,突出個人存在價值,對哲學和美學等領域影響極其深遠。所謂“自覺“的觀念,是指自我存在的價值觀,在魏晉南北朝以前,美術還未完全脫離實用的目的,只有當美術家清楚的意識到人的存在價值時,他們對手中的書畫形式形式才能形成自覺的觀念。在頻繁改朝換代的時期,對抱有儒家治平理想的政治家來說,更難找到精神上的歸宿,人的自覺意識因此喚發出來,思考對于不朽理想的追求。當時人們關心的不再是人格的完善,而是人物的風采神韻。
六朝時的著名詩評家鐘嶸很明顯贊美“初發芙蓉”的美。陶潛作詩和顧愷之作畫,都是突出的例子。王羲之的字,也沒有漢隸那么整齊,那么有裝飾性,而是一種“自然可愛”的美。這是美學思想上的一個大的解放。詩、書、畫開始成為活潑潑的生活的表現,獨立的自我表現。
唐代在唐初四杰之時,還繼承了六朝之華麗,但已有了一些新鮮空氣。經陳子昂到李太白,詩歌完全表現出了“初發芙蓉”的美的理想。李白詩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這里的“清真”也就是清水出芙蓉的境界。杜甫也有“直取性情真”的詩句。司空圖《詩品》雖有雄渾的美的主張,但他說過“生氣遠出”、“妙造自然”的詩歌理想,也就是“清水出芙蓉”的境界。
到了宋代,蘇東坡用奔流的泉水來比喻詩文,要求詩文的境界要“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平淡并不是枯淡,中國向來把玉作為美以至于人格美的理想,玉的美就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美。蘇軾又說:“無窮出清新。”“清新”與“清真”也是同樣的境界,即“初發芙蓉”的境界。 總而言之,魏晉以后這種“初發芙蓉”的審美理想受到歷代大家的推崇,漸漸成為藝術創造中的正宗和主潮。
回顧中國藝術的獨特面貌,追溯中國美學的特異觀念,甚至考察我們民族性格的許多特征,都不得不聯系到這一“轉向”。兩個“轉向”也許本無關聯,不過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它們都發生在魏晉時期。一個是崇尚神似韻味而輕視形似寫真,一個是從崇尚“初發芙蓉”而不再留戀“錯彩鏤金”,兩者均以魏晉為分野。難怪美學史上通常說魏晉是中國藝術自覺的時代。也許我們可以認為,重寫意而輕寫實,重“初發芙蓉”而輕“錯彩鏤金”,兩者合流深刻地塑造了中國藝術的獨特形態,進而締造和完善了中國美學的基本觀念。
從三代銅器那種整齊嚴肅、雕工細密的圖案,我們可以推知先秦諸子所處的藝術環境是一個“錯采鏤金、雕繢滿眼”的世界。先秦諸子對于這種藝術境界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對這種藝術取否定的態度,如墨子,認為是奢侈、驕橫、剝削的表現,使人民受痛苦,對國家沒有好處,所以他“非樂”,即反對一切藝術。又如老莊,也否定藝術。莊子重視精神,輕視物質表現。老子說:“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另一種對這種藝術取肯定的態度,這就是孔、孟一派。藝術表現在禮器上、樂器上,孔、孟是尊重禮樂的。但他們也并非盲目受禮樂控制,而要尋求禮樂的本質和根源,進行分析批判。總之,不論肯定藝術還是否定藝術,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種批判的態度,一種思想解放的傾向。這對后來的美學思想,有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