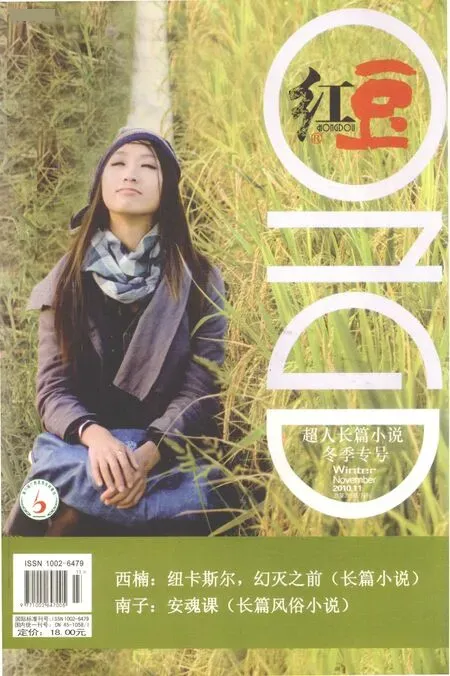幸福的婆水拐
黃惠娟
在記憶的深處,總會有一種美食填滿過往的味蕾,這種味蕾會讓你想張開全身的毛孔、全身的細胞去感知它、去擁抱它。在三月不知肉味的年代,一種讓人念念不忘的美食,是讓人身心愉悅的最好良藥,吃上它就會得到一種奇異的平靜與安寧。
婆水拐是我從小就特別喜歡的食物。小時候因兄弟姐妹多,僅靠阿爸一個人的工資,難以支撐整個家庭十幾口人的開支。幸好家里田地多,肉雖少,但大米、青菜、紅薯、芋頭之類的食物頗多,所以吃飽是不成問題的。但因為胃里油水少,對肉尤其期待,因此特別期盼下班歸來的阿爸,在二十八寸鳳凰牌自行車的車頭上掛著用竹篾串好的一塊長條豬肉。而肉餡婆水拐更是難得一吃的八珍玉食。
家里做婆水拐一般是在一年中的四個觀音誕以及慶豐收時。在我國民間,慶祝觀音誕的日子有四個:農歷二月十九,觀音的生日;農歷六月十九,觀音出家之日;農歷九月十九,觀音成佛之日;農歷十一月十九,是恭迎日光菩薩圣誕。雖然后一個與前三個不是同一神仙,但家鄉人習慣把這四個節日統稱為觀音誕。
做婆水拐是大費周章的一件事。觀音誕的前一天,阿婆(奶奶)和阿媽就要做好準備工作了。先把糯米、粳米提前按7︰3的比例洗凈,泡好。小時候見阿媽早上洗好米,把米浸泡在挑水用的木桶里,到下午把泡發好的米倒出,放在圓筲(筲箕)里面瀝干水。在泡米的那段時間里,阿媽去菜地里拔蒜,沒有蒜的季節,就用韭菜或者小蔥代替。拔好的蒜先挑到村里的池塘剝去第一層蒜衣和去掉根須,接著把泥洗掉,然后再用糞箕(當然此處的糞箕不是挑過糞的,而是專用來挑菜和挑草的干凈的糞箕)晃悠悠地把蒜挑回家。在阿媽拔蒜、洗蒜、挑蒜的時候,我總會屁顛屁顛地跟在后面,總想出點力幫忙可以快點吃上婆水拐。但很多時候,我總是幫倒忙。因為拔蒜不得要領,我總是把蒜拔斷,留下一大截在土里。阿媽就得把埋在土里的那截蒜拔出來,在被太陽曬得硬硬的地里拔半截蒜比拔整根蒜難。阿媽只好先教我如何拔蒜,她說要把手握到靠近地的根部再拔,而且要反手握蒜。只見阿媽一只手抓住近根部的地方,輕輕松松就把蒜拔了出來,拔出來后再抖抖蒜根上的泥巴。孩童的我也想學阿媽單手拔蒜,無奈把蒜莖捏扁捏出汁,還是拔不出來。只好用雙手抓住蒜,把屁股撅高,使出吃奶的力氣想把蒜拔出來。應該是出力不得要領,有時好不容易把蒜拔出來了,卻人仰馬翻。我就順勢坐在地里,捂著通紅的小手靜靜地觀看地壟上行走的螞蟻。這時候阿媽也不會打擾我,她在地里忙,有時候我盯著阿媽看。那時的阿媽多好看啊,成熟的韻味就像飽滿的水蜜桃,有時候我也盯著螞蟻浮想聯翩,反正阿媽干完活肯定會叫我回家,有時盯著盯著我就睡著了。
阿媽把蒜挑回家后,就是哥和姐大展身手的時候了。哥從搖井里搖水,姐用圓形的大木盆一邊接水,一邊把阿媽洗過一次的蒜沖洗干凈。一根根穿著綠長裙的蒜在姐的手中翻轉,被潔凈的井水沖洗得越發青翠欲滴,在午后的陽光下盡情地舒展它們窈窕的身姿,特有的蒜香撲面而來,在井邊搖水的哥哥忍不住折一段生蒜來吃。生蒜若能蘸點鹽來吃,味道會更好,而我絕對是那個被叫去拿鹽的人。生蒜蘸鹽,咸辣入口,也頗有一番滋味,似乎吃了就會蒜氣沖天,從而就會讓哥哥牛氣沖天,那哥哥搖水就會搖得更帶勁。接著哥、姐會把沖洗干凈的蒜,放在圓形的大簸箕里,抬到屋檐下晾干。
到了傍晚,阿婆和阿媽就到老屋去把石臼和木杵刷干凈,用木碓把米搗成米粉。木碓就像一個蹺蹺板一樣,中間有一個支點,一上一下地工作,用重的那一端把米粒搗成粉末。此時,阿媽在木碓那邊用單腳踩木杠,阿婆在石臼旁時不時地把泡發晾干的米加進石臼,讓木碓頭把米搗成粉末。這樣需要幾個小時才能把米搗好。米搗好后,阿婆、阿媽她們還要經過另一道工序,把搗好的粉末過篩,留下精華部分,然后在大簸箕里晾開,前一天的工作才算完事。
第二天一早,阿媽開始剁蒜、剁肉、剁魚。姐把灶火燒熱,阿媽便開始炒餡。我們家鄉把餡叫做“芯”,所以婆水拐可叫做“蒜籺”,也可叫做“芯籺”。炒好的餡香氣四溢,我常常禁不住誘惑,蹭到灶臺旁,阿媽準會用小勺子舀一勺餡吹冷喂進我嘴里,笑瞇瞇地說:“饞吃鬼。”而我也因為吃了那一勺久違的葷,高高興興、蹦蹦跳跳地跑到一邊,去逗早已垂涎三尺的小狗玩。
接下來就到揉面的時候了。阿媽用開水把四分之一的生米粉揉成小粉團,再分成幾個小擠子,壓平,放入開水里煮熟,然后把煮熟的粉團撈出,放進裝在大簸箕的生米粉里,就著生粉拉扯燙手的粉糊,然后揉搓,揉成光滑的大粉團,揉十幾斤粉的粉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揉好粉團后,年輕的阿媽總會汗水濕透衣背,那時我能做的事就是拿毛巾幫阿媽擦擦汗,也總會得到阿媽的夸贊。“真乖!”阿媽揉粉團的時候總會預留些生粉,以便粉團粘手時可用來“脫手”。這邊揉好粉團,那邊的餡已不再燙了,這樣就可以開始包婆水拐了。
家鄉的婆水拐形狀像餃子,但是比餃子大,所以也有人稱之為“落水餃”。與北方的餃子相比,我們更喜歡大米制做的、糯糯的婆水拐。阿媽從大粉團那捏出一個乒乓球大小的小粉團,兩手掌揉成小圓球,然后放在大簸箕上沾點生粉壓平,再拿起來,左手握住壓平的小粉團,右手拇指放在它的中間,以便引導其余四指不停地圍繞這個支點轉動,直到這小粉團在阿媽的手上像施了魔法般變成個小碗的形狀。接著把餡舀進這個捏好的“小碗”里,餡八分滿即可,餡過多湯汁會溢出來,“小碗”也會被撐破。最后,把“小碗”的邊緣兩邊對捏,一個落水包就包好了。其實,我們都管這粉團叫“籺皮”,籺皮的厚度決定著婆水拐的口感。太厚,則嘗不出餡的鮮美;太薄,籺皮會被煮爛,剩下的粘在籺皮上的那點所剩無幾的餡也淡而無味。
等到包完婆水拐,把水燒到八九分開后就可以下鍋煮了。當然也可以用菜葉包好蒸來吃,還可以用油煎來吃,但我們更喜歡用水煮來吃。似乎用水煮,吃完婆水拐,再舀點煮過婆水拐的籺水來喝,那才是正確的吃法和正宗的味道。特別是那種用干竹葉或禾稈生火煮出的婆水拐,味道尤為鮮美。小時候,看到婆水拐下鍋了,心里便會很急,老是嘀咕到底要煮到什么時候才可以吃。阿媽告訴我們,當婆水拐“婆”(音)起來時就基本上熟了。于是就一直眼巴巴地盯著鍋里,希望這些頑皮的婆水拐不要再浮在水里,趕緊“婆”起來。孩童時代,眼里的熱切,也都付諸行動中,向灶臺旁靠近,就再也挪不開腿,頻頻往鍋里引頸而望。好不容易等到它們一個個露出雪白發亮的身體,阿媽說再等上一兩分鐘,心急吃不了熱豆腐。聽了阿媽的話,只好無可奈何地把欲飛流直下的口水拼命往回咽。小時候一直在想,稱為“婆水拐”的它們與“婆”和“拐”到底有什么關聯呢?在我們那讀音“婆”(不是指人的時候)有浮起來的意思,也就是說當婆水拐“婆”(音)起來時,就基本上熟了,就可以不用再往灶膛里放柴火了。也或許“婆水拐”還有另一層含義,在我們當地已婚的婦女稱為“嬪娘婆”,婆水拐的“婆”是不是因為它像已婚的孕婦一樣肚子里“有貨(有餡)”,所以可稱為“婆”呢?當婦女熬成拄拐杖的“婆”,就是瓜熟蒂落的時候了。當白白嫩嫩的婆水拐在水深火熱中,表皮變得有點“人老珠黃”時,就可以任憑人用筷子夾著吃或攔腰夾斷來吃,無論你怎么折騰,它們都無所謂了,似乎有著“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壯。究其歷史卻難以查其蹤跡,只知道婆水拐和其他用糯米、粳米等為主料制成的食品統稱為“籺”。縱觀歷史,做籺都是自古以來的傳統,逢年過節做籺敬神,以祈求生活美好,而且不同的節日會做不同的籺,逢年過節、婚假等多種場合都會做籺。
婆水拐煮熟起鍋后,第一鍋的第一碗一定是盛給觀音娘娘的,阿婆(注:奶奶)用笊簍撈出婆水拐,然后裝在一個“大碗公”(注:可盛湯或盛菜的大瓷碗)里,踮著小腳用竹籃子提著婆水拐,裝著香火,先去祭拜觀音娘娘。以前村上敬神的地方分為“阿公廳”和“阿婆廳”,觀音娘娘就在“阿婆廳”,現在村里已把兩廳合二為一了。小時候曾為這種情形產生過疑問,跟著大人去供神時,就會問大人為什么阿公和阿婆要分開住,大人只是對我笑而不答。疑惑雖未被解,但也沒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念頭,孩童的心早被在神仙享用完籺后用來歡送神仙放的鞭炮聲吸引住了,哪還有心思去管他們是否住在一起呢?長大后方知不論阿公廳、阿婆廳是獨立的,還是合在一起的,神仙都有各自的神位,都有自己管轄的范圍。
等阿婆回來,阿媽把盛好婆水拐的碗,從灶臺上端到飯桌上,一聲“食籺嘍”,我們方可以像餓死鬼投胎似的大快朵頤。一聲“食籺嘍”,喊出了多少垂涎欲滴的味蕾。之后阿媽還會指使我們兄妹給未做上婆水拐的左鄰右舍和村里的五保戶送上熱氣騰騰的婆水拐,名堂曰:送籺給他們食。“食”這個字在甲骨文中很像在一個屋檐下升起的一堆火,吃到嘴里的是帶著煙火味道的美食,留在人們心里卻是一股濃濃的人情味。無形中,阿媽以勤勞善良、尊老愛幼、助人為樂給我們兄妹樹立了榜樣。阿媽就是這樣,在曾經那個貧下中農的家庭里,努力把手上有的食材想方設法地讓它們變得更好吃,目的是讓所愛的人吃得更幸福。
地里的蒜收了一茬又一茬,地里的泥土翻了一遍又一遍,轉眼間我們兄妹一個個長大,連我這個“滿女”也大學畢業,開始了工作。家里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好了,想食籺隨時可以做,不用再考慮做頓籺吃要費多少金錢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在相隔家里七十五公里的地方工作,因為怕暈車,所以不敢經常回家。可阿媽卻常常惦記著我,還把我當成那個饞嘴的還沒有長大的丫頭,時常托人把婆水拐捎來。獨在異鄉,能吃到媽媽的味道,幸福的感覺不言而喻,品味飽腹的同時,也會籠罩上濃濃的鄉愁,即使在外闖蕩多年,味覺上的思念,始終忠心耿耿地跟隨著,就像思念家里的親人,日漸濃郁。阿媽給予的樸實的情感,賦予了我無窮的力量。阿媽說,無論遇到什么事,只有吃飽了,才有力氣去做好所遇到的事情。因此在那段歲月里,即使歷經了許多如梗在喉的心結,往往在滿足了味蕾之后,我就可以和自己握手言歡,重整行裝再出發。
那年阿婆吃完阿媽喂的婆水拐后,心滿意足地合上了眼。那木碓也隨著阿婆的去世完成了它的使命。隨之而來的是機器碾粉的時代代替了純手工的木碓操作,做籺變得容易多了。各種各樣的美食琳瑯滿目,應接不暇,但記憶深處的婆水拐仍是我百吃不厭、念念不忘的美食。
最近幾年阿媽老了,年邁的阿媽再也不能大費周章地做婆水拐給我們吃了。每當我們嘴饞時,只能到街上買來吃,或者帶阿媽上飯館吃。可無論換過多少家飯館,再也吃不出以前的那種味道了。或許是那樣的婆水拐里融入了金錢的味道,細微之處就差了那么一點叫做情感的東西,有情感的食物,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啊!
幸好阿媽做婆水拐的手藝被姐傳承了下來。我們當地有個風俗,那就是嫁出去的女兒每每回娘家時都會“擔籺去村”,方才顯得孝順,也方才覺得有面子。這個面子不僅包含了夫家婆婆做籺的手藝是否精湛,對親家是否尊重,而且還包含了出嫁女兒在婆家是否得以善待和教導,都會從是否有“擔籺去村”體現出來。當然時代變了,許多年輕人已不落俗套,凡事都想往輕松快捷去了。以前走親訪友,都要用籮筐裝滿籺馱在自行車或摩托車后面,現在一般用水果代替。比如圖吉祥,以前用“發籺”,現在如果來不及做或不方便買時,可以用橘子代替,寓為大吉大利,也可用火龍果代替,寓為紅紅火火。當然有些是永遠替代不了的,那就是祝壽時用的“壽桃籺”。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東西會推陳出新,但有些東西仍會永久保留它歷史的痕跡,歷久彌新。
姐在家里講的是客家話,嫁給講地佬話的夫君,所以做籺的手藝就不盡相同。姐把阿媽和她家婆兩人做籺的手藝結合起來,兩者相得益彰。做出的籺,尤其是婆水拐,除了外形還保留著阿媽當年的風采,味道上卻感覺略勝一籌。或許是現在生活更好了,不用再考慮做了一頓婆水拐后家里的油壇是否會見底,甚至可以任憑喜好加上各種海鮮以及各類調味品。或許姐知道她是兄弟姐妹中唯一把阿媽做籺手藝完美傳承下來的人,所以每逢他們那過農歷十月初十和過冬至節時,她就會做很多婆水拐和落水包,不管路途遙遠,委托人或委托車,送到在不同地方工作的我們兄弟姐妹手中。雖然所備食材一樣,但夫家喜歡吃的是圓形的落水包,而娘家則習慣吃是新月形的婆水拐,前者寓指團團圓圓、圓圓滿滿;后者寓指希望,如孩童一般的初生之物,擁有美好的未來。兩者均含有吉祥之意。當吃進滿嘴的幸福,滿肚子的吉祥時,我都會感慨:“有姐真好,有姐真幸福!”
一直不知道姐那一身爐火純青的婆水拐的手藝是怎么學來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必須要滿懷愛意和擁有耐心。我一直在遙想若我會做落水拐就好了,用不著青出于藍勝于藍,能成形能下咽就好。只是遙想卻從未付諸行動,因為一想到那煩瑣的工序,我就缺乏耐心和勇氣。直到為人妻、為人母之后,體會到為所愛的人洗手做羹湯也是一種幸福。當孩子邊吃婆水拐邊夸張地稱贊我的手藝時,對孩子大言不慚的贊美言辭,我也會欣欣然地接受。當阿媽吃到外孫端上的婆水拐時,也大贊這個讓她操碎了心的滿女。曾經的我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對家務活更是一竅不通。阿媽最擔心的就是獨自在外的我怎么解決一日三餐的問題和做事缺乏耐心的毛病。當她吃到我親手做的婆水拐時,她多年懸著的心終于可以放下來了。婚內的生活,不僅把我的棱角磨平,而且造就了我煙火的氣息。煙火之愛,飲食男女,或許這就是生活的本色吧。
《舌尖上的中國》曾有過這樣一句話:中國人對食物的感情多半是思鄉,是懷舊,是留戀童年的味道。婆水拐就是我伴著鄉愁,伴著回憶的味道,它讓我們投入了感情,成為我無數次前行的力量,也成為我們情感的紐帶。做的人幸福,吃的人也幸福,幸福的味道緊緊包裹著藍天下的我們!
責任編輯? ?謝?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