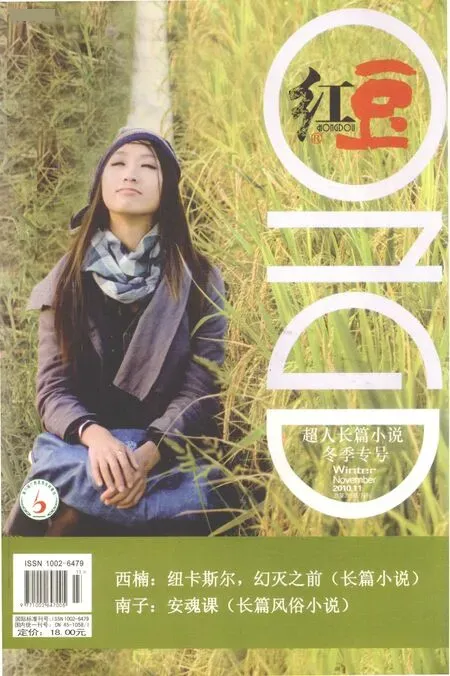鎖
農麗嬋,女,壯族,1973年生,廣西大新縣人,南寧地區教育學院漢語教師,廣西民族大學少數民族文學專業碩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會員,廣西地方志辦學術委員會成員,發表文學作品近二十萬字。
平日里,我是一個花癡,大凡看到路邊閃現出花的影子,就像打了雞血似的,第一時間會把它們拍下來制成美圖,或能挖的,就挖回家種,我的電腦和陽臺幾乎被花占滿了。
近日,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曬出了美圖,家鄉的梅子花開了,山洼里大片大片白色的花,香飄十里。這令我夜不能寐,但苦于書稿未竟,眼看向出版社交稿的日期臨近,只好隱忍在家,默默地工作。
一日上午寫了幾個小時的書,有些困了,居然在電腦桌前睡著了。在恍惚間,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我的母親,她用溫熱的手,觸碰著我冰冷的臉。我猛然醒來,是冰冷的書觸碰著我的臉。傷心了一小會兒,心想該回家看看了。
晌午十分,剛好接到了久居家鄉的外地朋友周給我打來電話,邀請我回家探梅,順便做些民俗調查。我樂極了,跳了起來,爽快地答應了。在寫書的日子里,一個人關在書房里日子久了,和家人、朋友彼此的感情也淡漠了。山洼里的那片花海,讓我決定打開書房這把生銹的鎖。
我匆匆地扒了幾口飯,給母親打了個電話。“媽,我想回家,聽說武姜的梅子花開了。”“什么?那幾朵爛花有啥好看的?”母親沉思了片刻,隨即說道,“好吧,你還是回來吧。我現在在外邊,和你表弟商量點事情。”得到了母親的許可,我急匆匆地往車站趕。車站人里擠滿了人,肩挑手提的,我看著他們候車時焦躁的臉,想起了我遠方的家。
車子在崎嶇的山路上盤旋了三個多鐘,終于回到了我的故鄉,偏遠的小鎮——桃城鎮。那是一座百年的老城,據說土司爺們曾在這城墻里邊的大宅子里住過,至今那光滑的石板和雕花的窗尚存。
冬天,桃城的天黑得特別早,沒到六點,天已經全暗了下來。走過東門城墻,隱約看見五十多歲的、白頭發的阿威在餅店里忙碌著弄米餅。餅店門口擠滿了人。我穿過擁擠街道,回到家中,門前我春天種的茶花已經開了,三朵,紅色的。父親在廚房煮好了我最愛吃的桃城切粉,外加兩個雞蛋和一塊扣肉。我端著滾燙的米粉,感覺到了陣陣暖意。
吃過晚飯,我上樓和母親一起看電視,陪母親聊了一會天。
“沒到年,你回來干嗎?”母親一邊看電視,一邊剝著龍眼干。去年家里的龍眼豐收了,賣不出去,母親只好拿來曬干,曬干了,好泡酒。
“我約了朋友過來看花,聽說武姜村的梅子花開了。”
“你又說寫書忙?”“我想休息兩天,順便過來看看你們。”我想起前幾天父親生日而我仍在值班監考的情形,有些愧疚。
“和誰去呢?有車嗎?”“和周。”
“周是誰?”“他不是廣西人,福建的,喜歡這邊的風景,所以住了下來了,是個公務員。”母親一聽,立刻警覺起來,說道:“嗯?我雖然老了,但腦子還管用。他們福建有錢人那么多,他跑我們這窮地方干嗎?不會是騙子吧?”我想起了和我交往多年的周,一頭白發,一臉的傻氣,笑了,“不會吧,他在我們這窮地方呆了十幾年了,能騙到啥呢?”
“他多大呢?”“比我大10歲,是我大哥的朋友。”周是一次我在家鄉做田野調查的時候認識的,他是一個研究家鄉土司文化的學者。
“他應該成家了吧?”“沒有,聽大哥說他離婚好幾年了。”母親一聽周的情況后,眉毛一皺,有些不快,對我說:“那你還是別去了。”我嘟噥地說道:“可我已經答應人家了呢。”
“你一個四十幾歲的已婚婦女,和一個離婚的男人廝混在一起,咱鎮上的人會說啥呢?這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吐口口水都會淹死人的,要注意影響,不要搞得滿城風雨,以后我老臉往哪里擱?你大哥介紹的也不行。你不為阿力著想,也要為高三的兒子著想。”我想起兒子這幾次聯考成績連續下滑,心里有些不快。電視里的節目是一個介紹老歌的節目,母親最喜歡看了,我卻絲毫聽不進去。
我回想起之前下田野時,確實和異性的朋友出去過,但從未和周出去。“我這是第一次和周出去,媽。”母親越說越起勁,大聲地說道:“講你都不聽,快過年了,家庭主婦應該在家打掃房子,準備過年,而不是去看什么梅花。被子洗洗曬了沒?粽子包好了沒?”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想起家里的亂樣子,年貨也沒有備好,心有些收緊了。
“我寫書得做這些調查才行呢。”“阿力上次回家的時候,他和我說了,你關起門來寫幾本書都可以轟動世界了,何必去那個什么欖圩?三天洗一次澡的地方,能弄出什么科學數據?當心阿力不要你!”母親的聲音有些顫抖。我想起了丈夫平日對我的好,在我下班的時候,總能吃到熱飯。于是,收斂了語氣,說:“嗯,我會注意的。”
“我還有個同事要過來呢。”“同事是男的吧?”“對。”
“他是我的領導。”“男領導也喜歡看花?”“嗯。我們順便去考察一下山歌。”
“不要和自己的上司扯不清關系,當心被人家抓住把柄,當不成系辦主任。”我無語,想想平時和老李出門開會、搞調查確實多了一些,但我從未想過其他。老李是個很敬業的老實人。
電視我是看不下去了,我走到父親的房間,摟住父親的肩膀,緊挨著他蒼白的頭發,試圖讓他幫我說話。父親平時最疼我了,很少批評我,但這次他也有些生氣了,他對我說:“你媽說得對,你一個女孩子以后少出門,加上你又是人民教師,一言一行以后都要注意點。”我默默地聽著,上了樓,心里想著那些有可能被我帶壞的可憐的孩子。
我跑到樓上,一個勁地和周訴苦。周一直安慰我。我突然覺得他就是一個騙子。
我在樓上蒙頭睡覺,突然聽到樓下母親在大聲地和我表姐通電話。
“阿春明天就要入新房了,他家門前有根電線桿,剛好擋住了大門口。今天他叫我去問仙,五山那仙婆說電線桿位置不好,擋住了祖宗的牌位,過年、過節祖宗出入不方便,會擋住財路,以后他家的啤酒攤就開不成了,得請仙來作法。”
近年來,我一直在研究壯族的原始宗教,一聽要請仙做儀式,心想我的核心期刊論文有望了,立馬回歸和顏悅色的常態,從三樓直奔二樓,問母親:“媽,啥時候請仙?”母親余怒未消,說道:“初步定大年初二。”
“作法就作法唄,打電話給我表姐干嗎呢?表姐買菜忙著呢。”“問她要錢啊,她做那么大的生意,她家入新房,還不得出錢?”
“要出多少錢?”“一萬多吧。”
“啊,那么貴。”“當然啦,仙一出門,就要雞鴨魚肉,還有大米伺候,還要給她做儀式的錢。完了以后,還要請村里的親戚吃飯。我們家的親戚那么多,起碼要上萬元。”
“那親戚來了,不得給人情嗎?可以補償一些費用呢。”“這次仙說不能要親戚的錢,要不就不靈了。你啥都不懂,還搞研究呢,以后啥事都要聽我的。”我怔住了,默默地回去睡覺了。
在樓上,我早早地關了燈,但徹夜難眠。想起了周,想起了明天喧囂的宴席。我決定一早和周告別,不看梅子花了。
第二天早上,匆匆地吃了父親給我煮好的雞肉粉,出門去搭車了。臨走的時候,父親一如既往地遞給我五塊零錢,把我塞進了三輪車。他對我嘆息道:“你頭發都和我一樣白了,咋啥事都不懂呢?”我不吭聲。
小鎮我是一刻都呆不下去了,我買了最早回南寧的班車票。窗外,我日夜思念的故鄉就這樣漸漸地遠去了,古老的城墻已沒有門了,墻上是些枯萎的茅草。不遠處的田地里是大片大片被割過的整齊的稻稈。在雨中,田里走過一頭瑟瑟發抖的小黃牛,它的母親就跟在它的身后,一只長尾巴的紅色毛雞飛過田野。看著那些雨中可憐的牛,我想起了我的母親。
回到了城里,我又繼續寫我的書。書房的門一直開著。寫書的時候,我偶爾會想故鄉,想起周以前寫過的一句詩:“冬天下著小雨,沒有風,南方的天空正鎖著一片灰暗的云。”
責任編輯? ?藍雅萍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