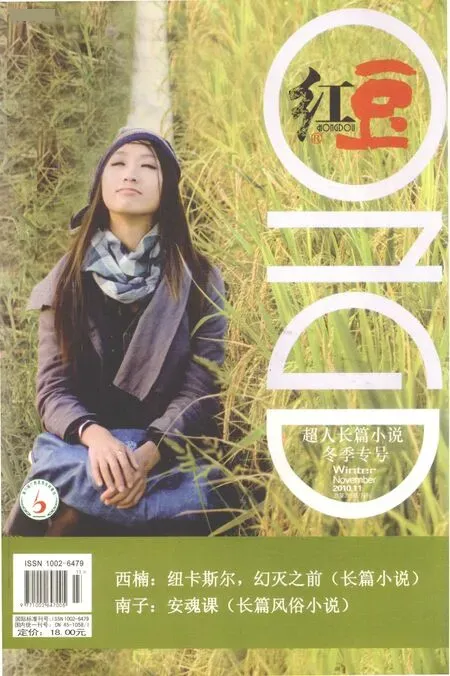老街
解方
小時(shí)候,我與外公一同生活。外公是位和藹的老人,待人和善,他最喜歡的就是去老街聽(tīng)?wèi)颉?/p>
我也喜歡老街,去老街是我最大的樂(lè)趣。街口的大叔,最喜歡拿著糖葫蘆在老街穿梭。他遞給我糖葫蘆時(shí),我有著一躍而起的喜悅。一顆顆糖葫蘆被我依次咽進(jìn)肚子,糖的甜味膩透了我的味蕾。洋溢著甜的嘴,常常因滿足而笑得不合攏。吃完糖葫蘆的我,會(huì)回頭看看人潮涌動(dòng)的老街,尋覓著賣(mài)糖葫蘆的大叔。
街中是張家影樓。張老板人特別精神、帥氣,一身黑色的西裝穿得特別筆挺。聽(tīng)外公說(shuō),張老板家是縣城里數(shù)一數(shù)二的狀元戶。張老板和他的兒子都去過(guò)很遠(yuǎn)的地方念過(guò)書(shū),是小縣城十里八鄉(xiāng)公認(rèn)的“大明白”。那時(shí)候,我喜歡纏著張老板借他的那頂綠色的軍帽拍一張帥氣的照片。而張老板每一次都經(jīng)不住我的糾纏,總會(huì)給我拍一張照片。張家影樓對(duì)面的米店,是外公常去的地方。米店的老板是外公的發(fā)小,從小玩到大的兄弟。除了買(mǎi)米,外公也順便與自己的發(fā)小在店里喝喝茶,聽(tīng)聽(tīng)?wèi)颍牧奶臁?/p>
街尾有賣(mài)熱湯面的老爺爺,老爺爺?shù)臒釡媸俏彝胬酆笞钕氤缘降拿牢丁@蠣敔斢幸恢回垼m懶洋洋的卻很是可愛(ài)。老爺爺在樹(shù)下賣(mài)著熱湯面,橘色的貓爬在樹(shù)枝上曬著太陽(yáng)。風(fēng)吹過(guò)帶動(dòng)樹(shù)葉的聲音,唰唰唰,很舒服。每次老爺爺端上來(lái)的熱湯面,我都很心急地往嘴里送,總被燙到,這時(shí)他就會(huì)拿一碗水給我,揉揉我的頭對(duì)我說(shuō):“小子,被燙到了吧。哈哈哈。”老爺爺那爽朗的笑聲,在夕陽(yáng)的照射下被拉得越來(lái)越長(zhǎng),好似過(guò)堂風(fēng),穿過(guò)整條老街。
后來(lái)我長(zhǎng)大了,離開(kāi)了縣城。一天在收拾舊物的時(shí)候,我看到了一張發(fā)黃的照片,照片里是戴著綠色軍帽的我。我對(duì)著照片里的自己漸漸出神,剎那間,內(nèi)心翻涌出萬(wàn)千思緒;不知道是在思索什么,仿佛想說(shuō)些什么、做些什么,卻又只能怔在原地。我收拾了行囊,決定回一趟小縣城。
……
路程很短,下了車(chē),握著那張被我反復(fù)摩擦而褪色的車(chē)票,站在站臺(tái),我看著一片片鋼筋水泥的樓宇,內(nèi)心五味雜陳。
我騎著借來(lái)的自行車(chē)回到老街,老街已經(jīng)不再是當(dāng)年模樣。當(dāng)年街口的二胡曲調(diào)仿佛成了我一個(gè)人陌生而熟悉的哀傷。張家影樓也已經(jīng)換了主人,一張張陌生的照片沖淡了記憶里戴著軍帽的我。外公聽(tīng)?wèi)虻拿椎暝缫殃P(guān)門(mén),而街尾的熱湯面也已經(jīng)消失不見(jiàn)。只有那棵街尾的樹(shù)默默地生長(zhǎng)著,仿佛記憶著老街漫長(zhǎng)而短暫的歲月。糖葫蘆的叫賣(mài),早已消失不見(jiàn)。在老街走著,我總是時(shí)不時(shí)地回頭,想要尋找早已不見(jiàn)的人與事。
我透過(guò)手指看著天空,天空依舊清澈明朗。老街卻沒(méi)有了我懷念的爬滿青苔的青磚綠瓦,沒(méi)有了倒貼著福字的木門(mén),沒(méi)有了擁擠窄長(zhǎng)的小巷,更沒(méi)有了大樹(shù)下升起的熱湯面的炊煙。
再見(jiàn)了,老街。
責(zé)任編輯? ?練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