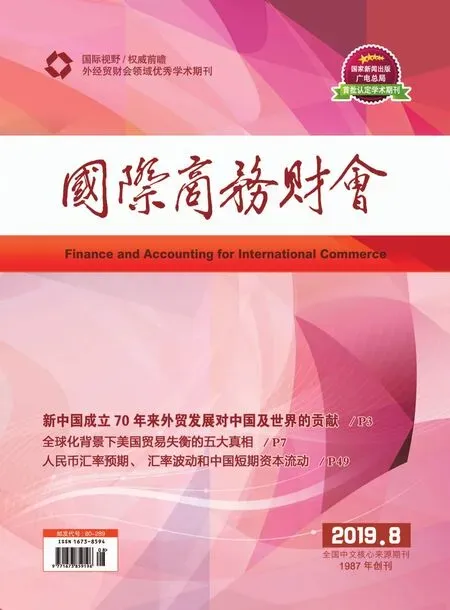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美國貿易失衡的五大真相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
為解決所謂“貿易不平衡”問題,特朗普執政以來先后挑起與中國、墨西哥、加拿大、歐盟、印度、韓國等主要經濟體的貿易沖突,已有近40個國家和地區受到美國的貿易威脅或關稅制裁。然而,關稅大棒適得其反,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下降反而繼續攀升,不斷加碼的貿易沖突正在深度和廣度上劇烈升級,并出現了超出貿易爭端范疇的趨勢,給世界前景帶來了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沖擊。深入分析美國貿易失衡的根源及其背后的真相是我們研判當前中美結構性問題的關鍵。
一、美國全球化史就是一部貿易失衡的歷史
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商品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為1.67萬億美元和2.56萬億美元;以國際收支為基礎的商品貿易逆差為8 913億美元,擴大了838億美元,增幅10.4%。其中,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總額4 192億美元,較2017年擴大436億美元。美國對歐盟貨物貿易逆差總額1 693億美元,較2017年擴大179億美元。“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并未阻止美國貿易赤字持續擴大。
事實上,比中美貿易失衡歷史更古老的話題恐怕是美國長期貿易失衡,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的全球化史幾乎就是一部貿易失衡的歷史。二戰后,美國在經濟實力上一直處于絕對優勢。戰后初期的美國極力推崇貿易自由化戰略,由于美國產品具有較強競爭力。1946—1970年24年里,美國對外貿易一直表現為貿易盈余,然而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黃金脫鉤,1971年美國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為1.52億美元。此后逐年遞增,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逆差國。1987年超過千億美元大關達到1 736億美元。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點,幾乎占美國GDP的6%以及世界GDP的1.5%。目前,美國對全球超過100個經濟體呈現貿易逆差。從分布看,美國僅與中南美洲、中國香港、荷蘭、澳大利亞、比利時少數經濟體保持順差。而與中國、歐盟、墨西哥、德國、日本等全球主要貿易伙伴都處于逆差狀態,是全球最主要的逆差貢獻國。
二、美國“三大赤字”的恒等式論
美國長期持續大幅逆差似乎成為“經濟之謎”,對此經濟學界有不同的假說。比如儲蓄失衡說、國際貨幣體系說、國際分工說等。美國龐大的貿易失衡和經常項目貿易逆差正是當前國際貨幣秩序和國際分工格局的重要體現。美國利用貨幣主導權,濫用金融信用,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其國內生產力的增長速度,美國極低的國民儲蓄率導致的儲蓄赤字也使得美國總需求長期超過總供給,成為全球經濟的風險之源,并直接導致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
開放經濟中的國民收入恒等式是我們理解美國貿易赤字、儲蓄赤字、財政赤字及其相互關系的基本框架。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X-M)=(S-I)+(T-G)(其中,X為出口,M為進口,S為私人儲蓄,I為私人投資,T為稅收收入,G為政府支出),將等式變形即可得到:財政赤字+儲蓄赤字=貿易赤字,可見,美國經常項目下的貿易逆差赤字實際上是由政府和居民支出超過其收入的部分,這部分的過度支出需要外部融資彌補其債務虧空,并使貿易失衡和經常項目赤字的長期化、巨額化。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美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1974年的31.9%飆升至2018年的107.2%,美國國債規模也超過22萬億美元,再次刷新了美國國債規模的歷史紀錄。
從美國國內經濟結構看,美國貿易逆差是儲蓄——投資不平衡的結果。美國國內的國民儲蓄率長期低于美國國內的國民投資率。國內儲蓄不能滿足國內投資需求,只能依靠“進口”儲蓄來支撐國內投資需求,這就是典型的“美國模式”——高消費、低儲蓄。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顯示,美國總儲蓄率在1965年到達最高點的24.9%后,20世紀80年代,儲蓄和投資出現了下降,但儲蓄率下降得更快,導致資本流入和貿易逆差增加。這一時期美國儲蓄率下降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聯邦預算赤字引起的公共儲蓄率下降;二是私人儲蓄率下降。此后,美國儲蓄率一路下滑,直至降至金融危機期間2009年最低點的13.7%。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后在一定程度上讓美國風險意識和家庭預防性儲蓄增強,達到了2018年的17.3%,然而在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美國儲蓄率仍是最低。
對于“一國外部失衡歸根結底是國內失衡的結果”這一論斷美國經濟學界內部也有認同。2005年美國國會研究部經濟學家在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曾指出:“逆差擴大的原因主要由國內外宏觀經濟條件決定的,而并非受到貿易壁壘或者外國商品傾銷的影響。美國支出超出了其產出,需求大于供給,其結果就是外國產品的凈流入,導致貿易逆差。而同時,其他國家的產出超過其國內的支出,必然產生貿易順差”。
三、美元霸權是債務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制度基礎
二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經歷最深刻的變化就是美元霸權的形成,而這也使貿易逆差成為美元輸出的主要途徑。由于美元的特殊霸權地位,加上美國市場巨大的容納能力,使得通過貿易逆差“出口”的美元又幾乎通過資本與金融賬戶“進口”,才會使得債務型經濟增長模式得以長期存在,而且美元霸權的運行機制具有內在強化特征。
美元作為關鍵貨幣和美國作為流動性主要提供國,是支撐美國歷史上打貿易戰,甚至冷戰,維護霸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中心地位為美國提供了全球性鑄幣稅收入,美國政府不僅能夠憑借政府職能在國內獲得鑄幣稅收入,而且能夠基于美元在國際貿易和國際借貸中的地位通過國際貿易取得鑄幣稅。自20世紀70年代,由于美國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迅速增長,美國的儲蓄與投資差距顯著擴大,與此同時,同等數量的美元與美國國債在美國之外被增持。因此,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經濟格局決定了美元和美債的強勁需求,美國貿易逆差有增長的系統傾向。
然而,與此相伴也形成了所謂的“特里芬悖論”。“特里芬悖論”是指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國家面臨的兩難困境:要保持儲備貨幣國家的地位,要求經濟必須堅固穩定,但同時國家必須保持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用資本輸入來平衡國際收支,否則主權貨幣就不可能成為主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和金融避險貨幣。但是,這種地位反過來又會侵蝕經濟的堅固性和穩定性,這就形成了“特里芬悖論”。
四、金融分工理論下的國際“雙循環”
恒等式論、美元特權論只能說明為什么美國存在貿易失衡,且長期存在貿易失衡,但并不能解釋貿易失衡為何越來越嚴重這一現象。事實上,隨著全球化分工格局的不斷深化和各國主導產業形態的變化,20世紀80/90年代后世界經濟呈現出一種新格局,即出現了以金融分工和貿易(產業)分工為紐帶的“雙循環”:一面是在實體經濟有強大優勢的德國、日本以及中國等商品輸出大國,擁有龐大的貿易順差和經常項目盈余,另一面是具有強大金融優勢的美歐經濟體,其主要輸出貨幣、金融產品以及各類金融服務,因此擁有大量的貿易逆差和經常項目赤字。
基于新的金融分工理論,再來理清其貿易失衡背后的邏輯就更加清晰。一個國家必須提供對外貸款,為其出口融資,而世界其他國家也愿意借款,為其進口盈余融資。由于凈進口或出口余額需要抵消凈對外借款或貸款,經常賬戶余額必須剛好被資本賬戶余額抵消。簡單來說,經常賬戶= 商品+ 服務+ 要素服務+ 資金轉移,其中要素服務包括應付外國投資者的利息、利潤或外國投資賺取的利息收入。
20世紀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通過對外借款來支持其經常賬戶赤字,這些資金流動顯得越來越重要。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資產在全球資產總額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隨著美國去工業化的日益深入和經常項目賬戶逆差的日益擴大,美國的經濟增長動力日益從生產和貿易轉移到金融經濟的增長上,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對外經濟模式開始轉變為貿易資本的輸出和金融資本的輸入,美國通過提供金融資產接收了大量的跨國資本流入。在此基礎上,國際分工格局形成了新局面:美國通過向世界提供美元和金融產品,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和技術優勢獲得周轉和交易中的溢價。例如,中國外匯儲備作為美國財政部證券存放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可產生利息收入,這些利息作為借方記入美國經常賬戶,并作為貸方記入中國余額,金融賬戶下的失衡甚至超過簡單的雙邊貿易往來所造成的失衡。
美國金融角色的轉變對于全球經濟格局產生了較大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風險資本的盈利模式及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結構的變化;二是一國資本的輸出脫離了商品的輸出;三是全球資源的配置更加依賴于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流動;四是中心國家的金融風險更容易向外圍國家轉移,轉移渠道增加。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以及短期內不可能出現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創新的背景下,國際分工格局不可能從根本上發生改變,全球利益的分配將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然而,伴隨著美國從“世界銀行”轉向“風險資本”的中心,全球利益分配方式已經不僅體現在貿易經常項目上,金融利益所得也成為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渠道。
從全球金融分工主導的資本循環來看,美國占據了全球金融分工體系最高端,美國金融資本不斷向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流動,而由發展中國家貿易盈余所形成的儲備資產又通過資本流動輸往美國。這種國際金融分工格局帶來的最大影響是資本在全球配置中流動失衡,中國等國在全球金融分工體系中處于不利地位,而美元資本則憑借其作為國際貨幣在國際貿易定價結算、金融資產定值、交易和投資,以及作為儲備貨幣等方面的優勢地位,達到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主導性調整。然而,其負面結果就是不斷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規制導致的資產證券化,致使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美國實體經濟、制造業日益空心化以及貿易全球失衡的進一步加劇。
五、全球價值鏈揭示貿易失衡中的結構性問題
美國貿易失衡不僅具有長期化、巨額化、系統化,還有明顯的結構化特征。在美國逆差來源國中,亞洲,特別是東亞是其最主要的逆差來源。數據顯示,1985年至今,亞洲地區對美國貨物貿易逆差貢獻均值為73%。其中,亞洲地區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主要來自于六個國家和地區,即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印度、中國和中國臺灣。這六個國家和地區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的貢獻占整個亞洲地區的90%。而隨著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重要的中間品貿易大國以及貿易節點,中國也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
美國貿易失衡的結構性特征可以說與全球價值鏈形成和深入發展不可分割。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制造業出現了三次跨國大轉移,制造業跨國投資、技術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動了生產全球化,特別是隨著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和內部生產網絡的形成,成為經濟全球化在生產、制造、流通領域的突出表現,全球價值鏈基礎也由此形成。各國資源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產品的生產鏈也被最大限度地細分,出口品價值由不同生產模塊上的不同國家組成,價值鏈貿易對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的貢獻度顯著增加,平均占到全球貨物貿易的60%左右。
全球價值鏈貿易形態下,大量的原材料類中間投入品、零部件類中間產品,在整個價值鏈中流動,從而產生了大量的中間產品貿易。以加工貿易為代表的中間品貿易不僅催生了亞洲區域的“三角貿易”,也使得中國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發展成為規模與深度兼具的“全球制造基地”。然而就價值鏈分工的水平和所處的位置而言,美國在全球價值鏈的高端,進口第三國的中間產品較少;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包含相當比例的中間投入品,中國從第三國進口中間產品形成貿易逆差,再向美國出口最終產品形成順差,因此背負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順差,并轉化為中國對美的順差。
美國東亞銀行所編制的數據就曾經反映了全球價值鏈對貿易失衡的影響。這些數據將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貿易失衡數據以及根據貿易往來企業來源國所調整的數據予以區分,即在全球范圍而非美國國內衡量美國公司的貿易失衡。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貿易失衡水平顯著降低。例如,一家美國公司在中國擁有合資企業,對于企業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應將其中49%計為美國公司的份額,同時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即使該企業位于中國,這些出口額仍然屬于美國公司的出口收入。
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占全球貿易的70%以上,近年來,全球100家最大跨國公司的海外銷售收入和雇員人數的增速都明顯高于母公司的業績增長。加入WTO以來,美國跨國公司主導中國加工貿易也成為價值轉移和貿易利益的主要獲利者。中國商務部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57%來自外資企業,59%來自加工貿易。以貿易總值和關境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統計法,高估了中美貿易逆差情況。一項資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國公司關聯交易,美國對華逆差將下降30%;扣除在華外資企業出口的因素,美國對華逆差將減少63%;如果再扣除加工貿易部分,這個數字將減少更多。
由此可見,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度和依存度因全球價值鏈深入合作得以極大提高,一國產業結構只有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才能獲得要素配置效率、資源整合效率提高所帶來的全球化紅利。美國貿易失衡系統性問題不會因特朗普極限施壓的關稅政策和對全球主要貿易伙伴發動貿易戰而發生根本改變,但卻可能讓全球進入了一個未來更加動蕩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