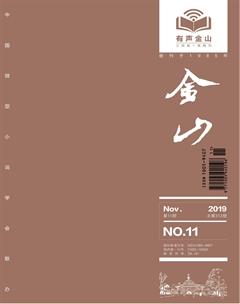鶯鶯傳
顏益揚
唐朝元稹,不知大家有無印象?元稹,《鶯? 鶯傳》的作者,但是他的一句詩可能比《鶯鶯傳》更為人所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這是他在妻子死后所作之詩,還稱“取次花叢懶回顧”,表達自己對妻子的一片真心。但在那個三妻四妾是平常事的唐代,元稹,真的對妻子一心一意么?那他的著作《鶯鶯傳》又為何要塑造一個始亂終棄的張生,一個悲劇的愛情故事呢?我覺得,這取決于那個年代的兩性觀念與愛情觀。
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女子都一直處于一個卑微的社會層面中,有學者稱:“在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女性被輕易地玩弄。”在《鶯鶯傳》中,張生一開始對崔鶯鶯的一見傾心,到后來的變心,始亂終棄,都說明了張生愛的只是崔鶯鶯的一副皮囊。在元稹那個年代,女性對于男子來說可能就如同家中擺放的物品,我不追求你的內在,只關注你的外表,你美麗,我對你傾心,不惜一切手段地得到你,但是當有一個比你更美麗、更完美的選擇出現在我的面前,曾經的山盟海誓也就像一句玩笑一般可笑。就拿元稹自己來說,妻子死后他曾痛哭寫道:“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從詩中仿佛看到了元稹對亡妻的緬懷和追憶,但事實上呢?妻子死后元稹依舊續了弦,對亡妻的一往情深很快被其他妻妾的甜言蜜語沖淡。有人說《鶯鶯傳》中的張生是元稹自己的投影,又何嘗沒有根據呢?
《鶯鶯傳》中的崔鶯鶯,表現了唐代女子的受教育程度較其他朝代高,辭令、鼓琴、刀札無不精通,曲未終而聞者動容。她聰明明慧,不像后世女子一般癡情留戀于一個不再愛自己的人,在張生變心時她便已經看出了張生情感變化的端倪,分手前她“恭貌怡聲”道出的話語表現出她作為一位女性的尊嚴。在那封長信中,她也能用言辭把自己的哀怨、委屈、痛苦、不甘的內心世界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不論現實還是精神領域,不論智商情商還是文化領域,崔鶯鶯都展現出了與當代才子們相比肩的才智與能力,與后世奉行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相比,《鶯鶯傳》的那個年代,對于女性的教育程度頗為重視。在唐代這樣相對開放的社會環境下,作為家長的父母、兄長,對在室女教育方面也表現出較為開明的態度,準許并鼓勵她們在家庭中習文讀書,這使得唐代女子雖不能像同輩男子一樣上學讀書,但在家庭中卻獲得了與男子大致相同的受教育的權利。但這依舊只是相對而言,相比于男子,女性不允許隨便出門,不能參與社會交往,不能隨自己的意愿選擇成婚對象等,也都說明了女性社會地位的低下。
而且,崔鶯鶯的愛情觀又何嘗沒有扭曲呢?至少,她在表達愛情的方式上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在席中,她原與張生互相以詩歌表達了愛慕之情,但當張生按詩中所言前來幽會時,她又“端服嚴容”,義正詞嚴地數落了張生的“非禮之舉”,讓張生如同葡萄架下的狐貍一樣,對“葡萄”可望而不可得,而在張生已然陷入絕望時,她又變得大膽而主動,“囊時端莊,不復同矣”,主動前往幽會,而最后遭到拋棄,被張生稱為“尤物”“妖孽”時,又“愚不敢恨”,只能自怨自艾,表現了她在追求愛情時的軟弱。
再說說《鶯鶯傳》中的紅娘。紅娘是什么身份?簡單來說,是婢女,是仆人,在千金閨秀都被社會所約束的年代,婢女的身份也就更為低賤,她為崔鶯鶯與張生之間牽線搭橋,又何嘗不是希望自己家小姐能有一個理想郎君、有一個美好的歸宿呢?紅娘雖不像大家閨秀一般識得什么大道理,但她所展現出的是純粹的、美好的祝愿。她知道自己不能如愿擁有理想的愛情,但希望自家小姐能夠收獲夢想中的幸福。而“紅娘斥責老夫人”,則展現了紅娘的愛情觀——自由,不被社會、家族所約束,與自己喜愛的人在一起。在她眼中,張生能夠帶給小姐幸福,所以她才會選擇暗中幫助張生,才會“以下犯上,以卑觸尊”,斥責老夫人。
而張生呢?我認為,對于張生,我們要分成兩個人來看,一個是應試之前的張生,落魄書生,“夜晚讀書時有紅袖添香”可能是他心中與金榜題名一樣分量的夢想,這個時候,他遇到了崔鶯鶯,這個在他當時眼中堪稱絕色的女子,而且這個女子對自己似乎也有情愫,日思夜想的“紅袖添香時”就在眼前,所以他才敢不顧當時社會道德倫理,幽會崔鶯鶯,才敢以一介書生的身份做出無禮之舉,當時,張生是愛這個女人的,至少,這個女人讓他心動了。而另一個張生,是已經知道崔鶯鶯對他而言唾手可及之后的張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渣男的身份,他覺得,以自己的才華,前面一定有大片森林在等著自己,又豈能在崔鶯鶯這棵小樹旁徘徊不前?所以在紅娘一再催促他去向崔鶯鶯求婚時,張生一再推托,乃至于到后來變心之后,更是以殷周之例,翻出了中國古代有名的“紅顏禍水”論,斥責崔鶯鶯為“尤物”,將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點上,對他人指指點點,洋洋得意之態溢于言表,其嘴臉令人作嘔。
事實上,從唐朝的各類文學來看,男女戀愛較之后世比較寬泛,基本是兩情相悅,女子愛慕男子才華,男子追求女子美貌,但男子大多重視自己才華而不拘于禮數,“縱酒狎妓,肆無忌憚”在當時被默許,導致始亂終棄的行為在當時屢見不鮮。很多男性把這種行為視為理所當然,而女性對這種始亂終棄的行為幾乎都抱有“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的奴性態度,不敢反抗,只得默默接受,而崔鶯鶯也逃不過這種命運,由“自重自薦”到“自哀自絕”,得知張生對自己的拋棄后也未曾反抗,將苦水自己咽下。
所以說,造成《鶯鶯傳》這一悲慘結尾的,與其說是封建社會這個籠統的東西,還不如說是對男子驕縱妄為的默許與女性不敢怒、不敢言的奴性的雙重作用下所得出的必然結果。在男女不平等基礎下的愛情,能夠開花結果,善始善終的,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