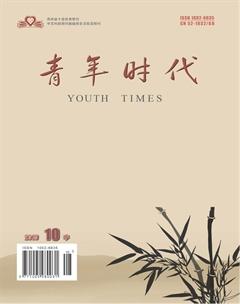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文化負載詞口譯
曹雅琴 李延林
摘 要:在外交場合,文化負載詞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這對譯員提出了不小的挑戰。準確恰當的翻譯,不僅能發揚傳播中國文化,而且還利于中西交流。本文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出發,以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歡迎宴會上致辭為例,分析口譯的翻譯生態環境,根據選擇與適應的策略及三維轉換的方法探討如何優化文化負載詞的口譯,以期更好地展示中國魅力,傳遞悠久的歷史文化。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翻譯生態環境;三維轉換;文化負載詞
一、引言
文字運載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生活勞動中產生的物質和精神產品。而語言則是人類交流思想、傳達情感的工具,是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口譯中,除了要重視文化及語言層面的轉換,還要注重交際功能。這是因為口譯具有即時性的特征,口譯活動的目標是傳遞信息進行交流。將富含民族文化信息的詞,即文化負載詞,短時間內口譯成英語時,不僅要求含義準確無誤,還且還要能被聽眾理解接受,達到交際意圖的目的,這樣的口譯才真正符合標準達到基本要求,且有利于文化的對外交流。近年來,中國已在154個國家地區開設548所孔子學院,舉辦“漢語橋”“CCTV漢語大賽”等漢語競賽,世界上越來越多人正學習漢語,并且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如今,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不僅要“引進來”國外優秀文化,加以借鑒,還要讓中華文化“走出去”,讓世界更加全方位地了解中國。因此,研究漢語文化負載詞的口譯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生態翻譯學核心理論
生態翻譯學理論作為一個年輕的翻譯理論體系,正處于發展期,該理論由胡庚申教授提出,起步于2001年,立論奠基于2003年,倡學整合于2006年,全面拓展于2009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一屆國際生態翻譯研討會上指出,翻譯是翻譯下屬的一個分支,至今尚未得到完全接受和批準。雖然生態翻譯在國際翻譯界引起了興趣和關注,但并未產生太大的影響力,目前國內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將目光放在該理論上著手進行研究。因此,生態翻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正不斷成熟完善,能為翻譯提供更充足的理論指導。
(一)翻譯生態環境
胡庚申教授將“翻譯生態環境”定義為“影響翻譯生存和發展的一切外界條件的總和”。翻譯生態環境可分為三個層次:宏觀、中觀及微觀,或稱之為大環境、中環境及小環境。宏觀上,各個國家有著不一樣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同的群體的翻譯政策也有所差異,如自然經濟環境、語言文化環境、社會政治環境。中觀上,即使是同一個國家,文學翻譯和應用方面也不盡相同。微觀上,翻譯研究自身的內部結構,如理論、歷史和批評等的差異。翻譯生態環境對所有翻譯主體來說是不可改變的,屬于一個統一體。
(二)適應/選擇理論
“適應/選擇”理論借用達爾文的“適應選擇”學說原理,轉意“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的概念。該理論認為翻譯過程中的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特征是:一為“適應”,即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二為“選擇”,譯者在適應的基礎上對譯文進行選擇。整個翻譯過程便是選擇和適應的循環交替。在“譯事中”,譯者處于“中心”地位。翻譯的選擇適應論則將翻譯過程視為是“天擇”和“人擇”的過程。所謂“天擇”,也就是翻譯的第一個階段,是以原文為典型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選擇,“人擇”為第二階段,指在接受了翻譯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對最終的行文進行選擇,因此翻譯過程就是從“天擇”到“人擇”轉換過程。不同譯者的“適應”中的選擇不同,因此就產生了不同的譯文。
(三)三維轉換
生態翻譯學的翻譯方法可以概括為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三維”轉換。首先,語言維轉換基于語言學,關注的是翻譯的文本語言表達,源語與譯語在句法、語法、詞法及修辭等方面都存在差異,在翻譯時就要考慮語言形式表達的轉換問題,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文化維注重的是語境效果,源語與譯語的文化生態存在著差異,對不同生態文化的認知差異導致同一事物在中西方文化中引起的聯想也不盡相同。例如,“龍”表示皇權神圣,而英語dragon則是貪婪邪惡的象征。為了避免曲解原文,譯者還要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文化系統,然后再進行譯文的選擇,而文化負載詞正是突出強調文化維轉換的必要性,要克服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實現兩種語言的文化生態和諧平衡。最后,交際維強調翻譯的人際意圖。除了語言和文化內涵的傳遞外,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層面,這點在口譯中更為突出。口譯對于遣詞造句的要求沒有筆譯那樣嚴苛,以口語體為主,過度拘泥于文字,文縐縐的語句反而阻礙交流,交際意圖是否實現才是交際維轉換成功與否的定斷條件。
三、文化負載詞的口譯
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主要存在兩大障礙。一是對等詞匯的缺失和詞義沖突。一些反映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匯往往在英語中找不到對等或相似的詞匯或表達。例如,一些日常的食物,餃子、饅頭及油條等,還有本命年、太極及氣功等特色詞語。此外,需要避免“望文生義”,某些詞匯雖然有對應的表達,但有時其表達的含義卻恰好相反,稍有疏忽,就會出現嚴重失誤。例如,由于地理位置的差異,英漢中“東風”和“西風”有著截然相反的內涵。漢語中“東風”指代春風,代表溫暖和春天,“西風”則指秋風,寓意寒冷。但是對于英國這樣一個位于西歐,屬于溫帶海洋性氣候,盛行西風,全年溫和濕潤的國家來說,“西風”則是溫暖代表。二是對等文化含義的缺失。某些詞匯即使在英語中有對應的表達,但其內涵也可能是有空缺的。例如,“武夫”一詞英文中對應的可用warrior或者soldier來表示,但是放在具體語境下的句子中,如“這人就是一介武夫”,這里的“武夫”就暗含了胸無點墨的貶義。而僅僅用warrior來對應就無法傳達該句話的語氣和暗指含義。由于這些特點,文化負載詞在某種程度上可譯性有限,但是譯者可以在生態環境下做出自己的選擇,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一)語言維的適應性轉換
語言維的適應性轉換指的是在不同方面和層次上對語言形式的轉換。漢語屬于漢藏語系,而英語屬于印歐語系,一個注重表意,一個注重結構,所謂的“形散而神不散”表明漢語以意驅形,而英語則是強調形式、邏輯結構及連接來突顯出句子、以及語篇的聯系,達到以形制意。譯者需要根據兩種語言的特點適當選擇合適的表達方式和語言結構,實現語言維的轉換。
例1.與君遠相知,不道云海深。
譯:Nothing can separate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vision.
“與君遠相知,不道云海深。”出自唐代詩人王昌齡的《寄歡州》,意即,縱使相隔萬里,只要彼此心意相通,便不覺路途遙遠。五言絕句是中國傳統詩歌體裁,英語中沒有對應的表達方式,要解決這種翻譯難題,譯員不僅得有文化貯備,明白源語所要傳達的意思,還要結合語境將將語言形式做出轉換,習近平主席引用這句古詩后闡述了對“一帶一路”的愿景,顯然,“相知”在這就是指共識。在適應了這樣一個翻譯環境后,譯員做出適應性選擇,把源語的文體舍去,用樸實的語言把該句的含義清楚地表達了出來,在語言維上做出了轉換。
例2.從開羅到圣地亞哥,曾經的促膝相談還余音在耳,當時的深入交流恍如昨天。
譯:From Cairo to Santiago, our heart-to-heart discussions still ring in our ears, as if they happened only yesterday.
“促膝長談”“余音在耳”這類漢語四字成語結構,英語中沒有,那么在進行翻譯時,這類詞就無法保留原有形式,譯文很巧妙地用heart-to-heart discussions以及類似的英語習語ring in our ears進行轉換。同時譯員還用as if 將漢語中“散句”轉換成結構和邏輯緊湊的句子。
(二)文化維的適應性轉換
在進行口譯時,譯員要有文化意識,注重文化的傳遞和闡釋,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的轉換,還要跨越文化的障礙。這大大增加了翻譯的難度,不僅要盡可能的保留文化內涵,還要考慮到聽眾已有的文化儲備、接受能力和對另一文化的接受程度。
例1.走四方固然辛苦,但收獲是“朋友圈”越來越大。
譯:Frequent overseas trips may be exhausting, but we are repaid with a broader network of friends.
“朋友圈”源于中國社交軟件微信,隨著微信用戶人數不斷擴大,這一近年來流行起來的新詞被廣泛用于日常交際中,而外國網友常用的facebook、instagram等軟件沒有對應的說法,因此譯員考慮到這一文化差異,沒有直譯成circle of friends,而是采用了英語中表示人際網絡的network,這樣既符合英語的表達又準確地將含義傳達。
例2.“一帶一路”“兩廊一圈”
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gether with the Two Corridors and One Belt
近年來,中國提出了很多理念、計劃和項目,如命運共同體、五位一體、三去一降一補及滬港通等,這些都屬于帶有中國特色的新詞。這類詞匯的翻譯有些已經固定且被國外接受,而有些沒有一種官方固定的翻譯。這就需要譯員在口譯時把“是什么”這層意思得給傳遞解釋出去,否則譯語聽眾將會不知所云。例如,“多證和一”譯為merge different forms of certification required of business into one certificate.譯文準確地傳達了“證”“一”的含義,簡潔明了又有沒有扭曲原意。
(三)交際維的適應性轉換
生態翻譯學認為要在語言和文化的轉換基礎上,側重于交際意圖,因此在口譯時要體現交際情感,關注譯語能否正確傳達交際意圖。如果信息沒有起到交際作用,那就毫無意義。
例1.此刻的人民大會堂,高朋滿座,勝友如云
譯:Tonigh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s graced by the presence of an august gathering of world leaders
漢語中有很多類似于“高朋”和“勝友”的敬辭或者謙辭,如犬子、令堂、惠贈、垂愛及高見等。這是含尊敬口氣的用語,中國人說話一向較委婉,做人講究圓滑,而歐美則是單刀直入,直切要點,因此這類詞匯在口譯時取其基本含義即可,而且“高朋”和“勝友”語義重復,需要簡化,不需重復翻譯。漢語為了講究氣勢、韻律往往出現語義重復的情況,即“雙動詞現象”,如調整與優化,提高與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此外,還有一些四字詞語意思疊加,如朝氣蓬勃和充滿活力、共聚一堂和共襄盛舉等。這類詞匯或現象可采取適當簡化的方法,把說話者的主要意圖進行傳遞,否則會使譯文晦澀難懂,進而會阻礙交流,拉低整體的口譯質量。
例2.在當今世界行走,恰似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作為各國領導人,我們沒有退卻的理由,只有前進的選項。
譯:Like sailing upstream, we will be pushed back if we dont move forward. Yet for world leaders, going backward is not an option.
該句譯文有三點值得肯定,首先漢語注重表意,經常會省略成分,例句中“在當今世界行走”和“逆水行舟”的主語“我們”在漢語中省略了,這并不影響意思,但是英語則不然,若是按照原文的結構和句子成分機械地對譯,英譯文缺主語,阻礙了聽眾理解發言者的意圖。其次,英語強調句子間的邏輯關系,而漢語則不然,文中“在當今世界…不進則退”這句與后面的“作為各國領導人…前進的選擇”之前暗含了轉折的意思,漢語中未直接點明這層關系,但是在英語中則需要加上“Yet”,指出句子間的邏輯關系,使整個語篇渾然一體,結構緊密。最后,條件狀語的使用。中文有很多的并列句,句子看似是并列的關系,例句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就存在條件關系,所以譯文用“if”將兩句連成一個完整句,由散化整,符合英語句子的特點,利于聽眾理解,達到了交際意圖。
四、結語
本文主要從生態翻譯學的“三維轉換”對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辭的口譯進行分析,強調在適應生態翻譯環境下,對譯文從語言、文化及交際三個角度進行選擇,具體采用簡化、添加連接詞將漢語中隱形的邏輯關系變為顯性及改變語言形式等策略。但文化負載詞的口譯并非某幾種方法就是完美解答,還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譯員可以在口譯時將這三個維度作為心中一把衡量的尺子,對譯文質量進行評估,從而能不斷自我糾正進步,提升口譯能力和譯文質量。生態翻譯學是個新興的理論體系,提供了一種科學合理地跨學科研究視角和理論支撐,正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發展,定會為翻譯研究和實踐開創一片新天地。
參考文獻:
[1]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2]胡庚申.生態翻譯學—建構與詮釋[M].北京:商務出版社,2013.
[3]胡庚申.翻譯選擇適應論[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賈延玲.生態翻譯學與文學翻譯研究[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7.
[5]楊承淑.口譯教學研究: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
[6]英文巴士.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歡迎宴會上祝酒辭全文[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