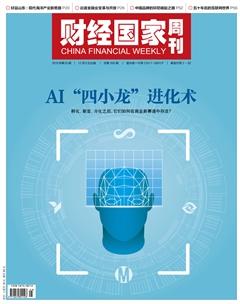對“信息繭房”,你到底該不該恐慌
安彤
今天讓我們來聊聊一個隨著技術發展被不斷提及的詞:信息繭房。
在網絡信息傳播中,因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往往只注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使自己愉悅的訊息領域,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
——這是WEB 1.0時代,美國學者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烏托邦》中提出的概念,也是信息繭房最為人熟知的來源和版本。
人類對技術原生式的懷疑,將這個詞一路帶至移動互聯網時代。如今打開手機上網,進入視線的似乎都是“你感興趣的”“你關注的”內容,從文字到視頻,形式不限,都很“了解”你。
于是人們開始質疑基于算法推薦的內容分發機制,是否更嚴重地桎梏了信息獲取?我們被“信息繭房”綁架了嗎?
事實上,簡單套用一個概念去看事物本質并不可取,尤其是對待技術,我們更應該理性辯證地去層層分析、拆解。不能被綁架的,是認知本身。
恐慌從何而來
“信息偏食”乃至“信息孤島”,現代人對信息恐慌的來源無非如此。
確實,如今關于信息大爆炸的論調是能夠被佐證的,巨量的、冗雜的信息在互聯網時代被創造、傳播、再創造,人們的擔憂不無道理。
據IDC(國際數據中心)研究,當今每48小時所產生的數據量,是過去人類文明開始到2003年累積數據的總和。
巨量 據IDC(國際數據中心)研究,當今每48 小時所產生的數據量,是過去人類文明開始到2003年累積數據的總和。
可怕嗎?面對如此大的信息量,一個人就算全天24小時保持接收狀態,也絕不可能接收完,更別提還需要給人腦留下處理消化信息的時間。
矛盾甚或恐慌由此而生,人們既覺得被信息繭房中的“蠶絲”裹挾得透不過氣,又礙于攝取的信息有限,擔心信息通道變窄,個體越來越狹隘。
相似的狀態早在上世紀就已被預言——尼爾?波茲曼曾在《娛樂至死》中對比兩個著名“寓言”,有的人害怕信息被剝奪,有的人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
多年后,當信息在移動互聯網和算法技術的加持下,變得個人化、定制化、更加高效便捷,恐慌也在加重。
但不論是預言還是實際的情緒,“信息繭房”式恐慌并未得到科學實證。下面這個小小的研究試驗或可作為一定參考:
2016年,哈佛大學的Seth Flaxman等研究人員選擇了5萬名參與者,要求他們報告自己最近閱讀、觀看或收聽的新聞媒體,同時通過電子手段直接監測和記錄他們的實際新聞消費行為,包括網頁瀏覽歷史等。研究最終發現,人們實際的媒體消費比他們自己想象的更具多樣性。
研究中一個細節顯示,人們實際并沒有陷入“信息繭房”中,但他們可能會裝作自己陷入了其中。這是一個“被迫害”的妄想。
我們可以想象,在面對一輩子都看不完的信息時,選擇是必然,情緒是附加,那么自己的選擇究竟基于什么?算法是在幫助你還是粗暴地禁錮你?這些問題顯然值得探究。
雙向選擇的可能性
看到這里的你,估計已經開始細數自己手機中的資訊類、視頻類、購物類、種草類APP和各種搜索引擎。

當信息在移動互聯網和算法技術的加持下,變得個人化、定制化、更加高效便捷,恐慌也在加重。
多數人可能還是希望,這些平臺能夠盡可能地提供更多雙向選擇。就像走進一間綜合性商場,商品的多樣性是基礎,商場的索引若能幫助縮小選擇范圍,甚至推薦真正適合顧客的商品,是否更加分?
但在這之前,對于算法的疑慮,還有幾句話得說說。
不能簡單化理解算法。
“算法不就是我看足球看久了,以后給我推薦的就都是世界杯歐冠意甲英超中超了嗎?”有人這樣理解算法。
乍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但這其實只是一種最基礎、最表層的算法。真相是,你經常看足球的比賽內容,系統會根據協同過濾模型,找到與你相似的人群,再以群體興趣愛好進行內容推薦;或是,通過深度學習,對你的各項身份特征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再去優化推薦結果……
用于實踐的算法維度,要比想象的復雜得多。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計算機系專門進行過實驗,讓兩組人同時在協同過濾算法推薦的平臺上獲取內容,一組人對推薦結果進行“跟隨”,一組人對推薦結果毫不理會。
實驗結果和一般的認知完全相反:綜合21個月的數據,跟隨組獲得的信息更加豐富多元,不理會算法推薦的一組,視野反而更加狹窄了。
所以為何說簡單套用一個概念去定義事物本質不可取,在懷疑技術的同時,對自己的認知也需要反思與更新。
近日今日頭條的CEO朱文佳在2019生機大會上說,頭條要做的是通用信息平臺,通過推薦、關注、搜索來分發圖文、視頻、音頻、問答等各種信息內容,這種內容和分發手段的多元組合不僅不會帶來信息繭房,還會帶來一個“更大的世界”。

過去七年,今日頭條在產品上的嘗試,其實有非常清晰的邏輯,那就是“一橫一豎”。“一橫”是盡可能豐富的內容體裁,“一豎”是盡可能多的分發方式。
這幾乎是挑戰人們認知的說法,但結合雙向選擇的可能性,此話未必不成立。
朱文佳提及的“通用”有兩層意思:一是普惠,人人都可以使用;二是豐富,能夠支持多種分發方式和內容體裁。“過去七年,今日頭條在產品上的嘗試,其實有非常清晰的邏輯,那就是‘一橫一豎。‘一橫是盡可能豐富的內容體裁,‘一豎是盡可能多的分發方式。”
按照這個思路去理解移動互聯網崛起與今日頭條的關系,一切都很清晰了。
2012年,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元年——中國手機網民數量首次超過電腦上網網民數量。這一年,頭條首先在移動端引入了個性化推薦這種分發方式,提高了移動時代的信息獲取效率,一定程度上解決了WEB時代小屏幕如何容納海量信息的行業難題。
此后,按照豐富內容體裁和分發方式的邏輯,2014年,頭條號推出,幫助圖文創作者降低創作和傳播門檻;2016年,大力投入短視頻,進一步豐富內容體裁;2017年,上線問答和微頭條,鼓勵更多人創作,同時也強化了關注這種分發方式;近期,正式推出“搜索”的功能——把尋找信息的“權柄”,還給了用戶。
仔細觀察這一歷程,會發現一個現代人所能接觸到的幾乎所有內容體裁和分發方式,都已在頭條平臺上得到了容納和體現。
有了這些基礎,信息才能“有資格”與用戶進行雙向選擇。比如你可能因為一部紀錄片所獲獎項,去了解一個導演的人生經歷,因為Ta的故事繼而關注某一行業,甚至發散到相關領域創作者的內容主頁。
從這個角度,頭條及一些“頭條們”反而在通過不斷升級的技術和內容,試圖打破信息繭房,削弱人們在獲取信息上的焦慮感和恐懼感。
“變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如果說,算法不該為信息繭房背鍋,那么我們真正該注意的究竟是什么?要與技術怎樣相處,才能化解恐慌和偏激等存在問題?
首先要做的,可能是保持獨立思考能力。在信源單一的情況下,不做人云亦云的判斷,不能僅憑算法的推薦去獲取新知。
其實,這里也涉及到分發方式多樣性的價值。越豐富的信息分發方式,用戶可能獲得的信息便越多樣,搜索、關注、推薦等等方式結合起來,“信息偏食”自然減弱。
平臺們有各建的數據庫、小百科,形成足夠豐富的信息分發模式矩陣,才能基本避免信息繭房。
除此之外,平臺做好內容質量,是更進一步的事。
朱文佳認為,傳統搜索引擎用戶一點就發出去了,但在頁面上滿不滿足就不知道了,但是如果把內容生態做好,有些結果是不用擔心的。
這也是今日頭條做信息通用平臺的原則,一切基于優質的內容信息。
由此,我們有理由分析判斷,信息繭房在當下的成因包括技術限制,也有人的本性情緒使然。但解決方式也很清晰——讓技術的歸技術,人性的歸人性,兩者和平共處,不要將之混為一談。
畢竟,即便是提出信息繭房概念的桑斯坦也在《信息烏托邦》中指出:“新的傳播技術正在使事情變得更好而不是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