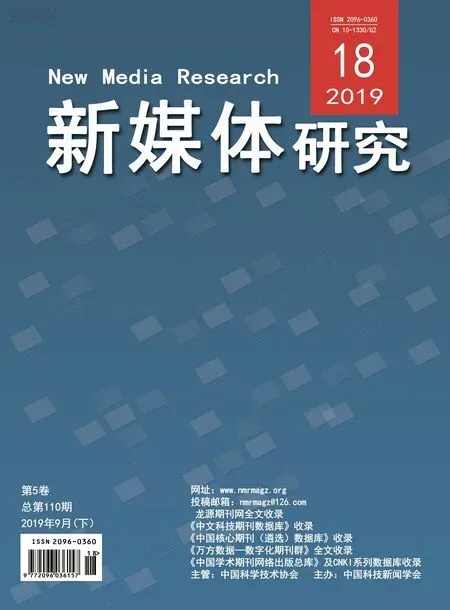認同與愿望建構:中國夢在網絡小說中的傳播現象探析
梁榮驍
摘? 要? 中國夢從2012年提出至今,幾乎擴散到了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文章通過質性的研究方法,對涉及中國夢的代表性網絡小說作品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近年來網絡小說呈現出一種“中國夢”游戲化敘事的傳播現象,與網絡小說的主要受眾——青年一代對游戲化敘事的認同密切相關,其內在邏輯是青年群體受“中國夢”得以實現的象征性現實影響,產生的一種愿望建構。
關鍵詞? 中國夢;網絡小說;網絡亞文化;擬態環境
中圖分類號? G2?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9)18-0004-03
1? 中國夢的敘事層面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時提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2013年6月7日,習近平在加州與奧巴馬會面時進一步指出,“中國夢就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它也是合作、發展、和合、共贏的夢。這與美國夢和各國人民的美好的夢想是相通的。”用“中國夢”來概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因為中國夢是一種形象的表述,是一種為群眾易于接受的表述[1]。
與此同時,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主流文化符號,由于不同個體的認知偏差,中國夢在不同的維度和場域中的敘事常常會生成不同的意義。馬文霞認為“中國夢”的話語存宏大敘事與個體敘事兩個維度,宏大敘事偏向西方精英階層,個體敘事偏向國內普羅大眾[2]。趙光懷等認為中國夢具有平民化敘事特征,其中既有社會個體對中國夢觀念的認同與意義分享,亦有將中國夢作為符號具象化為個體理想夢的問題[3]。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說,通過平民化敘事模式與個體夢建構在國內進行中國夢傳播,是得到學界認可的。在具體傳播實踐上,孟建等通過對新浪微博的涉及中國夢的原創博文研究發現,中國夢在官方媒體表述中多次強調“民族復興”與“個人夢”的關聯,同時高轉發博文多涉及房價、弱勢群體等平民化敘事層面[4]。
2? 作為平民化敘事的網絡小說
在中國夢作為社會主流文化傳播的同時,無數亞文化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應運而生,它們有著不同于主流文化的獨特風格,根據經典伯明翰學派的研究,亞文化帶有“儀式抵抗”的風格,并將亞文化視為階級批判的一部分[5]。但是,中國的亞文化更多的則體現出一種后亞文化研究提出的“身份認同”,并沒有明顯的核心政治理念,以青年群體為首的互聯網使用者,更多的將亞文化視為在父輩代際沖突下,尋找到的一片能實現身份認同的“避風港”。這片避風港隨著一代青年的成長,正日益成為主流文化下最大的一片精神田野,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的重要陣地,而網絡小說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國夢傳播的具體實踐上,平民化敘事模式是一種相較以國家民族等寬泛概念為核心的宏大敘事模式而言,更符合社會的真實情境的,以日常生活元素為主要素材的敘事方式。以單一普通中國人為主角,隨著敘事的發展完成個體提升乃至個體夢的實現為主線的網絡小說,更容易引起普羅大眾的共鳴。因此,青年群體完全可以在網絡小說的媒介使用中,找到亞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間的“最大公約數”[6]。與此同時,網絡小說作為有別于精英文學的亞文化圈中的一員,隨著互聯網興起與青年一代的成長而快速發展,讓我們不能忽視在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時,這個圍繞網絡小說而聚集起來的青年亞文化群體的重要地位。
3? 青年群體的游戲化認同
當下,網絡小說和傳統小說在敘事方式上仍有較大的差異。傳統小說一般是根據真實社會現實進行藝術加工后寫作,但網絡小說在當下卻呈現出一種游戲化邏輯結構的趨勢。黃發有將網絡文學的游戲化趨勢歸納為普遍強調娛樂與游戲功能,和網絡文學與網絡游戲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相互滲透兩個方面,認為游戲化是“消費寂寞”[7]。這是一種從媒介自身形態為視角的審視,但從互聯網時代的更大時代背景的媒介生態來審視游戲化的趨勢,游戲化其實體現的是青年一代人在動漫、游戲等網絡文化下形成的一種游戲化審美。如王義明等用“云養青年”來定義在互聯網技術和網絡文化覆蓋的社會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群體一樣[8]。
從整個社會環境變遷而言,以1994年內地出現第一本專業的游戲雜志《電子游戲軟件》為標志,“80后”“90后”等一批青年群體開始在成長的過程中,從各類電子游戲建構的虛擬空間汲取養分。這直接影響了幾代青年群體的思維與認知。因此,以“80后”為主體的網絡小說作者傾向于借由現實中不存在的二次元幻想元素,如“系統”“智腦”“外星科技”等虛幻存在,將現實生活發展的邏輯游戲化。印上互聯時代烙印的“80后”“90后”等青年群體,對這種游戲化的敘事邏輯具有天然的認同感。他們對游戲化的敘事具有老一輩讀者群體所感受不到的代入感或沉浸感。
這種敘事模式在中國夢文化出現后迅速與之結合,在已有的科幻、武俠、都市、游戲等網絡小說類型基礎上,衍生出以“學霸”“復興”等為關鍵詞的游戲化小說流派。在游戲化的敘事中,小說中擁有“系統”的主人公不僅可以從宏觀的視角覺知自身各個學科能力的量化數據,更可以對某個學科進行“升級”。同時,與一般小說的反派人物不同,中國夢與游戲化結合的小說中,主人公最大的困難往往是一個個的標明可獲“經驗值”的難題,整個小說敘事跟隨著主人公“發現難題—破解難題—收獲經驗—級別提升”的循環而進行。如較有代表性的網文作品:《學霸的黑科技系統》《我只想當一個安靜的學霸》《大醫凌然》《醫師》等。
在起點人氣榜單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為《學霸的黑科技系統》,其長時間占據科幻類作品各個子排行榜的前列。如原創風云榜第二,24小時熱銷榜第一,推薦票榜第二①。這種游戲化結合中國夢的敘事模式得以突破以往玄幻、穿越為主的敘事模式,并在網絡文學平臺上呈現出擴散的跡象,是青年群體對游戲化認同的一種外在表現。
4? “象征現實”與“愿望建構”
在李普曼《公眾輿論》中,擬態環境理論認為由大眾媒介對現實符號選擇加工后所建構的擬態環境,對人們的行為產生著巨大影響。李普曼認為,擬態環境是影響人們行為的三種現實之一的象征性現實,是客觀現實與主觀現實的中介[9]。作為文學作品的網絡小說,是由一個個平面符號所構成一次元世界,是一種獨立于客觀世界之外的幻想空間[10]。在中國夢的文化場域下,網絡小說中以游戲元素“系統”為支點所建構的,糅合了國家復興與日常生活的幻想空間,正在越來越向客觀現實靠近。
網絡小說的游戲化敘事過程是中國夢在個體層次的理想化建構,借由現實符號“菲爾茲獎”“諾貝爾獎”“學術論文”,建構了一種能得到青年一代認同的象征性現實。多數小說作品的最主要“爽點”相對一致,以小說主人公向全世界證明了中國的科研創新能力,收獲國內及世界贊譽為主。這樣的“爽點”背后隱藏著青年一代對當下成功符號的認可與渴望。正如晨星LL筆下的主角陸舟,作為普通中國大學生的他,論文發表到《科學》《自然》等頂級期刊,在普林斯頓讀博期間更是破解了數學千禧難題黎曼猜想,因此獲得了世界最頂級的數學榮譽“菲爾茲獎”,由于二次元幻想元素的“系統”的幫助,陸舟的學習過程猶如游戲般“升級打怪”過程,所以他能輕松的實現跨學科的研究,并因其在化學上無與倫比的科研成就收獲諾貝爾獎。這種模糊了真實與虛擬的敘事,與青年群體心意相符,令其沉浸其中。
根據諾曼·N.霍蘭德關于“檢查者”的論述,娛樂性的文藝作品相較“杰作”使讀者更多的融入作品并進行個性色彩的幻想[11]。因此,以小說為媒介的游戲化中國夢敘事更易引起人們內心原始的幻想,幻想現實生活中渴望而無法實現的欲望之事與物。在中國夢的文化場域下,經由網絡小說建構的象征性現實,一種真實的愿望在自我價值乃至整個國家復興得逞后,會潛移默化的改變讀者的主觀現實建構。換言之,網絡小說媒介下的中國夢游戲化傳播,有達到行為層次效果的可能。
作品的討論區是讀者抒發情感的虛擬平臺,如起點中文網的作品討論區、追書神器中的討論區,百度貼吧等。由于此類平臺多具有匿名性的特點,讀者在平臺上進行意見表達時,更容易表現真實的性格[12]。有調查研究顯示,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在匿名情景下,更愿意也更大膽的表態自己真實的想
法[13]。因此通過作品討論區的讀者互動行為來探討讀者的想法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在《學霸的黑科技系統》進行到主角陸舟成為研究生導師時,其小說討論區內有讀者發起了“想報陸教授研究生的同學麻煩到這兒報下名”的投票,投票選項按陸舟在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學科能力劃分,分別是數學、化學、物理等,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讀者在科研學術上的一種進取精神。在劇情進行到陸舟和研究團隊終于實現可控核聚變時,討論區開始關心真實世界的國家“人造太陽”項目,并表達出對國家早日實現可控核聚變技術的希望,如月下射雕2018年11月18日發表了“現實中要是真成功,老百姓應該也能享受到福利,下個月電費少交一半應該是穩了……”。
除此之外,作品討論區內不時會有讀者發出一些屬于有調侃又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評論,例如讀者當盡歡2018年12月3日發表的“剛剛點開這本書,我突然想學習了,嗯,明天去圖書館”,別子固2018年11月27日發表的“感覺大學里的日常才是學霸文和一般都市文的區別所在啊”,皮皮不語2018年11月25日分別發表的“中國夢完成了,后面就是沖出太陽系走向宇宙的節奏了”,道生123發表的“吾生也有涯,而學也無涯”,十三少爺的劍發表的“真的很希望有像陸舟這樣的人幫助國家走向強大,造福國家百姓,這樣的人比什么明星都更值得崇拜”等評論。這樣的評論在以劇情發展為主要討論內容的傳統類型小說討論區中很難出現。
5? 結束語
網絡亞文化之一的網絡小說,作為互聯網開放包容文化的代表性產物,雖然打破了傳統精英文學的表達渠道,但也導致了網絡小說的作品質量參差不齊,低俗下流、口水話多、情節冗長、不符合常理一直是貼在網絡小說上的一道道負面標簽,使之備受爭議。
但是,當網絡小說和以中國夢為代表的社會主流價值觀結合后,網絡小說平臺卻是涌現出一批以實現國家夢和個體夢為敘事主線的游戲化網絡小說。這批小說出現在中國夢的平民化敘事層面,結合了游戲化的敘事發展邏輯,獲得了青年群體的認同。同時,網絡小說作為傳播媒介之一,借助中國夢相關的現實符號為讀者建構了一個模糊了真實與幻想的象征性現實,并直接作用于讀者的主觀現實。綜合作品的特定情節與討論區的讀者評論,以中國夢為敘事主線的網絡小說對主觀現實的作用,更多的體現在經由“中國夢”得以實現的象征性現實,所引起的真實愿望建構。
注釋
①數據引自起點中文網科幻類人氣榜單,最后更新2018年12月9日,http://www.qidian.com/rank?chn=9。
參考文獻
[1]本書編寫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2018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2]馬文霞.“中國夢”的國際話語體系構建與對外傳播[J].江西社會科學,2015(5).
[3]趙光懷,周忠元.平民化敘事與“中國夢”的大眾傳播[J].當代傳播,2014(1):18-19.
[4]孟建,孫翔飛.“中國夢”的話語闡釋與民間想象——基于新浪微博16萬余條原創博文的數據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11):27-43.
[5]楊小柳,周源穎.“亞文化資本”:新媒體時代青年亞文化的一種解釋[J].中國青年研究,2018(9).
[6]陳一.和青少年一起穿越“次元墻”[N].中國青年報,2017-06-26.
[7]黃發有.消費寂寞——網絡文學的游戲化趨向[J].南方文壇,2011(6):19-25.
[8]王義明,阿九.“云養青年”——互聯網新生代群體解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8(10).
[9]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10]劉小源.二次元文化與網絡文學[J].東岳論叢,2017(9):104-116.
[11]康橋.網絡文學中的愿望—情感共同體——讀者接受反應研究之一[J].南方文壇,2013(4):49-54.
[12]Kang, R., Brown, S., &Kiesler, S. Why do people seek anonymity on the internet?:informing policy and design.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ACM,2013:2657-2666.
[13]陳曦.互聯網匿名空間:涌現秩序與治理邏輯[J].重慶社會科學,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