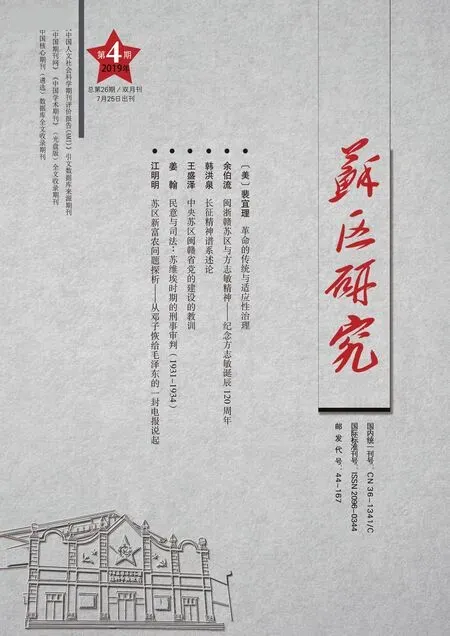中共福鼎縣委成立時間考辯
提要:閩東黨史上認定中共福鼎縣委成立于1933年冬,但圍繞誰為福鼎縣委首任書記的“兩黃之爭”,曠日引久。筆者通過對涉及中共福鼎縣委成立的閩東革命大背景、福鼎革命斗爭史實、老同志回憶文章、農村革命“五老”證明材料以及相關歷史文獻資料的分析考辯,充分發揮史料和史實的力量,厘清中共福鼎縣委這一重要組織的歷史真實,并做出新的認定;同時也希望這一新的認定有助于止息“兩黃之爭”。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福建省福鼎市的黨史研究部門經調查研究,認定中共福鼎縣委成立于1933年冬。但首任書記是黃淑琮,還是黃丹巖,至今難以確定。當地老同志以及兩位黃姓烈士的后人亦是各執己見,爭執不休,即“兩黃之爭”。解開歷史謎團、還原歷史真相的使命,歷史般地落在我們這一代黨史工作者的身上。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共福鼎縣委成立時間的考辯,讓史實說話,發揮史料力量,厘清歷史真實。錯漏之處,請黨史學家、讀者以及“兩黃”后人批評指正。
一、老同志的回憶和證明無法支撐“1933年冬”之說
據《福鼎黨史資料》記載,1930年10月,黃淑琮在店下筼筜村建立了福鼎第一個黨小組后不久,黃丹巖、黃心耕、林則允等10多位黨員先后成立3個黨小組。1931年冬,福鼎沿海幾個黨小組合并,成立了中共福鼎特支,書記黃淑琮。1933年冬,福安中心縣委派詹如柏到福鼎建黨,在筼筜村主持成立了中共福鼎縣委。關于福鼎縣委首任書記到底是黃淑琮,還是黃丹巖?福鼎縣委黨史辦1981年成立后立即著手調查,歷時整整十年,反反復復,備嘗艱辛,但首任書記還是無法認定。
1992年12月,《中共福建省組織史資料》一書出版,遵循“歷史宜粗不宜細”原則處理歷史遺留問題,認為“兩黃”都是福鼎早期黨組織負責人,按照犧牲先后排名,即丹巖之后列淑琮。此后,地縣《組織史資料》出版時,均與省保持一致。
筆者在研究閩東黨史過程中,發現福鼎黨史部門做出“中共福鼎縣委成立于1933年冬”的認定,其主要依據是老同志回憶文章和訪問記錄、解放初期老區調查資料、農村“五老”證明材料以及有關敵偽檔案材料等。但即使是在閩東戰斗過的革命老前輩,如葉飛、曾志、任鐵峰、范式人、鐘大湖、曾阿繆、鄭丹甫等,也未能講清楚福鼎縣委成立的具體時間。
1988年,時任福安中心縣委書記的葉飛同志,于6月3日在北京接見閩東黨史工作者時說:“開始是工委,還沒有成立縣委時是工委,到了成立閩東特委的時候,福鼎就是有縣委。”“開始就是他(指黃丹巖),后來是謝作霖。”當問到“兩黃”哪個為主時,他說:“這個我記不清了。”[注]《福鼎黨史通訊》第41期,總第89期。但1990年12月1日,葉飛同志接見福鼎縣委外調組的同志時,又認定黃淑琮為福鼎縣委首任書記。[注]《關于編寫福鼎早期黨史的一些說明》(1999年5月13日),《福鼎黨史通訊》1999年第6期。
福安中心縣委委員曾志同志,1988年6月3日與閩東黨史工作者面談,當問到“福鼎縣委是1933年冬成立的,領導人是誰”時,她回答說:“我不記得。”[注]《福鼎黨史通訊》第41期,總第89期。
閩東紅軍獨立2團團長任鐵鋒同志,1985年10月25日在回答福鼎縣委相關問題時說:“你們縣的黨史大事記中寫,福鼎成立縣委,書記是黃淑琮,這些我沒印象。沒聽說過福鼎成立縣委,據我個人看,福鼎不可能單獨成立縣委。”
閩東紅軍獨立2團秘書長范式人同志,在1959年7月21日接見福安地委黨史辦同志時,有這樣一段談話記錄:“1933年冬,葉秀蕃、黃淑琮兩同志在福鼎領導革命取得很大進展,是年冬中心縣委派詹寅(如柏)去建立福鼎縣委,黃淑琮任縣委書記。”[注]范式人:《土地革命時期閩東黨的斗爭歷史》(1959年7月21日),《范式人紀念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8頁。
不過筆者以為,范式人同志于1933年5月被捕,12月下旬才獲釋被派回壽寧工作,后一直在紅軍部隊中任指導員、教導員等職。對此前福鼎黨組織的情況并不了解,其消息主要是獲釋回壽寧后從葉秀蕃處得知。
據稱后來擔任浙南特委書記的龍躍同志,有一封信函可作為佐證,“福鼎縣第一任縣委書記,我印象是黃丹巖。”但龍躍是1935年10月后才跟隨劉英、粟裕率領的紅軍挺進師進入閩東的。這樣的佐證顯然也是蒼白無力的。
1984年,福鼎籍老同志鐘大湖在福鼎第二次老同志座談會上明確說:“在我小的時候,1934年,我沒見過‘二黃’,但聽說福鼎的領導人是黃淑琮。”[注]據1984年,鐘大湖在福鼎縣第二次老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錄音資料整理。
1982年,福鼎籍老同志曾阿繆在《憶福鼎早期的革命斗爭》文中寫道:“我當時有聽說黃淑琮同志是福鼎地下黨的縣委書記”,“黃丹巖同志我沒見過,但聽說有這么一個人,對他的革命活動情況我不了解。”[注]轉引自小土:《福鼎首任縣委書記爭議問題已澄清》,《福建黨史月刊》1990年第2期,第40頁。
這兩位福鼎籍老前輩當時都只是剛入伍的紅軍戰士。對“兩黃”都只是聽說,沒見過面,不了解。可見他們的證言只能是僅供參考。
福鼎籍老同志鄭丹甫當時受黨組織派遣到地主民團當排長,他曾回憶說:“1934年1月,新成立的福鼎縣委領導人黃丹巖被捕,2月福鼎縣委書記黃淑琮同志被捕,先后被敵殺害于桐山和秦嶼。”[注]鄭丹甫:《回憶閩浙邊根據地的斗爭》,《黨史資料與研究》1983年第3期。
由于年代久遠,當年親歷者的回憶大多模棱兩可,沒有定數。還有一些老同志“撰寫”的相關紀念文章,表述清晰而肯定,對一些歷史事件和黨史人物的描述也是有鼻子有眼的。眾所周知,老同志和回憶文章大部分是黨史工作者幫助其整理撰寫的。黨史部門的觀點以老同志的名義公開發表后,又被黨史工作者所引用,作為“權威”論據。
那些農村革命“五老”的相關回憶更是自相矛盾,或相互矛盾。有的甚至超出了他們當時的年齡、身份所能知曉黨內秘密的范疇;還有的被人為地植入了記錄整理者個人的觀點。因此這些回憶和證明材料看似很多,但可信度和引用價值并不高。
此外,從現存的敵偽檔案中,也查找不到任何有關福鼎縣委成立時間和領導人任職的資訊和證據,只是稱“兩黃”為“本籍奸匪重要分子”“共首”“土劣”和“共匪”等。
筆者認為,僅憑這些老同志的回憶和“五老”證明材料,不足以支撐“福鼎縣委成立于1933年冬”的認定,同樣也無法確定誰是縣委首任書記。鑒于此,我們只能借助于歷史文獻來進行分析、推論和判定,看看能否解開這一歷史懸疑。
二、諸多史實和史料否定“1933年冬”之說
史料學家認為,雖然記述和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要以史實為據,但僅憑史實并不能總結歷史的客觀。支撐歷史大廈的支柱是史料,它可以建構歷史,也可以改變歷史敘述。
正如沈志華教授所言,歷史學家應當永遠把史料擺在第一位。可見,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征集的史料不多,且“對這些史料缺乏系統的整理,有的還未認真的甄別或作必要的分析研究”;加之受老同志回憶文章和農村革命“五老”證明材料的影響,因此當地黨史部門和縣委組織的外調組,一開始就作出了“福鼎縣委成立于1933年冬”的認定。
30多年來,閩東黨史學界對這一認定似乎沒有什么異議。同樣,福鼎的許多老同志以及兩位早期領導人的后代,也沒有對此提出過質疑。有爭議的只是“誰是首任書記”。故而后來調查、爭論的重點,都集中到“誰是首任書記”這個問題上。倒是忽略了這場爭議的重要前提,即福鼎縣委是否成立?何時成立?
因此筆者認為,解決“誰是首任書記”爭議的關鍵,首先是要弄清福鼎縣委成立的時間問題。而要弄清福鼎縣委成立的時間問題,還必須從源頭上找答案,即從福鼎第一個黨小組入手,循序漸進,讓史實說話,發揮史料力量,還原歷史真相。
(一)福鼎第一個黨小組
據《福鼎黨史資料》載,福鼎店下筼筜村進步青年黃淑琮,1929年春在福州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派回家鄉。他以教師身份為掩護,在福鼎沿海一帶秘密從事革命活動。1930年10日,黃淑琮在筼筜村農民小組中發展黨員,建立了福鼎第一個黨小組,組長黃淑琮。
據《壽寧地方革命史》載,1933年6月初,葉秀蕃到福鼎后,幫助建立了福鼎第一個黨小組,組長黃淑琮。[注]中共壽寧縣委黨史研究室編:《壽寧地方革命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頁。
這與《福鼎黨史資料》的表述,在成立時間上存在較大的差異。
此外,筆者從原福鼎縣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莊孝趙編著的《合抱楓之歌》一書中,也有相似的表述:“葉秀蕃、黃淑琮在宣傳發動中,選擇忠實、可靠的對象,吸收了蔡家城、蔡其擇、陳寶鼎等數十名中共黨員,并建立了福鼎第一個黨小組,第一個筼筜支部和群眾團體。”[注]莊孝趙編著:《合抱楓之歌》,寧德市文化與出版局2007年版,第139頁。
據范式人同志回憶:“1932年黃淑琮回福鼎時很少活動,1933年農歷3月底壽寧暴動起來后,葉秀蕃同志去福州匯報工作,于端午前后被中心市委派到福鼎,福鼎革命才有較大的發展。”[注]范式人:《土地革命時期閩東黨的斗爭歷史》(1959年7月21日),《范式人紀念文集》,第468頁。
福鼎縣檔案館所藏敵偽檔案《福鼎縣三年來特種會報工作總報告》(秘133-2-96-100)也印證了這種說法。“(甲)匪情:查本縣奸偽,起源民國二十一年間,先由壽寧籍著匪葉秀蕃(福高畢業)潛入店下嵐亭一帶秘密活動,事發……”
如果福鼎黨小組是葉秀蕃領導建立的,那其成立時間不是1930年10月,而是1933年6月之后。
當時發展黨員需要上級機關批準,成立黨小組、黨支部更需上級派人主持成立,因此福州市委必然知曉福鼎建黨的情況。可是我們找不到這一時期中共福州市委有關福鼎黨小組的任何文字記載,而其他各地的黨組織在福州市委的文件中都有相關記錄。
(二)中共福鼎特支
筆者反復查閱《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這是國內目前能找到的福建革命歷史文獻之大全,從這套書中同樣沒有找到福鼎特支的相關記載。只有在1932年8月19日《福州中心市委給中央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及,與福州中心市委有工作連系者有屏南、福鼎、壽寧、霞浦、古田等七縣。[注]《福州中心市委關于政治形勢和工作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8月19日),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甲12,內部編印,第163頁。文獻中所謂的“有工作連系者”或“建立了工作關系”,指的是還沒有建立縣委、特支、支部,但已有中共黨員在活動且與市委保持工作聯系的地方。
這份報告只是表明,福鼎此時已經有若干中共黨員在活動。聯系到該報告中同時提到閩東的屏南、壽寧、霞浦、古田等縣,當時已有中共黨員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回家鄉活動,但都沒有建立黨的基層組織。
時至1933年5月1日,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給黨中央的《關于福州的工作報告》,對福州中心市委領導建立的各地基層組織做了一次全面匯總。“現市委除本市十二個支部(同志八十余人),外縣單位五十五個,三個中心縣委(莆田、建甌、福安),兩個縣委連江、仙游,七個特支(永泰、羅源、松溪、松[政]和、寧德、壽寧、建陽),其余三縣有支部(長樂、福清、霞浦)。不過最近新建立了古田、沙縣兩縣的工作關系”[注]陶鑄:《關于福州的工作報告》(1933年5月1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甲13,內部編印,第70頁。。至此還是未提及福鼎特支。
此后不久,葉秀蕃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到福鼎開展工作。
同年9月19日,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陳之樞在《關于福州地區形勢和斗爭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中,只提到“在市委領導下福安中心縣委,有寧德縣委,壽寧特支”[注]陳之樞:《關于福州地區形勢和斗爭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9月1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甲13,內部編印,第131頁。。直到1934年1月30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關于福州、福安、連江工作給中央的報告》中依然明確寫道:“福鼎還沒有黨的支部。”[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關于福州、福安、連江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1月30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甲13,內部編印,第234頁。
筆者認為,“中共福鼎特支1931年冬成立”之說,缺乏文獻依據。由此可見,福鼎黨史研究從一開始就將本地早期中共黨員的革命活動時間,特別是建立早期黨組織的時間提前了。
(三)中共福鼎縣委
據《福鼎黨史資料》記述:1933年5月,福州中心市委派原壽寧特支書記葉秀蕃到福鼎加強領導。是年冬,福安中心縣委認為成立福鼎縣委時機已成熟,委派詹如柏到福鼎建黨,在店下筼筜村主持成立了中共福鼎縣委。1934年一二月,黃丹巖和黃淑琮相繼壯烈犧牲后,由謝作霖(后叛變)接任縣委書記,委員蔡家城、蔡愛鳳,繼續領導革命斗爭。是年四五月,福鼎縣委所轄的部分區域被析出,分別成立了霞鼎縣委和霞鼎泰縣委。但福鼎縣委依然存在,書記仍由謝作霖擔任,直到1935年8月,福鼎縣委劃歸特委鼎平辦事處領導。
筆者以為,“中共福鼎縣委成立于1933年冬”,表述不夠準確。
眾所周知,農歷冬季的概念十分寬泛,1933年冬的跨度為當年的11月8日至次年的2月3日。從同期的歷史文獻看,福鼎只是與福州中心市委建立了工作聯系。中心市委在外縣建立的縣委、特支、支部名單中,也不見福鼎。在還未建立基層黨組織的前提條件下,筆者不認為福安中心縣委會從福鼎黨小組一步到位,正式建立福鼎縣委。
福鼎黨史部門曾經將《福安中心縣委擴大會后三個月來的工作報告》中提到的,“對閩東領導成立四個縣委,即上南區、東區、霞浦一個縣委,下南區、西區、寧德一個縣委,北區、壽寧一個縣委,福鼎一個縣委”[注]《福安中心縣委擴大會后三個月來的工作報告》(1934年2月16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甲19,內部編印,第244頁。,作為福鼎縣委已經成立的重要依據。
但是結合該報告的前后文內容可以看出,這只是工作部署與計劃,并不能作為福鼎已經成立縣委的文獻依據。事實上,福安中心縣委12月底成立了福霞、安德、福壽3個邊區縣委,福鼎由于尚不具備條件未成立縣委,而是到翌年4月初才成立霞鼎縣委。
不過,筆者在這份《工作報告》中,找到了建立福鼎縣委的相關記載:“福鼎已派老詹同志去巡視,日內即可回來,據報告,臨時縣委可以建立,工作則很普遍,但都是群眾組織來開始建立支部。因為福鼎是葉少蕃(脫離了黨的組織)發展起來的,根本沒有一個同志,這次才派老詹去。”[注]《福安中心縣委擴大會后三個月來的工作報告》(1934年2月16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甲19,內部編印,第244頁。
從“據報告,(福鼎)臨時縣委可以建立”這句話來看,只能說明福鼎臨時縣委已經具備條件“可以建立”,但并不表明已經建立。可是,就在福安中心縣委將成立“福鼎一個縣委”納入工作計劃,且已具備“可以建立”條件之時,發生了一個足以影響福鼎革命進程的重大事件。就在《工作報告》成文后3天,福鼎冷城武裝暴動失敗。2月19日,福鼎黨組織早期領導人黃淑琮不幸被捕,2月23日英勇就義。而在此之前,福鼎黨組織早期領導人黃丹巖,已于1月10日不幸被捕,1月27日壯烈犧牲。由于福鼎冷城暴動失利,加上黃丹巖和黃淑琮先后犧牲,福鼎黨的領導力量和赤衛隊武裝受到嚴重損失。福安中心縣委原定成立福鼎臨時縣委的計劃部署,因此夭折。
從這份歷史文獻來判斷,原先當地黨史部門做出的“福鼎縣委成立于1933年冬”的認定,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即使退一步做假設說,老詹從福鼎巡視回去后,福安中心縣委立即成立福鼎臨時縣委,最早也在2月下旬。而2月3日之后就已經是1934年的春天了,何來的“福鼎縣委成立于1933年冬”之說?按同樣的邏輯推理,黃丹巖、黃淑琮倆同志已經壯烈犧牲,都不可能成為首任縣委書記。
緊接著,是年4月初,福安中心縣委在福鼎和霞浦毗鄰地區,正式成立了霞鼎縣委,書記鄭宗玉,縣委駐地霞浦柏洋鄉陳羅洋村。霞鼎縣委管轄福鼎境內的5個區委和霞浦境內的8個區委。原在福鼎領導開展革命活動的葉秀蕃,調回閩東蘇區首府福安溪柄柏柱洋,擔任中心縣委機關報《紅旗報》編輯,6月任閩東蘇維埃政府副主席。謝作霖則進入霞鼎縣委領導班子。
2013年12月,筆者從閩東蘇維埃主席馬立峰嗣孫馬騰輝那里,征集到馬立峰1934年八九月間寫給施霖的一封書信。信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表述:“入春以來,我黨連續召開霞鼎縣委會議,謝作霖等同志在會上相繼發言,強調雙方立即停止沖突,同謀對敵……”[注]繆小寧:《閩東蘇維埃1934》,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頁。這封信印證了謝作霖此時的身份并非福鼎縣委書記,而是霞鼎縣委委員。
1934年6月,霞浦柏洋又成立了霞鼎縣蘇籌備處,8月霞鼎縣蘇正式成立。福鼎境內的上南、下南、沿海等5個區蘇,也歸屬于霞鼎縣蘇管轄。
在此情況下,再成立福鼎縣委、福鼎縣蘇已無必要。
如果堅持認定“福鼎縣委依然存在,書記仍由謝作霖擔任”,那么福鼎縣委在閩東蘇區的各縣中便表現出異常的另類,就無法解釋福鼎革命在鼎盛時期1934年間存在的諸多匪夷所思的狀況:
為什么在1934年2月至1935年3月期間,福鼎縣委的工作和領導人的活動,出現難以置信的空缺和斷裂?
為什么福鼎縣委書記謝作霖成了霞鼎縣委的委員?
為什么本該由福鼎縣委管轄的福鼎境內上南、下南、沿海等數個區委,卻歸于霞鼎縣委管轄,而自己成了光桿司令,但為了與省市《組織史資料》保持一致,只好將這些區委“劃撥”到福鼎縣委屬下?
為什么福鼎縣委沒有像閩東蘇區其他各縣那樣,相應成立自己的縣級蘇維埃政權,領導開展分田運動?不論歷史文獻還是老區調查材料,都沒有福鼎縣蘇的只言片語。
為什么福鼎縣委沒有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年逾半百的“福鼎縣委書記”謝作霖率領的是霞鼎獨立營第八支隊,史稱“白毛隊”。
為什么福鼎縣委沒有相應成立團縣委和婦女聯合會等群團組織?
為什么《福鼎組織史資料》《福鼎革命史稿》中的人員職務和上屬領導機構,與《福鼎烈士英名錄》對不上號?
正如1999年5月13日,福鼎縣委黨史研究室呈報給縣領導的那份《關于編寫福鼎早期黨史的一些說明》中坦言,“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這又何嘗不是個天大的謎?”“真可謂斬不斷理還亂”[注]《福鼎黨史通訊》1999年第6期。。
上述這些情況有悖常理,令人費解。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福鼎縣委此時并不存在。1934年間,領導福鼎革命的是霞鼎縣委、霞鼎縣蘇。
愚見以為,以上這些歷史疑問其實和福鼎縣委的成立都是有關聯的。只要能破解福鼎縣委究竟于何時成立這個關鍵問題,其他諸多歷史疑難也將迎刃而解。
三、歷史文獻進一步否定“1933年冬”之說
由于受到歷史的、時間的局限,那些身份和經歷相當有限的農村“五老”們的口述記錄只供參考,即便是歷史當事人的回憶也難免掛一漏萬。殊不知,一份歷史文獻往往勝過一打所謂的證明材料。因此,記述重要歷史事件或重要組織或重要人物,僅僅依賴老同志的回憶文章或“五老”的證明材料是不夠的,它更倚重于歷史文獻資料。
因歷史原因,有關閩東黨史的文獻資料原本就不多。自1934年4月初福建臨時省委被破壞后,更是出現了斷檔,這給閩東黨史研究帶來很大困難。不過,閩東黨史還是有幸的。就在1934年十一二月間,閩東臨時特委書記蘇達在上海給我們留下了3份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
在國民黨軍隊即將大舉“圍剿”閩東蘇區的前夕,閩東臨時特委書記蘇達按照不久前北上抗日先遣隊留下的一個黨中央在上海的聯絡地點,在特委機關工作人員阮伯淇的陪同下,于10月上旬末離開閩東前往上海,尋找黨中央匯報工作。
蘇達抵達上海找到上級黨組織后,在阮伯淇的幫助下,夜以繼日趕寫了3份書面匯報材料。分別是《關于閩東形勢及黨的組織情況的報告》(1934年11月18日)、《關于特委及各縣委組織情況的報告》(1934年12月14日)和《關于紅軍組織情況的報告》(1934年12月14日),代表中共閩東臨時特委呈報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
據蘇達給中央的《關于閩東特委及各縣委組織情況的報告》中記載:“特委領導之下,有安德縣委、福霞縣委、霞鼎、福壽、福安[安福]縣委、寧德臨時縣委,連羅縣委、壽寧特區。”閩東蘇維埃政府下轄的“縣政府共有6個,正式成立縣蘇的,是福霞縣、安德縣、福安[安福]縣蘇、連羅縣蘇、福壽縣蘇、霞鼎縣蘇,還未正式成立[的],于十日內可完全正式成立”[注]中共閩東臨時特委:《關于閩東特委及各縣委組織情況的報告》(1934年11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叢書資料編審委員會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閩東游擊區》,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頁。。
對于蘇達這3份報告,范式人同志曾經指出“有許多不實之處”。但從筆者對它的研究分析來看,其對閩東黨組織早期歷史的追述部分,的確存在一些錯漏。這與他早年不在閩東工作,不了解具體情況有密切關系。而對1934年3月至10月上旬期間閩東地區發生的大事,他還是了解的,記述也是客觀準確的。從3份報告中引用了大量的數據和領導人姓名及代號這一點來看,蘇達到上海匯報工作,是有備而去的。
正是現存于中央檔案館的那3份歷史文獻,使當時的黨中央對閩東蘇區的情況大致有所掌握。同樣,它也為今天的史學工作者研究閩東黨史、革命史,提供了3份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因此,蘇達的這3份報告,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包括福鼎縣委、霞鼎泰縣委在內的幾個閩東蘇區的黨政組織,在這3份報告中都不曾被提及。這只能說明這些黨政組織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如果認為這是蘇達記憶上的疏漏,筆者以為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有理由認為,1933年冬福鼎縣委并未成立,至少到1934年10月蘇達離開閩東到上海找黨中央之前,福鼎縣委還未成立。甚至可以認為,1934年10月之后直至1935年3月,福鼎縣委成立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因為此時,國民黨當局正調集重兵大舉“圍剿”閩東蘇區。在敵人的瘋狂進攻下,蘇區首府柏柱洋和各縣縣委、縣蘇駐地相繼淪陷。大批黨政軍領導人犧牲,各縣黨政組織遭致破壞,被迫轉入地下活動。1935年1月15日,閩東主力紅軍被迫撤出福安中心蘇區,轉入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在這種嚴峻惡劣形勢下,還有可能成立福鼎縣委嗎?
四、中共福鼎縣委成立于1935年三四月間
中共福鼎縣委究竟成立于何時,的確是一個歷史難題。因為它沒有直接的史料依據,也沒有哪個老同志的權威回憶。我們只能通過對當時閩東革命歷史大背景的觀察分析,尋覓事件發生發展的脈絡和走向,探究歷史的結局,力求得出客觀的結論,復原真實的歷史面貌。
1935年初春,是國民黨重兵“圍剿”最瘋狂的時期,也是閩東革命最黑暗的時期。經過敵人4個多月的殘酷“圍剿”,福安中心蘇區已經淪陷,各縣根據地被分割,地下交通網絡被破壞,閩東臨時特委與各縣委之間的聯系幾乎全部中斷。只余下少數在兩縣交界的崇山峻嶺間,由一批堅定的領導人率領余部在各自的區域中獨立堅持,與敵周旋。
在這一艱難時期,原霞鼎縣委書記鄭宗玉和縣委委員謝作霖等人,不僅與閩東臨時特委和閩東紅軍獨立師失去了聯系,而且與霞鼎縣委委員許旺所部也失去了聯系。他們和黃固生、羅烈生、蔡加城、蔡愛鳳等人,在敵人“圍剿”力量相對比較薄弱的福鼎與平陽交界地區,獨立堅持游擊斗爭。
是年3月,國民黨當局認為閩東“匪患”基本剿滅,便將國民黨軍主力陸續撤離閩東,敵情得以緩和。在各地隱蔽堅持的葉飛、阮英平、范式人、鄭宗玉、許旺等領導同志和閩東紅軍余部又開始活躍起來,重振旗鼓。
筆者推斷,這是最可能誕生中共福鼎縣委的歷史窗口期。
根據對敵斗爭的需要,鄭宗玉和謝作霖等人認為必須盡快建立黨的組織,形成領導核心。于是自主決定成立中共福鼎縣委,由原任職于霞鼎縣委委員的謝作霖擔任書記,組成成員有黃固生、羅烈生、蔡加城、蔡愛鳳等人。
由于處在特殊時期,此時成立的福鼎縣委自然不為多數人所知。但是他們率領霞鼎獨立營第八支隊,襲擊福鼎店下民團、攻打店下嵐亭保安兵等消息,還是被在相鄰地區堅持斗爭的許旺所獲知。許旺與范式人、葉飛的隊伍相繼會合后,又將這些新情況向特委領導做了匯報。
因此,葉飛和阮英平在5月上旬研究閩東全盤工作時,做了相應的規劃分工:“寧德成立一個辦事處,領導古屏、寧德、安德、周墩,小阮(即阮肖遠)、東玉(即鄭宗玉)可能回來時,寧德辦事處書記小阮負責;霞鼎、福鼎、福霞成立一個辦事處,向浙江發展,書記鐘[宗]玉負責;福壽、安福、壽寧成立一個辦事處,書記小范負責……”[注]阮英平:《致安德縣委暨陳鴻、嫩妹等人的信》(1935年5月15日),《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閩東游擊區》,第73頁。
筆者注意到,古歷四月十三日,阮英平化名“楊贏”寫給安德縣委的這封指示信中,其開列的閩東各縣縣委清單上,已經出現了“福鼎”。這是目前看到的第一份關于中共福鼎縣委的文獻資料,也印證了筆者對福鼎縣委成立時間的分析推論。
5月中旬,葉飛率閩東紅軍獨立師第四團取得福鼎仙蒲楓岔頭伏擊戰勝利后,得知鄭宗玉領導建立的福鼎縣委及其游擊武裝正在鼎平地區活動。隨即率部馬不停蹄前往福鼎后坪的龜洋,與鄭宗玉、謝作霖等人勝利會合。至此,自主成立孤軍作戰的中共福鼎縣委,終于與上級領導接上關系。
為了幫助福鼎縣委盡快打開局面,葉飛重新整頓了紅四團,從其中抽調了一批骨干力量,加上霞鼎獨立營第八支隊以及在當地擴招的新兵100余人,在龜洋附近成立了閩東獨立師第五團,約有150人槍,團長吳德興、政委陳義成。
在6月1日(農歷五月初一)召開的閩東臨時特委“含溪會議”上,新成立的福鼎縣委、霞鼎泰縣委與福霞、霞鼎、安福等縣委一道,正式歸屬閩東特委霞鼎辦事處的領導。
接著,在8月召開的閩東特委“楮坪會議”上,中共福鼎縣委歸屬新成立的閩東特委鼎平辦事處的領導。中共福鼎縣委肩負向浙南平陽方向發展的使命,開始了創建浙南游擊根據地的新征程。
通過上述對大量史實和史料的辨析、研判可知,中共福鼎縣委并非成立于1933年冬,而是1935年三四月間。換句話說,在黃丹巖與黃淑琮先后壯烈犧牲之前,福鼎縣委還沒有成立。由此而言,圍繞究竟誰是中共福鼎縣委首任書記的“兩黃之爭”,已失去了由頭和基礎。
但是歷史不會忘記,黃丹巖和黃淑琮同是福鼎革命早期領導人。他們獻身于革命事業的崇高品德與堅貞不渝的革命精神,永遠鼓舞著閩東人民繼承先烈遺志,為建設美好小康社會而繼續奮斗。閩東人民永遠懷念這兩位為創建閩東蘇區而英勇犧牲的優秀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