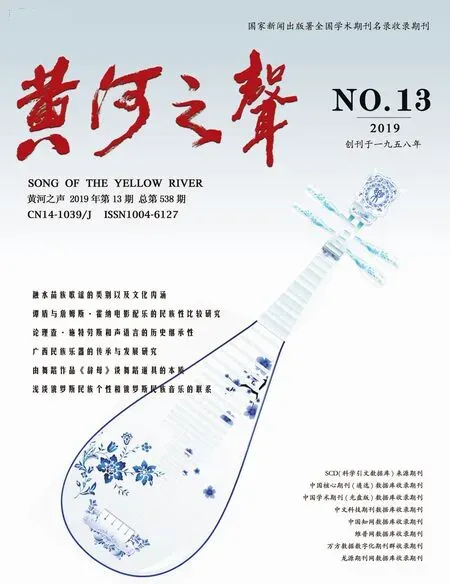由舞蹈作品《辭母》談舞蹈道具的本質*
潘春枝 朱培科
(嶺南師范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廣東 湛江 524048)
舞蹈道具本質的探討是對舞蹈道具內涵的探尋。當前,對舞蹈道具內涵的定義,有以下兩種權威解釋:《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對舞蹈道具的內涵界定為“為舞蹈表演而制作的用具,是構成舞蹈藝術形象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舞蹈詞典》將舞蹈道具定義為“是舞蹈表演時所用的舞具,是塑造人物性格刻畫人物性格的輔助手段,也是表現環境渲染氣氛的有力工具。”兩者定義相比較,前者將舞蹈道具的關注對象界定為“舞蹈藝術形象”比后者的“人物性格”更為貼切。因為“人物性格”不能涵蓋所有的舞蹈表達對象。回顧舞蹈的發展歷史,舞蹈演繹不僅涉及人文社會歷史題材,還有早期的自然模仿。自然模仿的對象是大自然的飛禽鳥獸或自然風光,而不是人物性格的刻畫。例如,著名舞蹈藝術家楊麗萍演繹的“孔雀舞”是對孔雀的模仿。不過,上述兩者解釋將舞蹈道具的角色與作用界定為“輔助”是符合舞蹈實際的。常言道:“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對事物現象的看法可因立場視角的不同而有所異。對事物本質的看法,也可以因基于不同的理論范式而持有多種觀點。那么,舞蹈道具是什么?將以藏族舞蹈《辭母》為例,從舞蹈道具存在的目的因、質料因、動力因、形式因視角切入,探討舞蹈道具存在的本質。
一、舞蹈道具為創造舞蹈形象而存在
舞蹈道具是一種工具性存在。所謂“工具性存在”是相對于目的性存在而言。舞蹈道具是為了創造舞蹈形象這一目的而存在的工具。更深層次而言,舞蹈形象是舞蹈演員利用姿勢創造的舞蹈幻象。美國舞蹈美學家蘇珊·朗格認為藝術是創造出能表現人類情感的知覺形式,其本質是一種基本幻象。不同類型藝術之間的本質區別在于其獨特的藝術幻象,每一件真正的藝術作品都具有離開現實的“他性”。“他性”是一個純粹的表象,是一個能夠表現情感的意象。舞蹈藝術則是“一種虛幻的力的王國——不是現實的、肉體所產生的力,而是由虛幻的姿勢創造的力量和作用的表現。”[1]舞蹈是一種虛幻的力,是對觀眾而言形成的力。力量的大小與舞蹈演員的姿勢、演繹的題材、情節以及烘托舞姿、渲染氣氛的舞蹈道具相關。正是舞蹈姿勢、舞蹈題材、舞蹈情節、舞蹈道具共同創造的合力,因而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的改變都將直接影響舞蹈的舞臺效果。
舞蹈道具的獨特元素確立了舞蹈的風格特征。舞蹈道具有共性元素和獨特性元素之分。獨特元素又具有地區性、民族性之別。舞蹈道具的共性元素是編創舞蹈所共同具備的元素。獨特性元素有地區性元素。例如:北有安塞腰鼓,南有普寧英歌。腰鼓、英歌槌的舞臺運用,呈現了濃厚獨特的地區特色。舞蹈道具的獨特性元素還有民族性特色。“我們可以根據一只象腳鼓、一頂尖頭斗笠、一件羊皮襖等帶有鮮明地域民族特色”[2]來識別民族屬性。正是多元存在的舞蹈道具的運用創造了多元存在的民族民間舞。有的民族民間舞甚至以道具名稱來命名,以致舞蹈離開了道具就失去了原有的表達意義。第一批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佤族木鼓舞,還有分布廣泛的苗族、侗族等民族創造的蘆笙舞、獨具特色的黎族竹竿舞、東北、陜北地區的紅綢舞等都是以舞蹈道具來命名。因此,舞蹈道具的工具性存在,除了共性的功用之外,還具有確立民族獨特舞蹈風格、舞蹈名稱的作用。
藏族運用傳統袖舞、山南鼓、熱巴能編創出具有各具風格的舞蹈形態。這些道具的運用使藏族舞蹈更具有獨特的民族特色,確立了藏族舞蹈的風格特征。藏族舞蹈作品《辭母》囊括了華北地區舞蹈編創大賽一等獎等多項大獎,其道具的運用尤為具有代表性,編導選擇了藏族當地婦女腰部所系的“幫典”。“幫典”在漢語中代表著圍裙的意思,而藏族文化中的“幫典”僅限于已婚婦女才能系戴,并且僅留傳于西藏地區,這對于藏文化來說是獨一無二的民族標志。因此,編導選擇獨具特色的“幫典”是基于道具獨特性元素的考慮,更是符合《辭母》雙人舞中的劇情需要。同時,既符合了作品中人物之間關系與環境背景的解說又推進了劇情發展的需要,創造了獨特豐富的藝術形象。
由上可知,對于表現舞蹈主題,創造舞蹈形象而言,舞蹈道具是一種工具性存在。對于確立民族獨特風格特征、舞蹈名稱的民族舞蹈而言,舞蹈道具起著重要的保存民族文化價值的作用。隨著歷史變遷、環境變化、生活磨難,若沒有起到舞臺效果的輔助性作用,民族的舞蹈道具或許將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
二、舞蹈道具助推了舞蹈形象的形成
清代著名文學家曹雪芹曾說:“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我”是舞蹈創作的主旨,舞蹈的作用在于運用舞蹈姿勢、舞蹈道具創造了“形象我”。“我”是什么樣的形象,既可以單獨運用舞蹈姿勢創編而成,也可以是舞蹈姿勢與舞蹈道具合力而為。這里面存在一個“三角形”立體關系,舞蹈形象是存在于舞蹈姿勢、舞蹈道具之上的角尖,舞蹈姿勢是左邊的角尖,舞蹈道具是右邊的角尖,左角尖的舞蹈姿勢與右角尖的舞蹈道具合力創造出至上的舞蹈形象。當然,舞蹈也可以是不需要舞蹈道具,也可以創造出舞蹈形象,呈現出“一字形”的結構。舞蹈形象是位于上端,舞蹈姿勢位于下端。從這個意義而言,舞蹈道具的作用是助推舞蹈演員創造了舞蹈形象。
具體而言,舞蹈道具的運用起到深化主題、渲染氛圍、傳情達意的效果。舞蹈的創編是舞蹈編導在想象中建構,根據舞臺效果在嘗試中完善,建構出符合主題需要與審美意識的舞蹈形象。深化主題是舞蹈道具能更好地表現出舞蹈主題,能將舞蹈蘊涵的思想情感呈現給觀眾。渲染氣氛、傳情達意更多是審美意識的需要,即德國美學家克羅齊所說的“美即表現,美即直覺”。在克羅齊看來,藝術活動是在心靈中為事物賦予形式。藝術創作是為人類的情感賦形,情感中有形式,形式中有情感,情感與形式交融。觀眾是通過藝術形式直觀藝術作品的本質。道具運用的獨特性是對特殊環境、獨特角色的一種呈現。有時候,融入舞蹈道具可以更加惟妙惟肖地表現舞蹈主題、創造舞蹈形象。舞蹈道具運用帶來的直觀呈現有利于加深觀眾對作品的理解,更好地讓觀眾了解舞蹈作品的精妙之處。
舞蹈藝術的精髓在于精彩的技藝中演繹深刻的主題。“技藝”的精彩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舞蹈演員出彩的舞姿,另一方面是舞蹈道具恰到好處的運用。舞蹈姿勢更多時候創造的是視覺效果,而舞蹈道具除了輔助視覺效果之外,還可以帶來聽覺效果,讓觀眾感受到演員的觸覺效果。這意味著舞蹈道具的加入豐富了舞蹈演員呈現的舞蹈形象,給觀眾帶來多維度的審美感受。《辭母》以藏族女子雙人舞作為表現形式,編導以道具作為故事發展媒介。穿針引線講述著織布、玩耍、辭別三個舞段,道具在舞蹈均是布、畫、時間、空間、捉迷藏背景、蓋頭……各種不同的呈現方式。
三、舞蹈道具需要靈動多樣的形式表達
舞蹈道具的形式多樣表達在于道具呈現的隱喻。道具運用在舞蹈中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個是“能指”,即事物本有意義。例如,紅綢就是紅綢。但是,還有道具呈現的隱喻,即所象征的“延伸意義”。“漢族民間舞蹈‘魚舞’中的‘魚’寓意為富富有余,‘獅舞’中的‘獅子’寓意為吉祥如意等”[3]。如果說舞蹈道具的工具性存在是舞蹈道具的內在機理,那么形式表達則是舞蹈道具的外在呈現。舞蹈道具作為舞蹈姿勢之外的輔助性舞蹈語言,不是舞蹈演員的舞臺裝飾品,而是與舞蹈主題、劇情、人物形象相符合。
道具在舞蹈中的身份可以各式各樣,有時表現為環境、有時是景物、有時是人。需要說明的是,如果編導過于追求道具的獨特性與技藝性,往往忽略了道具運用的合理性。舞蹈道具的獨特性與技藝性運用合理,確實能提升舞蹈的質量。不過,如果編導過于盲目追求獨特與創新,忽略了演員對道具的實操性,給觀眾呈現的是碎片化的視覺效果,在此情況下,道具在舞蹈表演中可有可無。相反,編導應依據主題、劇情、演員的能力而選擇舞蹈道具,將給觀眾帶來美的視覺盛宴,做到錦上添花。畢竟,舞蹈形象是整個舞蹈的靈魂與核心,作品是否成功在于對舞蹈形象的塑造。因而編導選擇舞蹈道具,除了要考慮道具的獨特性與技藝性之外,還需要考慮演員對道具的實操能力。
在作品《辭母》中,編導設定了兩個人物,分別是母親形象與女兒形象。樸實的母親用勤勞的雙手為女兒織著長長的“幫典”,這一個畫面體現出母親從勞作中透露了淳樸、善良的一面。女兒通過幫助母親織布情景反映出頑皮、可愛的一面。母親與女兒以道具“幫典”作為橋梁,呈現出生動、鮮明的人物性格。道具“幫典”雖然只是為舞蹈作品服務的道具,但是它起到烘托效果,傳情達意,深化主題的作用。隨著劇情的推進,編導借助“幫典”,創造出女兒和母親捉迷藏、躲貓貓的場景,呈現出藏族母女之間的深厚情誼。由編織“幫典”的靜態場景,到運用“幫典”靈活互動的動態場景,一靜一動,呈現出“幫典”作為舞臺道具的靈活運用。“靈活”是為了活化舞蹈形象,呈現出人物性格、人物心理和情感的對話。
舞蹈道具作為一種工具性存在,在舞蹈表演中被賦予了多重寓意。編導突破了傳統的創作思維,巧妙運用道具為作品帶來“點睛之筆”。道具作為一種表象性符號,承載了編導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不管是何種道具,都是一種外在的形式。形式固然吸引人,關鍵在于形式能否輔助表達思想情感,推動劇情發展到新的高度。舞蹈《辭母》以“幫典”為舞蹈道具,凸顯藏族文化特征和當地的人文風情,雖然在舞蹈中道具的表達多種多樣,但是道具的各種情景表述都離不開當地的民俗文化,如水袖、織布、帶幫典,道具自然的融入了民族風俗文化,均為舞蹈《辭母》奠定了藏族風格特點,直觀呈現藏族人們的精神風貌和性格特征。
“任何一部優秀的舞蹈作品,如使用了道具,其作為一個具體的實物,置身于舞蹈作品中,根據主題設定和需要,就必然衍生出很多象征性隱喻,那么必將會在設計表達的過程中賦予更多、更深層次的意義。”[4]編導在開頭采用畫卷形式,女兒躲在畫卷背后,母親用樸實的雙手織著“幫典”,隨著“幫典”在母親的手中越織越長象征著母親為女兒譜寫了畫卷中一樣美妙的人生道路,第一段織布舞段,道具間接達到了時空轉換目的,凸顯了虛實結合的夢幻效果。第二段舞段部分“幫典”寓意藏族傳統水袖,編導打破傳統穿在身上的水袖,利用道具的長度猶如水袖一般披在肩膀上,則雙手握著“幫典”揮舞著,女兒猶如精靈般帶著彩虹在空中跳舞,形成一道獨特亮麗風景,這時道具既能表達人物之間的情感紐帶又能渲染舞臺的氣氛也能為作品提高技巧部分,讓作品達到了唯美的視覺文化盛宴。第三段離別之前舞段,象征水袖的“幫典”回歸開頭情景,首尾呼應聯系著整個劇情的發展。女兒幫母親共同把織完的“幫典”折疊起來,離別之前重溫母女之情。第四段辭別舞段,隨著劇情的發展“幫典”寓意為女兒出嫁的蓋頭,母親為女兒帶上蓋頭,演繹母女辭別之情,道具巧妙的把敘事與抒情完美結合。女兒在遙遠的路上拋開“幫典”越走越遠,道具這時寓意著女兒離開的道路,母親看著遙遠的背影順著女兒離開的道路用自己的雙手進行空間的撫摸與接觸。
四、結語
舞蹈的本質是什么?以上是基于舞蹈道具存在的“四因”進行分析,分別是目的因、質料因、動力因、形式因。對于目的因而言,舞蹈道具是一種工具性存在,服務于舞蹈形象的創造。對于質料因而言,舞蹈道具是一種共性存在與獨特性存在,獨特性存在還分有地區性存在、民族性存在。對于動力因而言,舞蹈形象、舞蹈姿勢與舞蹈道具構成“三角形”的關系,舞蹈形象高居舞蹈姿勢、舞蹈道具之上,舞蹈姿勢與舞蹈道具作為邊角而并存。以舞蹈姿勢的演繹為主,以舞蹈道具的運用為輔,合力創造美的舞蹈形象。可以說舞蹈道具的存在助推了舞蹈形象的創造。對于形式因而言,即使是同一種道具在舞臺上的運用,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依據主題、劇情、演員能力的需要才靈活運用道具呈現豐富的形式。因此,舞蹈道具是一種為創造舞臺形象的工具性存在,具有共性與獨特性的元素,具有形式多樣的特征。
在《辭母》中,利用道具“幫典”貫穿舞蹈演繹的全過程。為觀眾呈現藏族地區一位勤勞淳樸的母親從編織“幫典”開始,到母女圍繞“幫典”戲玩,再到最后的送女出嫁回顧“幫典”凝聚的濃厚母女之情,著實令人感動。“幫典”作為藏族地區的獨特性存在,讓人看到“幫典”就想到了藏族。“幫典”的運用確立了藏族舞蹈的風格特征。“幫典”不僅深化了主題,也通過“幫典”推進了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串聯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將深厚的母女情意表達出來。其中,“幫典”的靈活運用起到了助推劇情發展,創造豐富形象的良好效果。往更大的方面說,舞蹈之美不僅在于技藝,更在于承載的獨特人文價值。要傳承和發展好當代中國民族民間舞,需要重視獨特的道具在民族舞蹈中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