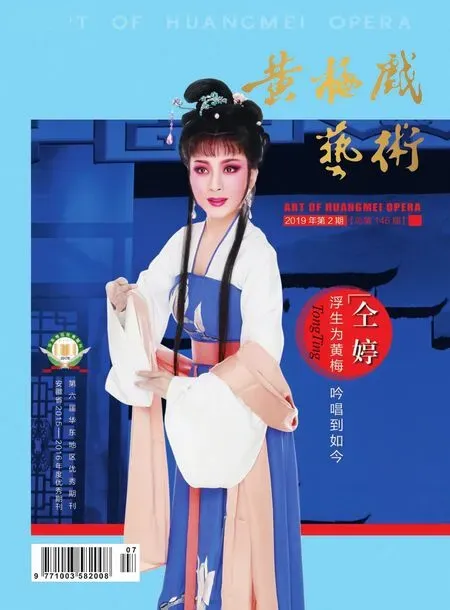岳西高腔表演淺談
□ 余培蘭
說(shuō)起戲曲表演,“四功五法”(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被視為戲曲界通行的金科玉律。
那么岳西高腔的表演也循此規(guī)么?不盡然。因?yàn)樵牢鞲咔皇敲鞔嚓?yáng)腔的后裔,青陽(yáng)腔是在“四功五法”尚未總結(jié)成型之前的幾百年就已經(jīng)唱遍大半個(gè)中國(guó)了,所以岳西高腔的表演規(guī)律與生俱來(lái)就有其自身特色。比如,岳西高腔的表演形式有“場(chǎng)上”和“場(chǎng)下”兩種。“場(chǎng)下”的表演是圍鼓坐唱,彩唱和彩扮走唱,具有曲藝特點(diǎn),承襲的是青陽(yáng)腔“唱、幫、打”三位一體的特征。“唱”當(dāng)然是演員的演唱,“幫”是一唱眾和的眾人幫腔,“打”則是指伴奏的打擊樂(lè)(不用管弦)。其演出主要是為民俗服務(wù),是民俗文化的組成部分。至于身段、步法,僅在“走唱”中有所運(yùn)用,但要求不嚴(yán),傾向自然。“場(chǎng)上”的表演是何形態(tài)?通過(guò)請(qǐng)教專家、走訪老藝人、查閱文獻(xiàn)資料,才有所了解。原來(lái)岳西高腔深藏許多寶貴的表演藝術(shù)資源。以身段為例,全國(guó)大多劇種都演過(guò)的小和尚《馱尼》(或稱《雙下山》),岳西高腔就是同中有異。其表演最富有特色的是《馱尼》的“馱”法,不是常用的“正背”(同向背),而是“大反背”(不同向)。方法是:二人背部相對(duì),小和尚彎腰雙手向后托住小尼彎曲的雙膝;小尼則仰靠于小和尚后背,同時(shí)曲膝雙腳緊靠小和尚腰部。這種反背法,在身段表演中須保持高度平衡與協(xié)調(diào)一致,難度很大,稍有疏忽便掉了下來(lái)。其次是“過(guò)冷水河”的步法,因小和尚嘴中銜著僧鞋而不能開(kāi)口(小尼則手執(zhí)云帚連唱帶做),只能通過(guò)各種表情和步法來(lái)表達(dá)劇情與待定環(huán)境。如以“擦步”表示摸水前行;用“踮步”表示過(guò)冷水淺灘;走“移步”也稱“云步”,表示過(guò)河謹(jǐn)慎小心;用“抖步”,表示山河之水冰冷刺骨;“飄步”表示水浮力較大,腳被水沖得飄忽不定;而“滑步”則表示山河中長(zhǎng)滿青苔的石頭滑溜。當(dāng)小和尚背著小尼行至河中心,小尼深情地一聲呼喚“和尚!”小和尚情不自禁地開(kāi)口應(yīng)聲,僧鞋掉進(jìn)河里被水沖走,此時(shí),劇情達(dá)到高潮,節(jié)奏突快。小和尚以“急錯(cuò)步”、“急滑步”以及前傾后仰,左歪右斜等一系列動(dòng)作,來(lái)表現(xiàn)他欲想趁水追鞋,又怕背上小尼落水的復(fù)雜心情和特定情景。小尼必須要配以相應(yīng)的身段。由于是“反背”,要完成這些難度較大的動(dòng)作十分不易。故岳西高腔有“《斬妖》靠嘴(說(shuō)白多),《馱尼》靠背”之說(shuō)。
再比如,岳西高腔《啞背瘋》的特技表演形式。劇情是:瘋癱女由啞丈夫背著,向在“念緣橋”上施齋的傅齋公求濟(jì)。啞丈夫與妻子兩個(gè)角色由旦角一人表演。須特制道具:兩個(gè)與真人大小一樣的半截假人。一截是男性(啞丈夫)的上半身(以生角扮),雙手向后做反托(背瘋女)狀;二是女裝(瘋女)的一雙假腿腳,著彩褲、彩鞋,呈屈膝狀。旦角將假丈夫(上半身)扎于胸前,將一雙假手系往身后,成反背瘋女狀;將(瘋女)一雙假腳扎在身后,裝成啞丈夫背著妻子的完整造型。
表演時(shí),旦角模仿生角步法,被傅齋公喚上橋唱曲時(shí),兩腿下蹲、分開(kāi)八字,每走一步吃力沉重,當(dāng)一層一級(jí)吃力地登上橋面時(shí),啞丈夫喘氣,上下微動(dòng),旦角以手巾為啞丈夫擦汗,逼真可愛(ài)。在向傅齋公獻(xiàn)唱高腔《勸世文》時(shí),旦角要配合伴奏鑼鼓踩著鼓點(diǎn)走著生角舞步。其上身則以旦角輕盈柔媚的身段動(dòng)作配合唱詞舞蹈,與腳下生角步態(tài)形成鮮明對(duì)比。看上去是一男背一女,實(shí)則一女背一(假)男,這是岳西高腔繼承青陽(yáng)腔,青陽(yáng)腔又源自目連戲的劇目,而目連戲是吸收民間“一身二人”、“人偶共戲”的特技表演。黃梅戲曾廣為移植演出的《啞女告狀》,就采用了“啞背瘋”的表演形式,當(dāng)時(shí)我們只感到這種形式新鮮有趣,誰(shuí)知其來(lái)歷如此悠久。
岳西高腔還有特殊表演技藝,如“爬柱子”,運(yùn)用于《蟠桃會(huì)》(又稱《鬧桃園》)劇中的孫猴子“爬樹(shù)”。演出時(shí),選擇左臺(tái)柱為桃樹(shù),孫猴子通過(guò)“正爬”、“倒爬”、“烏龍纏柱”、“金雞獨(dú)立”、“四海深望”、“柱頂?shù)沽ⅰ薄ⅰ盀觚敃癖场薄ⅰ巴哟蜃薄ⅰ俺俄橈L(fēng)旗”等等系列高難動(dòng)作,用以表現(xiàn)孫猴子在仙桃樹(shù)上爬上爬下摘桃、吃桃、遠(yuǎn)望、嬉戲、打睡等情節(jié),演員須扎實(shí)雜技(爬桿)基功,才能勝任。
岳西高腔舊時(shí)以唱文戲?yàn)橹鳎搴拥葢虬嗄苎莩霾簧傥鋺颍鋺虻恼惺捷^簡(jiǎn)練、粗獷。從留下的名目看得出其固定套路還真不少。比如,開(kāi)打的擋頭有:點(diǎn)陣、合陣、擺陣、接陣、對(duì)陣、打團(tuán)臺(tái)、打圍臺(tái)、打撥手、打扯拐、打三角、雙過(guò)場(chǎng)、打四門(mén)等;把子有:插槍三整(陣)、打三槍、打扯槍、打翻槍、拖槍、丟槍(出手)、壓槍、架槍、劈槍、挑槍、打單槍、打雙槍等;身段有:起霸、洗馬、大身膀、伏虎式、騎馬式、垮虎(又名掛虎)等;拳腳有:分拳、搪頭拳、護(hù)腰拳、托天掌、掃堂腿、飛腿等。這些身段、把子、擋頭,或是由師輩傳下或吸收民間武術(shù)加之變革。
劇目中的武打套路,古高腔抄本的“科介”都有記載:如《扈家莊》劇中,梁山寨與莊卒的對(duì)陣,科介有“旦上,殺介,凈敗下,付凈接陣,殺介,付凈敗下,旦追下,兩將同上”;“殺介、凈敗下。付凈上,殺介,付凈敗下,旦退下,四將合退下”;“付凈、凈同上,殺介,二凈又上,‘打圍臺(tái)’,旦退下,凈追下”;“眾復(fù)上,‘打撥手’捉旦,下”等武戲套路提示。
在《黃天蕩》劇中,表現(xiàn)宋、金兩軍對(duì)壘時(shí)的“科介”,有“大殺介,‘雙過(guò)場(chǎng)’,‘插槍三整’,‘打三槍’,‘打掛虎’再‘打丟槍’, 再打‘撕馬尾’,凈敗下,生追下”;“凈上、生追下,‘雙過(guò)場(chǎng)’,‘打三槍’,再‘打扯槍’,‘打翻槍’, ‘打撕馬尾’,四將齊上,‘架槍’,生敗下,凈追下”等提示。
《大度》劇中有關(guān)九尾仙姑與天兵天將的開(kāi)打“科介”:“兩邊雙上,亮兵。‘打三槍’,‘插槍三整’,‘垮虎丟槍’,‘司馬尾’,花臉敗下。四將與眾開(kāi)打,三槍,四將敗下。花上,旦追上,‘打三槍’,‘打扯搶’,‘翻槍’,‘司馬尾’,花敗下。四將雙上,眾妹妹打,四將敗下。花、將同上”。這些都是十分珍貴的“舞臺(tái)腳本”,是明清時(shí)代舞臺(tái)表演的實(shí)況記錄信息。
岳西高腔是首批國(guó)家級(jí)“非遺”,高腔前輩創(chuàng)造了豐富的表演藝術(shù),作為“非遺”保護(hù)單位的一員,我們必須忠實(shí)保護(hù),還要活態(tài)傳承。在傳承活動(dòng)中還要直面現(xiàn)實(shí),如何做到既要讓今天的觀眾能欣賞到高腔古韻,還能使觀眾真心喜歡上古老的戲曲藝術(shù),這也是戲曲界同仁面臨的大課題。
岳西高腔傳承中心在《龍女小度》復(fù)排工作中,將岳西高腔“場(chǎng)上”、“場(chǎng)下”兩種形式和圍鼓坐唱、舞臺(tái)表演兩種表演形態(tài)融為一處。既突出其“唱幫打”一體的藝術(shù)特色,又彰顯角色行當(dāng)“四功五法”戲曲程式表演的魅力。臺(tái)上不設(shè)劇情場(chǎng)景和表演支點(diǎn),不置固定道具,打擊樂(lè)和幫腔人員(14人)全部登臺(tái);呈八字形坐(或站)于臺(tái)中后部,幫打人員也化妝并穿裝飾性服飾。舞臺(tái)表演區(qū)由劇中主角龍女和金喬覺(jué)(小旦小生)以戲曲行當(dāng)妝扮,按劇情充分運(yùn)用“四功五法”的戲曲程式表演,甚至有“探海”、“滾叉”等大幅動(dòng)作。這種突出了“唱、幫、打”一體的高腔藝術(shù)特征又彰顯“四功五法”藝術(shù)魅力的表演,營(yíng)造出古色古香、鑼鼓喧鬧的高腔藝術(shù)意境,別具一格,在城鄉(xiāng)演出均受到歡迎。2004年在安徽省小戲調(diào)演中獲演出、音樂(lè)、表演三個(gè)獎(jiǎng)項(xiàng);2018年在江蘇“昆山百戲”展演中,上海戲劇學(xué)院一位老教授率博士生觀劇后,大加贊賞,認(rèn)為有繼承有創(chuàng)新,移步不換形,這路子值得肯定。
《龍女小度》的成功當(dāng)然并不代表岳西高腔表演僅此一條路。岳西高腔有著雄厚的藝術(shù)資源,且攜帶有明清時(shí)期的藝術(shù)基因,站在這“巨人肩上”,岳西高腔將在今后的藝術(shù)實(shí)踐中做出更多的嘗試,奉獻(xiàn)更多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