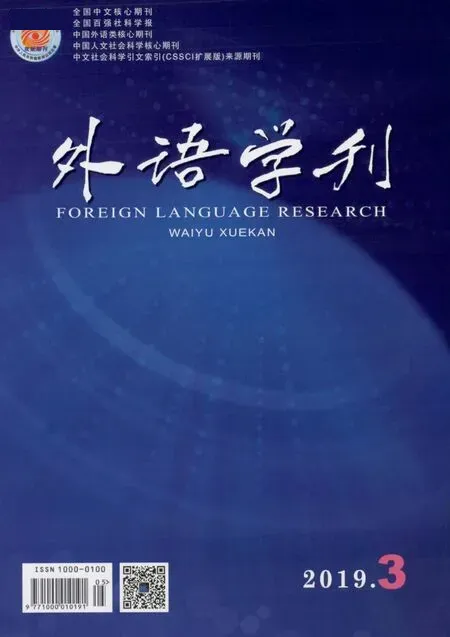雙語者心理詞匯語義表征的多視角研究*
黎 明
(西南交通大學,成都 610031/四川大學,成都 610065)
提 要:限于實驗方法本身的原因,僅從測量學視角研究雙語者心理詞匯的語義表征,目前尚無法得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結論。為此,本文從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言語產生和心理詞匯語義信息的存儲3 個視角研究雙語者心理詞匯的語義表征,通過對概念思維的純意義—概念、命題操作過程和言語產生3 層次等理論的分析得出:人類只有一套意義系統。通過對特定言語事實的分析推出:心理詞匯的語義信息不是固著在詞條之下,而是單獨存儲于人的認知系統。上述視角是從不同側面研究同一個問題,但所得結論并不相互矛盾。
1 引言
研究雙語者心理詞匯的語義表征模式有助于了解大腦的語言功能,考察語言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探索語言、思維及行為的本質。上世紀50年代起,國內外學者從測量學視角對雙語者心理詞匯的語義表征、詞匯通達機制和大腦皮層表征模式進行過大量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構建出眾多理論模型。但迄今為止,研究結論仍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Kroll et al.2012,Ma et al.2017)。本文將首先討論測量學視角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然后從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言語產生和語義信息的存儲這3 個視角進一步研究雙語者心理詞匯的語義表征。
2 測量學視角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
雙語者心理詞匯語義表征測量學視角的研究包括行為學和神經學測量兩類。前者的測試任務多基于詞匯加工,常用技術手段為視覺刺激呈現,測量反應時和準確率等指標;后者的測試任務多基于句子加工,常用技術手段有事件相關電位(ERP)和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測量 ERP 成分和神經元活動所引發的血液動力的改變(金曉兵2012)。測量學視角的研究結論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各測量方法本身都有局限性。
從上世紀80年代起,雙語者心理詞匯語義表征的行為學測量主要采用各種不同范式的啟動實驗。根據啟動刺激和目標刺激的呈現方式和時間間隔長短,可將啟動實驗分為長時重復啟動和短時快速啟動兩類。長時重復啟動范式包括一個學習階段和一個測驗階段,主要采用范疇判斷和真假詞判斷任務。如果測驗階段對學習階段呈現的詞的翻譯對等詞反應更快、更準,與未學詞存在顯著差異,就說明這些詞在學習階段得到激活,出現翻譯啟動效應,可推斷兩種語言的心理詞匯共同存儲;反之,則是獨立存儲。目前,該范式已成為國內雙語詞匯表征研究最普遍采用的行為學測量方法之一(黎明 2018),但 Kessler 和 Moscovitch發現,額外的加工策略會影響長時重復啟動效應的產生(Kessler,Moscovitch 2013)。
短時快速啟動范式不分學習與測試階段,啟動詞和目標詞連續呈現。SOA 為0 至數秒,長短不等,主要采用翻譯識別、語義歸類和真假詞判斷任務(Ma et al.2017)。在短時快速啟動范式的翻譯識別實驗中,被試必須完全看清楚前詞,提取前詞的語義,因此前詞開始呈現到后詞開始呈現的時間一般長達750-800ms.這意味著被試理論上至少有時間將一部分前詞在目標詞(后詞)呈現之前翻譯成目標語言,以便目標詞呈現后更快做出判斷,所以該范式理論上無法避免被試采用翻譯加工策略。為了最大限度減少翻譯策略效應,并保證被試有足夠時間識別前詞,Ma 等(2017)的實驗將前詞開始呈現到后詞開始呈現的時間縮短至300ms.但這里有一個悖論,如果時間太短,被試無法準確識別前詞;如果被試能準確識別前詞,就可能實施翻譯策略。因此,翻譯識別任務范式有缺陷。
現有短時快速啟動范式的語義歸類和真假詞判斷實驗大多為只采用一個SOA 的單點測試法。黎明和蒲茂華認為,在該測試法中,如果SOA 太短,啟動詞無法有效激活目標詞;如果SOA 太長,實驗無法排除翻譯等有意識的策略加工效應;如果SOA 足夠長,且能排除有意識的策略加工效應,但假如啟動詞和目標詞語義相關度不高,實驗仍無法獲得跨語言的語義啟動效應(黎明蒲茂華2014)。因此,SOA 單點測試法有明顯缺陷。
長時重復啟動實驗和短時快速啟動的翻譯識別實驗方法無法從理論上排除翻譯等有意識的策略加工效應,且不易通過改進實驗設計來消除這兩類實驗方法本身固有的缺陷。SOA 單點測試法則可以改進為SOA 多點測試法以消除設計缺陷。現有研究認為當SOA 不大于200ms 時,啟動實驗可最大限度地排除策略加工效應。因此可以在0-200ms 這一區間,選擇多個 SOA 點,如50、100、150 和 200ms 這 4 個點。只要能在這 4 個中的任何一個SOA 條件下發現啟動效應,就表明啟動詞能促進目標詞的認知加工。黎明和蒲茂華(同上)的SOA 多點測試研究是一次成功的嘗試,但所有啟動行為實驗,當然也包括SOA 多點測試法都共同面臨“反應時問題”。啟動行為實驗的主要分析依據是反應時,準確的實驗結論取決于真實的反應時,但實驗所測定的反應時間既包括被試根據心理詞匯的詞匯或語義信息,準確識別、判斷目標刺激的時間(如判斷目標詞是否是真詞,屬于哪一類語義范疇,前詞和后詞是否是翻譯對等詞等),也包括被試實施判斷的時間,即大腦準確判斷后發出指令,被試接收指令后通過實施某一具體操作完成判斷任務。因此,實驗所測定的反應時不都是被試純粹的反應時(趙翠蓮2012:40)。同時,由于實驗儀器的靈敏度不同及被試的實驗操作熟練程度不同,所以實驗過程存在較多不穩定因素,這些都會影響被試的反應時間。此外,“反應時(只)是體現言語加工綜合結果的單維指標”(張文鵬張茜2007:51)。“以正確率或反應時為因變量,這種以結果來推測過程的研究范式往往很難適應語言加工的高速整合特點。”(王沛蔡李平2010:283)
fMRI 和ERP 技術為雙語詞匯表征提供更為直接的研究方法,但fMRI 時間分辨率差,無法對詞匯及語義加工的心理過程進行連續測量(同上);難以確定皮層的活動到底是激活加工還是抑制加工,難以區別詞匯刺激的詞名層和概念層(張積家劉麗虹2007:313)。fMRI 能定位大腦詞匯加工激活的腦區,但定位不等于解釋。腦區分離,雙語仍可能相互作用;腦區重疊,雙語加工仍可能獨立進行(van Heuven,Dijkstra 2010:106)。采用ERP 技術研究雙語心理詞匯的認知加工過程可深化人們對語言加工腦機制的認識,不同ERP 成分為揭示不同過程和不同階段的認知加工提供具體指標,但對各腦電成分所反映的認知加工過程學界尚未達成一致認識。如有研究發現N170、N200、N250、N400 和 P200 都可以反映大腦詞匯認知的字形、語音和語義加工過程(黎明2018)。由于對反映雙語心理詞匯認知加工的主要腦電成分的心理功能尚存較大爭議,所以ERP 實驗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不言而喻。此外,在神經水平與意識水平之間,可能有一個巨大的鴻溝,因為經驗與對經驗的觀察不是一回事。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發現,限于實驗方法本身的原因,僅從測量學視角研究雙語詞匯的語義表征,目前尚無法得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研究結論。本文嘗試從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言語產生和心理詞匯語義信息的存儲3 個視角,對雙語者心理詞匯的語義表征模式做進一步研究。
3 語言與思維關系問題的研究
人在運用語言表達思維并完成交際之前,借以思維的媒介是什么? 福多的思想語假說(Fodor 1975)認為,人用思想語思考是天生的內在能力。思想語的實質是意義表征,即概念和命題的心理表征。心理表征發生在類似自然語言的表征系統內,由詞和句子組成,具有線性邏輯。其詞匯是全人類共有、獨特的思想語詞匯,語法結構比自然語言更簡單,信息更豐富;其對外部世界整體、直接表征,運作方式類似計算機的計算,計算過程本身不牽涉意義。福多的思想語假說在認知科學中得到廣泛認可,但也招致哲學、心理學、語言學界的質疑和批評。如 Jackendoff(2002)認為,語義/概念并非整體、直接表征外部世界,而是由概念元生成。概念元是天生的、不應再分割的原初概念。不少學者認為,人能用自然語言進行思維(黎明2018)。
現代人類思維的主要形態是概念思維,概念思維的媒介是否是福多式思想語? 維果茨基、李恒威和徐盛桓等論述過從概念思維到思維的言語表達可能經歷的過程。維果茨基認為,思維“首先是在內部言語中,然后在詞義中,最后在言語中”(維果茨基 1997:166)。李恒威等(2008)認為,思維起源于一個模糊的整體感受性語義。徐盛桓(2010)將人類思維分為語言前思維和語言思維兩個階段。語言前思維階段的意象思維生成內容思維,即類似于論元結構形式的主謂意義內容。意義內容進一步抽象為概念,再將語言承載的概念嵌入適當句式,思維成為可理解的語言表征,即語言思維。根據以上論述,概念思維可能經歷3 個階段:(1)思維主體獲得模糊的整體感受性純意義;(2)思維主體獲得概念和命題的心理表征;(3)精細化概念內容(定義)并以語言予以指稱(參見圖1)。

圖1 概念思維的流程
階段(1)是思維的源起,即思維起源于一個整體感受性意義:思維主體進行的思維活動是無需語詞的純意義操作。沒有語言參與,不能借助語詞概念對思維的操作對象(意義)進行有效切分,這種思維操作具有純意義性、整體感受性和模糊性特征。階段(2)是思維獨立于概念語詞外殼的純概念和命題(即概念關系)操作,思維操作不涉及心理詞匯的詞名表征。階段(2)的概念和命題思維操作有3 個重要特征。
其一,概念和命題的心理表征以共時的、聚合的、網絡的方式,而非以福多式思想語句的方式存在。概念和命題的所有信息同時表征,無語句線性邏輯。思想(概念思維的結果)是關于概念及命題的核心信息與相關信息的整合,是人腦中被語言刺激激活的信息成分以及這些信息成分之間的復雜聯系,即其聚合性相關關系的同時性合成。此階段的思想無語法形式,瑣細龐雜,是展開思想、形成話語的必經階段(官忠明 劉利民2000,徐盛桓 2010)。
其二,概念思維具有個體特異性。劉利民認為,概念語詞的語義涉及主客觀兩方面及主客觀互動,是多維度的、復雜的(劉利民2008:15)。概念語詞的核心語義為所有人共享,否則就不具有可交流性,但其語義不是單一核心定義元素的集合,而是這個集合與文化特異性、個體指向性和時空動態性構成的多維認知圖式。概念語詞語義的個體特異性表明概念的心理表征必然是個體特異的。盡管核心信息表征相同,但由于人與人之間的知識圖式、經歷體驗圖式等信息建構差異,概念相關信息的表征必然因人而異。概念和命題心理表征的個體特異性決定概念思維必然是個體特異的,所以,即使存在概念“思想語”,它既不具備語言的線性邏輯結構,也非人人共享。
其三,概念由概念元生成,無窮的概念和概念元都是思維主體后天習得的。Jackendoff(2002)的概念語義學對意義的分解與生成、意義與概念空間結構的論述能合理解釋概念思維的普遍性和個性差異,本文認同Jackendoff 的概念生成觀。概念元生成簡單概念,簡單概念組合生成復雜概念。但概念元并非天賦,而是思維主體后天習得的。新概念元和新概念伴隨新生事物不斷涌現,因而概念元和概念都是無窮的。概念和命題顯然也都是思維主體后天習得的,或者直接就是思維主體的思維產物。與階段(2)的概念思維不同,如果階段(1)不需要語言和概念的純意義操作性思維存在思想語,它更可能是天賦的。所以,如果存在概念思想語,它可能既有天賦的,也有后天習得的成分。
上述特征意味著:意義本身是動態的,并不一定涉及語言。
階段(3)是概念思維的語言表達階段,即搜索、提取或創造概念語詞和句式的語言表達思維階段。從概念思維到概念思維的語言表達要經歷兩個轉變。一是將概念和命題的心理表征轉化為自然語言形態的概念語詞,或直接創造新的概念語詞,當然也可能陷入“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尷尬境地。二是將概念語詞和命題(即概念關系)嵌入適當的句法表達式,或創造新句法表達式。概念思維外化為語言表達式是保留意義,逐漸形成、加強、固化語言格式的過程。階段(3)中思維的內容即思想經言語表達更加清晰,這種語言化的思想可多次重復階段(2)和階段(3),即思維主體“反復思考”,以獲得更加清晰的思想,這是概念思維的階段間反復、循環特征。階段(2)和階段(3)自身也都可以“反復思考”“深思熟慮”。階段(2)的“反復思考”可以使概念及命題的核心信息與相關信息更豐富,或相對更清晰。階段(3)的“深思熟慮”可以使思想表達更準確,這是概念思維的階段內反復、循環特征。從流程看,自然語言并不是概念思維的工具,因為語詞的意義不等于概念,思維的加工對象和產物都是思想,思想是關于概念及概念間關系的心理表征。語言為思維提供材料,調節思維加工的內容,促進思維發展,進而影響思維產物。因此,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理解思想內容和表達的工具,是思維與客觀外界聯系的中介,但不是思維的工具。
從上文分析可以得出:概念思維可能經歷的初期階段是無需語詞的純意義操作,思維結果產生模糊的整體感受性意義。核心階段是對作為心理表征的概念和命題的意義操作。此時,思維獨立于概念的語詞外殼,依據概念本身運作,不需要一套額外的符號系統來表示概念的心理表征。事實上,也不可能提供一套人人都相同的概念心理表征符號,因為概念心理表征具有個體特異性。如果要表達思想,則須要提取或創造概念的語詞外殼和句式,形成言語表達式,這就是概念思維的純意義—概念及命題心理操作過程。概念是意義的單位,是思維的基本元素(材料)。概念思維的媒介既不是福多式思想語,也不是自然語言。人可掌握多門自然語言,有多套心理詞匯,但只有一套意義系統。概念思維始終依據這唯一的一套意義系統進行各種心理操作,并用不同的自然語言表達思想。盡管概念思維的這一純意義—概念及命題假說性心理過程仍有待哲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相關研究的確證,但很多研究都表明,概念思維的操作是獨立于語詞外殼的概念及命題的心理表征,操作的是意義。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心理詞匯的詞匯表征和語義(或意義)表征是分離的,雙語者心理詞匯的語義表征共享。
4 言語產生問題的研究
言語產生是從組織交流意圖,激活概念,提取詞義、句法和語音信息,到控制發音器官發出聲音的過程,即人們運用語言表達思想的心理過程(李利等2006:648)。言語產生主要采用言語錯誤分析和命名的時間分析兩類研究方法,用以了解言語產生的句法計劃和詞匯提取特點,揭示語言的表征方式和言語產生從獲得概念,激活相應的語義、語音信息,到發音的全過程(周曉林等2001,張清芳 楊玉芳2003)。研究者一般將言語產生劃分為多個不同階段。桂詩春認為,言語產生大體經歷4 個階段:將意念轉換成待傳信息;把信息形成言語計劃;執行言語計劃;自我監察(桂詩春2000:483)。信息如何生成,意念從何而來,其變為詞語前以什么方式存在,這些問題仍有待學界繼續探索。在Levelt 的言語產生信息構成模型里,信息生成由話語概念啟動。言語生成首先產生交際意圖,然后決定要表達的信息。Levelt 將說話人的意圖作為執行言語計劃的開始。要成功實施言語行為,說話人必須首先對意圖進行編碼,這就涉及思想信息向言語計劃轉化,即制訂言語計劃(又稱信息編碼),包括“宏計劃”和“微計劃”。說話人通過宏計劃把交際意圖發展為一個個言語行為的內容;在微計劃里,說話人通過為每一言語行為的內容賦予信息結構、命題格式等方式,把每一個要表達的信息單位變成一個前言語信息。信息編碼輸出的前言語信息進入兩個編碼器:第一個是提取詞項的語法編碼器,第二個是語音編碼器。詞項的語法和語義特征即詞注(lem-mas)與其語音信息分開存儲和提取。語法編碼器產生表層結構,即恰當排列的詞注串。語音編碼器則接過句法框架生成語音計劃(轉引自桂詩春2000:548-550)。Fromkin 的話語生成器模型把言語產生分為6 個階段:(1)意義生成階段:生成要傳遞的意義,即選定話語的意義;(2)信息映現階段:對信息建立句子結構框架;(3)生成語調輪廓;(4)從心理詞典中選擇詞語;(5)規定語音;(6)生成言語的肌動命令,把話語體現為語音形式(Fromkin 1993)。Ferreira 提出,要把無序的思想、觀念通過有序的渠道表達出來,要將思想命題(即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系)線性化為言語結構,首先要把命題結構轉化為句法結構,再轉化為韻律結構,最后轉化為線性語音結構(Ferreira 1993)。
言語產生過程的關鍵是詞匯通達:將思維轉換成單詞表達,并進一步轉換為聲音。大量研究將詞匯通達分為詞匯提取和音韻編碼兩個階段(Schmitt et al.1999)。(1)語義激活和特定詞匯選擇:心理詞典中的語義表征被激活并擴散至中介的詞條水平,詞條具有語義和句法特點;(2)音韻編碼:詞條水平的激活進一步擴散至特定詞匯的音韻表征。詞匯通達理論有兩步交互激活模型和獨立兩階段模型。Dell 的“兩步交互激活模型”認為,從語義到語音水平經歷兩個步驟:語義特征節點的激活首先擴散至相應的單詞或詞條節點,然后再擴散至音素節點(Dell 1986)。激活擴散是雙向的,既可從詞匯層向語音層擴散,也可從語音層反饋至詞匯層。激活程度最高的即成為目標項,僅針對目標項制定發音計劃。目標項的語義和語音激活在時間上有重疊:語音激活稍晚于語義激活,但在言語產生的早期和晚期階段同時存在語義和語音激活。早期階段,目標項的語義激活緩慢增加直到音韻編碼開始后減弱,但晚期語音激活的逆向擴散可將激活傳遞至語義特征,引起語義激活反彈增加。目標項的語音編碼從早期階段一直增加直到執行發音計劃。Levelt 等的獨立兩階段模型認為,詞匯提取和音韻編碼階段分離,不相互重疊(Levelt et al.1999)。概念激活之后,目標項和語義相關項從輸入的概念處接受語義激活,經歷詞匯激活和選擇階段后只有目標項“幸存”,音韻編碼階段也只有目標項獲得語音激活。因此,早期階段只有目標項和語義相關項的語義激活,晚期階段只有目標項的語音激活。語義和語音激活在時間上沒有重疊(張清芳楊玉芳2003:6-11)。盡管兩類模型在各種激活的時間進程和各階段是否交互作用兩個問題上分歧嚴重,但它們都認為主要表征水平是概念層、詞條、音韻層或詞形層(phonological or word-form stratum),都認為概念激活是首要的。無論如何,要先有意義,然后才談得上詞語通達。這說明,人必須首先經過意義操作才能產生言語。
盡管言語產生的階段劃分存在分歧,但現有研究一般都將言語產生過程分為3 個層次(鄒麗娟丁國盛2014:435)。第一層是形成表達意圖和概念:即講話者要明確用言語表達的意義;第二層是言語組織:把要表達的意圖/概念轉換為語言形式,即為表達的意義選擇適當的詞匯,并建立詞匯的語義語法結構和發音結構;第三層是發音階段:講話者利用發音器官表達出所選擇的詞匯。第二層的言語組織包括詞匯生成和語法編碼兩部分。語法編碼指句子的選詞和排序,即根據詞匯的意義和語法性質選擇恰當的詞匯,并產生話語的句法框架。詞匯生成可細分為概念準備、詞條選擇、音位編碼和語音編碼等部分(周曉林等2001:263)。概念準備指大腦把思想、觀點等轉化成概念的過程。說話者的待傳意義由詞匯概念來表達,人在準備表達某個思想時,需要從大量相關信息中挑選最恰當的詞匯概念。因此,概念準備就是說話者所要表達的意義與心理詞典詞匯概念之間的匹配,這個概念必須對應心理詞典中的詞或詞素。如表達“有四條腿、嗅覺靈敏、會汪汪叫的動物”最簡潔的是“狗”(同上:263)。詞條選擇即對特定的詞或詞匯的選擇。對于要表達的意圖,可能有多個相關詞匯被激活,詞條選擇即是選擇目標詞。
從言語產生的3 層次、分階段、線性化(矢量化)理論可以推知:意義先于言語,言語產生首先要確立說話的意圖和想用言語表達的意義。此時說話人已經有要表達的意義,需要線性化為言語結構的思想命題已經存在。作為心理表征的意義內容可能是無序的、多維度的、動態的和個體特異的。意義內容要線性化為言語結構須要制定言語計劃:針對特定對象和特定場合,決定哪些需要說,怎么說,之后是詞匯通達/提取,即為所表達的意義選擇適當的詞匯,建立詞匯的語義語法結構和發音結構。這期間首先經歷概念準備,然后是詞匯選擇,其實質是說話人用相應的詞匯表達待傳意義。因此,概念準備就是說話人的待傳意義匹配其心理詞典的詞匯概念,之后是選擇目標詞。此外,現有研究認為,雙語言語產生在提取一種語言的詞匯時,雙語者兩種語言的詞匯都會被語義系統激活,即語義系統能同時激活雙語者的兩個心理詞庫(Costa et al.2000,Colome 2001)。以上論述表明,言語表達始于交流的動機和意向,說話的意圖和想表達的意義,即作為思想的意義內容要先抽象成為概念,然后再尋找已經存在于大腦的以自然語言為載體的概念語詞外殼。因此,不管說話人能用多少種不同的自然語言表達思想,卻始終只有一套意義系統。意義和語言形式是分離的,意義是抽象的、超語言的,不具有語言特異性。
5 心理詞典中語義信息存儲方式的研究
雙語者心理詞匯的語義是獨立還是共同表征,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持獨立表征觀的學者認為,心理詞典的存儲方式類似普通詞典,即每個單獨的詞條下都儲存著語音、句法、形態和語義等信息(The Meaning-Under-Entry Hypothesis);持共同表征觀的學者認為,心理詞匯的語義并非與其語音等信息一起存儲,而是單獨存儲在大腦認知系統。如果前者正確,雙語者兩部心理詞典之間的交流或翻譯就需要心理翻譯詞典。假設漢—英雙語者兩部心理詞典都存儲各自的詞義,即漢語詞的詞義存儲在漢語詞條下,英語詞的詞義存儲在英語詞條下,當他們交替使用漢英雙語時,為了理解,就需要一本翻譯詞典把英漢兩種語詞的意義連接起來。如用法語詞homme 把man和“人”連接起來;用法語詞aller 把go 和“去”連接起來。問題是任何兩種語言的完全等值詞都極少,絕大多數語詞的意義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一詞多義、一義多形是自然語言的基本特征(劉利民 2000:122)。
A1.It's important for you to be here punctually.
A2.Es ist wichtig,dass Du hier punctlich bist.
B1.You are very important here.
B2.Du bist sehr bedeutend hier.
C1.The sentence is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C2.Der Satz ist interesant und bedeutend.
A1 中的 important 譯成德語用 wichtig(A2);B1中的important 譯成德語只能用 bedeutend(B2)。德語詞bedeutend 又對應英語詞meaningful,所以C1的meaningful 譯成德語就是 C2 的 bedeutend.因此有:
(1)Fimportant={A、B};
(2)Fwichtig={A};
(3)Fbedeutend={ B、C};
(4)Fmeaningful={C}.
也就是說,important 有含義A 和B,wichtig 只有含義A,bedeutend 有含義 B 和C,而 meaningful只有含義C.因此,要構造一部翻譯詞典來溝通兩種不同語言的詞,由于語言的復雜性,這部翻譯詞典將因為語詞數量太過巨大而無法完成,也將因為耗費大腦太多存儲空間和認知資源而不具有存在可能性。可見,如果每種語言都形成一個封閉系統,形式轉換(翻譯)的心理操作將非常復雜,甚至不可想象。因此,邏輯地講,意義不可能固著在詞條下,只能將其單獨置于大腦認知系統里(劉利民 2000:123)。兩部心理詞典啟動認知系統的同一個意義系統,這樣的心理詞典才更有效。思維僅操作概念即意義系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經濟的,人類可用不同語言表達相同思想。只有承認意義的抽象本質和中介功能,才能理解二語學習和雙語形式轉換的可能性。形、義連接的多元性并不意味不同語言有不同概念體系,而是說不同語言對同一概念體系中概念單元的標識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漢語的“好”和英語的good 所標識的概念數量就不一樣,前者可標識與“不錯的、愜意的、令人滿意的、高尚的”有關的意義,而后者對這些意義可能要分別標識(李榮寶2002:71)。
另一方面,The Meaning-Under-Entry Hypothesis 難以解釋以下語言現象。第一是詞匯的創造性現象。如果語義固著在詞條下,接受一個詞就自動接納其固著的語義,因此舊詞將不可能增添任何新意,詞匯的創造性使用將無法解釋。比如,“花生米”本指可食用的果實,但卻可以將3 個字拆開制造幽默:“米”的媽媽姓“花”,因為“花”生“米”。如果“花生米”的意義已經固定在該詞條下,就無法將其拆開。喬姆斯基認為,小孩是語言天才,因為小孩使用語言非常有創造性。如一小孩洗澡前脫光衣服后說:I am barefoot all over! 另一小孩見有人嘔吐說:The man eat things out! 如果意義已經固定在barefoot 和eat 詞條下,小孩就不可能這樣創造性地使用它們。如果意義固著在詞條下,語言就會失去創造力,失去活力。
第二是話到嘴邊現象。一位教授在向學生推薦閱讀書目時說:I can visualize that book,but the name escapes me.教授能想象書的樣子,卻不記得書名,此乃知曉意義,卻忘記語詞(得意忘言)。也可能知道語詞,卻不清楚語義(知其言,卻不知其意)。比如知道“美”這個語詞,卻講不清楚什么是“美”,這都表明意義和語詞是分離的。如果每一個詞條下都有意義,意義和詞匹配在一起,“得意忘言”就無法想象,就不可能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此外,Fromkin 從言語失誤數據分析得出,心理詞匯是從語義和語音兩個方面組織起來的(Fromkin 1993)。李榮寶從3 個方面論證語義是語言表征的抽象實體(李榮寶2002:63-66)。第一,從發生論角度看,“意義”和語言的發展不同步,語言的形式與意義并非不可分割,詞的形態和概念等內容并非整體表征。第二,“意義”不是掌握自然語言之人的專利,聾啞人也能理解、表達“意義”。第三,不同語言具有不同句法結構,但語義的最高形式—命題則不因語言不同而異。既然語言的形態可以在不同層面整合為抽象的語義實體,就沒理由認為不同語言有不同語義表征。因此,語義是語言表征的抽象實體,語義系統是人對客觀世界認識的復合體。一個人所學語言越多,獲得的意義表達形式也越多,而不是更多的語義系統。語義是抽象的、超語言的,是單獨存儲在認知系統中,語義命題的超語言性也確保語言的可譯性。不同語言中因文化等原因引起的概念語詞缺失現象和形義連接的多元性使翻譯必須以語義為中介,而不是僅依據語詞形式層面的連接。
6 結束語
對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言語產生和心理詞匯語義信息存儲的研究表明,人類只有一套意義系統,心理詞匯的語義不可能固著在詞條下,而是單獨存儲在人的認知系統中。測量學視角的絕大多數研究也表明,雙語者的心理詞匯共享語義表征。如果雙語者不同心理詞匯的語義表征是分開單獨存儲的,就可能推翻上述4 個領域的幾乎所有研究成果。本文認為,雙語者不管有幾套心理詞匯,他們的所有心理詞匯都共享語義表征,共享同一套意義系統。而且即使是初學者,他們的二語、三語……N 語詞匯表征都能直接通達共享語義。語言間的一詞多義和一義多形決定任何語言的詞匯無法僅借助于其他語言的詞匯表征而間接通達共享語義表征。各語言詞匯表征和共享語義的連接強度主要受語言熟悉度調節,即語言越熟悉,連接強度越大。雙語及多語詞名層的連接模式及連接強度則主要受語言熟悉度、語言之間的相似性、學習媒介語和語言使用頻率等因素影響,并呈現出復雜多變的動態連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