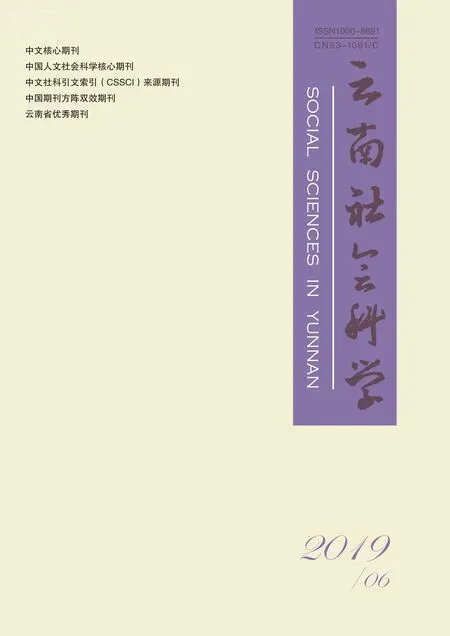“貧困女性化”的形成與治理
仲 超
一、問題的提出
從生物學角度看,兩性生理構造存在鮮明的差異,女性生理機能較男性脆弱。先天的生物弱勢性不可避免地為女性帶來了后天的社會弱勢性,“貧困女性化”就是其表現之一。
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將“女性與貧困”置于12個重大關切領域的首位,并嚴正指出,全世界有10億多人處于貧困狀態,其中大多數為女性,且主要分布在發展中國家。①[美]瓦倫丁·M.莫格哈登:《貧困女性化?——有關概念和趨勢的筆記》,馬元曦主編:《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31-62頁。同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進一步強調,貧困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在世界貧困人口中,女性占70%,與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容易陷入貧困、貧困程度更嚴重以及擺脫貧困更困難的特點。②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IFAD)也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農村貧困女性的增長率為48%,男性則為30%,女性貧困發生率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男性。③[美]瓦倫丁·M.莫格哈登:《貧困女性化?——有關概念和趨勢的筆記》,馬元曦主編:《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第31-62頁。在中國,“貧困女性化”趨勢同樣較為明顯,《中國農村貧困檢測報告2011》顯示,2010年中國女性貧困發生率為9.8%,比男性高出0.4個百分點,女性貧困者占貧困人口的比例亦超過了50%。④寧滿秀、荊彩龍:《貧困女性化內涵、成因及其政策思考》,《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年第6期。顯然,“貧困女性化”已經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命題。
學術界對“貧困女性化”的關注源于20世紀后半葉出現在美國的女戶主家庭貧困問題。1978年,美國社會學家戴安娜·皮爾斯(Diana Pearce)在研究20世紀50-70年代中期美國貧困問題的過程中發現,貧困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即貧困家庭中女戶主家庭和貧困人口中女性所占比重均不斷增加。①Diana Pearce,“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Women,Work,and Welfare,” Urban and Social Change Review,vol.11,no.1,1978,pp.28-36.皮爾斯將這一現象稱之為“貧困女性化”,由此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繼皮爾斯之后,學術界對“貧困女性化”展開了進一步的討論,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第一,“貧困女性化”具有多樣性和異質性。一方面,“貧困女性化”表現為多維貧困,不僅體現在收入和物質層面,還體現在資產、健康、教育、心理和精神等多個層面。②Deborah S.DeGraff and Richard E.Bilsborrow,“Female-Headed Households and Family Welfare in Rural Ecuador,”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6,no.4,1993,pp.317-336; Johanne Langlois and Daniel Fortin,“Single-Parent Mothers,Poverty and Mental Health: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Sante Mentale Au Quebec,vol.19,no.1,1994,pp.157-173; Kirang Kim,Mi Kyung Kim,Young-Jeon Shin and Sang Sun Lee,“Factors Related to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Public Health Nutrition,vol.14,no.6,2011,pp.1080-1087; Sylvia Chant,“Exploring the‘Feminisation of Poverty’ in Relation to Women’s Work and Home-Based Enterprise in Slums of the Global Sout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vol.6,no.3,2014,pp.296-316.另一方面,“貧困女性化”在年齡、婚姻狀態和地域等層面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差異,老年女性、單身女性和農村女性相對更容易陷入貧困。③Evy Gunnarsson,“The Vulnerable Life Course: Poverty and Social Assistance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Women,” Ageing and Society,vol.22,no.6,2002,pp.709-728; Pauline Stoltz,“Single Mothers and the Dilemmas of Universal Social Policie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vol.26,no.4,1997,pp.425-443; R.S.Katapa,“A Comparison of Female and 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Tanzania and Povert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vol.38,no.3,2006,pp.327-339; Ye′le′ Maweki Batana,“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mong Women in Sub-Saharan Afric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112,no.2,2013,pp.337-362.
第二,“貧困女性化”是多種結構性因素作用的結果。皮爾斯和大部分研究者都將家庭結構和市場參與視為“貧困女性化”的主導因素,認為女戶主家庭的快速增長和女性就業不足是導致貧困向女性傾斜的根源。④Diana Pearce,“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Women,Work,and Welfare,” pp.28-36; Jane Millar and Caroline Glendinning,“Gender and Povert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vol.18,no.3,1989,pp.363-381; Catherine Cross,“Women’s Households and Social Exclusion: A Look at the Urbanisation Dimension,” Agenda,vol.22,no.78,2008,pp.106-119; Gül?en Ger?il,“Küresel Boyutta Yoksulluk ve Kad?n Yoksullu?u,” Y?netim ve Ekonomi,vol.22,no.1,2015,pp.159-181.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強調,除了家庭結構和市場參與,家庭內部資源分配、公共政策、社會排斥等也是造成“貧困以女性面孔”出現的重要因素,“貧困女性化”是一個矛盾綜合體。⑤Janice Peterson,“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21,no.1,1987,pp.329-337;Jane Millar and Caroline Glendinning,“Gender and Poverty,” pp.363-381; C.Anne Broussard,Alfred L.Joseph and Marco Thompson,“Stressors and Coping Strategies Used by Single Mothers Living in Poverty,” Affilia,vol.27,no.2,2012,pp.190-204.
第三,“貧困女性化”治理的核心在于促進女性市場參與,同時多方施策。從既有文獻看,“貧困女性化”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消除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排斥,促進女性公平就業;⑥Deborah S.DeGraff and Richard E.Bilsborrow,“Female-Headed Households and Family Welfare in Rural Ecuador,”pp.317-336; Roni Strier,“Women,Poverty,and the Microenterprise Context and Discourse,” Gender,Work and Organization,vol.17,no.2,2010,pp.195-218; Gül?en Ger?il,“Küresel Boyutta Yoksulluk ve Kad?n Yoksullu?u,”pp.159-181.i二是提高公共政策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性別敏感性,在收入、資產、教育和金融等層面為女性群體提供更多的保障和幫扶;⑦Monique Cohen and Jennefer Sebstad,“Reducing Vulnerability: The Demand for Microinsur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17,no.3,2005,pp.397-474; Sara Horrell and Pramila Krishnan,“Poverty and Productivity in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Zimbabwe,”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43,no.8,2007,pp.1351-1380; Catherine Cross,“Women’s Households and Social Exclusion: A Look at the Urbanisation Dimension,” pp.106-119; Anahely Medrano,“CCTs for Female Heads of Households and Market Citizenship at State-Level in Mexico,” Social Policy & Society,vol.15,no.3,2016,pp.495-507.三是強化社會關懷和支持,通過社區互動和社會工作干預等方式為女性提供心理疏導和精神慰藉,激發其自信心和積極性,增強自我效能。①Jeffrey R.Kling,Jeffrey B.Liebman and Lawrence F.Katz,“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Neighborhood Effects,”Econometrica,vol.75,no.1,2007,pp.83-119; Marianne Daher and Ana María Haz,“Changing Meanings Through Art: A Systematization of a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with Chilean Women in Urban Poverty Situ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vol.47,no.3-4,2011,pp.322-334; Jean Francis East and Susan J.Roll,“Women,Poverty,and Trauma An Empowerment Practice Approach,” Social Work,vol.60,no.4,2015,pp.278-286.其中,促進女性市場參與是研究者們關注的焦點。
總體來看,現有研究對“貧困女性化”現象進行了較為全面和直觀的描述,從一個或多個維度分析和歸納了其形成原因,并基于不同的視角提出了治理策略,為人們認識和理解“貧困女性化”這一嶄新命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這些研究大多慣于孤立分析和靜態分析,疏于邏輯分析和歷史分析,因而存在局限性。現有研究雖然承認“貧困女性化”是一個復雜的矛盾綜合體,但卻并未對其內部結構和運行機理進行深入和系統的剖析,從而造成“貧困女性化”迄今仍然缺乏完整的理論框架,多種結構性因素之間的邏輯關聯及其形成的歷史脈絡均不甚明晰。理論框架的缺失又使得現有研究并未厘清家庭和市場的關系,單純強調市場的影響,從而忽視了從家庭維度審視生物性別差異和性別分工的基礎性建構作用,最終亦不可避免地導致對“貧困女性化”歸因的偏頗和應對的乏力。鑒于此,本文擬探索構建“資源分配-作用領域-歷史演進”的理論分析框架,以提煉“貧困女性化”的形成機理,并嘗試提出綜合聯動的治理策略。
二、理論分析框架構建
長期以來,人們對貧困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收入、資產等物質維度,貧困研究遵循較為單一的視角。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不斷意識到人類福祉的很多方面無法完全用物質來衡量,如教育、健康、精神、自由、安全等,貧困的概念亦開始被逐漸拓寬,由單一的物質維度向多維度轉變。②林閩鋼:《新歷史條件下“弱有所扶”:何以可能,何以可為?》,《理論探討》2018年第1期。然而,無論是傳統貧困視角下的物質缺乏,還是多維貧困視角下的基本權利、社會參與、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缺乏,從本質上看,都可以視為資源缺乏,而資源缺乏又根源于資源分配不平等。因此,資源分配是分析貧困的核心維度,“貧困女性化”亦不例外。資源分配具有多元性和復雜性。從內容上看,資源分配可以分為物質資源分配和精神資源分配。從環節上看,物質資源分配又可以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關于資源分配不平等(貧困)的解釋,學術界一直存在紛爭,尤其是結構解釋和文化解釋的對壘。③周怡:《貧困研究:結構解釋與文化解釋的對壘》,《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3期。結構論將貧困視為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一部分,認為貧困主要源于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對個體機會和資源獲取的制約。④孟照海:《教育扶貧政策的理論依據及實現條件——國際經驗與本土思考》,《教育研究》2016年第11期。文化論則認為,貧困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是一種自我維持的文化體系,⑤黃承偉、劉欣:《“十二五”時期我國反貧困理論研究述評》,《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源于貧困者自身形成的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即表現為好逸惡勞、不思進取、聽天由命的“貧困亞文化”。⑥鄭杭生、李迎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弱勢群體的社會救助》,《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由于這兩種解釋取向都存在較為片面和極端的局限性,當前貧困研究通常都將二者相結合。但“貧困女性化”研究重在解釋女性何以比男性貧困,而非何以貧困。從經驗研究看,女性貧困群體確實存在貧困文化,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形成貧困文化。因此,用文化論解釋“貧困女性化”較為不妥,可行的途徑是基于結構論考察資源分配中的性別差異。傳統的結構主義側重分析資源分配在市場、國家和社會三個領域中對貧困的建構作用,這種研究范式的分析單位是作為統一體的家庭。而“貧困女性化”的分析單位是男女兩性,家庭正是產生性別差異的核心領域。因此,除了市場、國家和社會,資源分配的作用領域還應擴展到家庭。在性別視角下,資源分配涉及多個領域和環節的互動,市場是資源分配的前端,國家和社會在資源分配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家庭則是資源分配的末端。
貧困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生物性別差異亦由來已久,但“貧困女性化”卻是一個在最近40年才出現的新概念。這表明,“貧困女性化”有著濃厚的時代色彩,正如馬塞洛·梅代羅斯(Marcelo Medeiros)和喬安娜·科斯塔(Joana Costa)所言:“貧困女性化是一個歷史概念,表現為兩性之間貧困差異的擴大化導致女性貧困發生率和貧困嚴重程度處于持續演變的狀態”①Marcelo Medeiros and Joana Costa,“Is There a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World Development,vol.36,no.1,2008,pp.115-127.。這種歷史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源分配所涉及的領域,二是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二者皆伴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而處于持續演進的狀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資源分配的作用領域、環節及其互動關系不同,各領域和環節作用于性別排斥和性別差異的條件也不同。因此,只有從歷史演進的視角出發,才能認識和理解“貧困女性化”形成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才能對其未來走向做出準確的判斷和預測。
基于此,本文構建了“貧困女性化”的理論分析框架,由資源分配、作用領域和歷史演進三角構成(見圖1)。其中,作用領域包括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

圖1 “貧困女性化”的理論分析框架
三、“貧困女性化”的形成機理
人類進化賦予了男女兩性不同的生理特征,且人類必須以婚姻和家庭為載體,通過勞動和生育來維持生存和繁衍。因此,基于生物性別差異的性別分工成為了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必然選擇。
起源于原始社會的性別分工屬于自然分工,男性負責狩獵和保衛家庭安全,女性負責生育和食物采集。在這一時期,資源的聚集與分配主要集中在家庭領域,且具有極高的整體性,性別差異并不明顯。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國家的形成,資源聚集與分配逐漸超越了家庭這一閉合領域,性別分工也隨之由自然分工向社會分工延伸。在社會分工中,男性扮演家庭經濟支持者的角色,主要負責勞動生產以及家庭外部事務;女性扮演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主要負責家庭內部事務。正如蓋爾·魯賓(Gayle Rubin)所言:“性別是既定的、生物的,而社會性別則是歷史過程的產物。女性生育屬于生物性別,而女性照顧家庭則屬于社會性別,是一種文化建構”②Gayle Rubin,“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Reiter,eds.,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5.。隨著社會分工的形成,資源分配的性別差異即社會性別差異亦隨之產生。但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資源分配并不具備構成顯著性別差異的條件。一方面,家庭資源仍然具有較高的整體性,分化程度比較低;另一方面,國家制度作用下的資源分配以及宗教等民間組織自發進行的慈善性質的資源分配規模和力度均較為有限,且以家庭為主要分配單位。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機器大生產和雇傭勞動制的出現使得市場成為了最核心的資源分配領域。同時,社會分工進一步擴大,在家庭與市場之間形成了性別隔離,男性活躍于市場,女性則受縛于家庭。此外,隨著以基于市場的社會保險為核心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與完善,國家亦開始干預和調節社會分配,成為資源分配的重要領域。至此,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等各個資源分配領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交織的性別差異,女性在物質資源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及精神資源的分配中均處于從屬地位。
首先,生物性別差異和性別分工造成女性在市場主導的初次分配中處于從屬地位。雖然基于生物性別差異的性別分工賦予女性的社會角色并非法律或制度所規定,但千百年的塑造已然固化了女性對這一角色的認同。在家庭這一非雇傭單位,女性從事的大量家庭照顧工作都屬于無償性質,無法享受對應的經濟權利,而家庭照顧責任的“女性化”又約束和分散了女性參與市場的時間和精力。①Jane Millar,“Gender,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Social Policy & Society,vol.2,no.3,2003,pp.181-188.同時,生物性別差異直接造成女性被視為先天弱勢群體,體能劣勢和難以規避的生育風險導致女性在求職、薪酬談判、晉升等諸多環節都可能受到市場的隱形排斥。女性即使能夠躋身勞動力市場,也大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和低端崗位,在工資待遇、工作穩定性、勞動權益保障等方面均與男性存在明顯的差距。市場是現代社會個人獲取收入的主要來源,女性在市場中遭受的排斥將直接導致其在物質資源的初次分配中處于從屬地位。
其次,初次分配中的從屬地位將造成女性在家庭分配和國家主導的再分配中處于從屬地位。一方面,家庭是人類社會生產、資源分配和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女性在經濟上的劣勢將導致其在家庭決策和資源分配中處于劣勢。通常而言,扮演家庭經濟支持者的男性將當仁不讓地成為家庭決策的主導者和資源分配的優先者,經濟、教育、社會網絡等資源也隨之向男性傾斜,以實現家庭的整體需求。然而,家庭整體需求的實現通常以掩蓋和犧牲女性的個體需求為代價。女性不僅從事的家務勞動具有無償性,從其他家庭成員手中獲得的“勞動報酬”也具有隨意性。②Martha Macdonald,“Gender and Social Security Policy: Pitfalls and Possibilities,” Feminist Economics,vol.4,no.1,1998,pp.1-25.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享受社會保障等國家提供的職業保障和補償的勞動者主體資格的限制,女性在市場中的劣勢將導致其在收入再分配中處于劣勢。基于職業勞動的社會保障是實現國民收入再分配和貧困治理的重要手段,但面對市場和社會中日益鮮明的性別差異,社會保障制度設計缺乏應有的性別敏感性,由此造成對女性的覆蓋和保障程度遠遠低于男性,在緩解女性貧困的同時,亦拉大了貧困的性別差距。正如黛安·塞恩思伯里(Diane Sainsbury)在《性別、平等和福利國家》一書中所指出,男性多從事正規工作,從而進入社會保險系統,女性多從事非正規工作或沒有工作,從而進入社會救助系統,二者性質的差異導致女性無法在以社會保障為核心的收入再分配機制中獲得足夠的補償。③Diane Sainsbury,Gender,Equity,and Welfare Stat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最后,市場初次分配、家庭分配和國家再分配中的從屬地位將造成女性在社會中處于從屬地位,導致社會無法為女性提供足夠的支持。社會支持是一定社會網絡運用一定物質和精神手段對社會弱者進行無償幫扶的一種選擇性社會行為,④陳成文、潘澤泉:《論社會支持的社會學意義》,《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年第6期。既是一種物質資源分配機制,又是一種精神資源分配機制。家庭、市場和國家的共同作用使得女性社會支持網絡較為狹窄,以非正式支持為主,正式支持較為匱乏。⑤陳龍芳:《城市貧困女戶主家庭社會支持網的缺失與建構》,《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一方面,家庭的束縛和市場的排斥阻礙了女性社會參與,并導致其失去了獲取正式支持的主體資格。家庭的閉合形態讓女性缺乏參與社會互動的機會和條件,市場的開放形態則讓男性擁有豐富的社會網絡資源和平臺。另一方面,國家對社會的約束作用導致制度的性別盲視加劇了正式支持對女性的忽視,造成社會對女性缺乏主動關懷。社區是女性日常生活和拓展社會網絡的主要平臺,但受國家制度慣性的約束,社區服務體系建設缺乏性別視角,未考慮女性的特殊需求,面向女性的心理咨詢和情感疏導等社會心理服務尤為不足。社會支持的缺乏不僅維持和強化了女性的物質貧困,還容易導致女性遭受社會疏離,在精神資源分配中處于從屬地位,陷入精神貧困。
概括而言,基于生物性別差異的性別分工導致女性承擔了大量無償性質的家庭照顧工作,無法正常參與市場和社會,并在家庭資源分配中陷入從屬地位。家庭的束縛和生物性別差異直接帶來的排斥又造成女性在市場中處于劣勢,不僅受到初次分配的排斥,還受到再分配的排斥。同時,家庭的束縛、市場的排斥和國家的性別盲視消弱了社會整合功能,導致社會無法為女性提供足夠的支持,進而加劇了女性的資源缺乏狀態。由此,資源分配的性別差異在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四個領域的分別作用及其交互作用共同構成了“貧困女性化”得以形成的基本邏輯(見下頁圖2)。

圖2 “貧困女性化”形成的基本邏輯
從上述分析看,伴隨社會分工的持續擴大以及資源分配領域和程度的不斷拓展和加深,“貧困女性化”的基本邏輯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初就已經產生。但“貧困女性化”為何在最近幾十年才形成?個中緣由必然深植于20世紀后半葉的時代背景。
20世紀中期以來,整個世界處于全面轉型的劇變時代。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來,經濟發展方式進一步轉型升級,就業形式更加靈活、多元化,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亦日趨復雜,這為女性參與市場和融入社會帶來了更多的排斥和障礙。同時,福利國家的誕生使得社會保障制度空前繁榮,并與政治、經濟秩序緊密關聯,進而鞏固和強化了男性在資源再分配中的優勢地位。此外,伴隨經濟、社會形勢的轉變以及第二次女權運動的興起,女性的婚姻和生育觀念更加開放,離婚、未婚生育和婚外生育行為日益普遍,不婚主義成為時代新潮,導致家庭結構愈發脆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作用于資源分配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女戶主家庭的大規模增長,進一步加劇了女性在資源分配中的從屬地位,擴大了社會性別差異。女戶主家庭通常家庭規模較小、戶主多為單身且年齡較大、缺少成年男性勞動力、撫養和贍養負擔沉重,①R.S.Katapa,“A Comparison of Female and 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Tanzania and Poverty Implications,” pp.327-339.在這種家庭結構形式中,女性需要扮演家庭照顧者和經濟支持者的雙重角色,極易陷入貧困狀態。在這一時期,資源分配的性別差異的擴大化導致貧困向女性傾斜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加之社會性別、社會排斥理論的興起和貧困理論的發展,貧困與女性的關聯逐漸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綜上可見,“貧困女性化”的形成既是必然,又是偶然。“貧困女性化”不僅是一種自然建構,更是一種文化建構和制度建構。由生物性別差異通過性別分工衍生出的社會性別差異伴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長期存在,但對于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在某種正式的國家和市場以及非正式的社會和家庭因素的作用下,資源分配的性別差異總是處于擴張或收縮狀態。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生物性別差異-性別分工-社會性別差異”是“貧困女性化”形成的基本機制,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四個領域的資源分配是社會性別差異的載體,時代因素作用下的“社會性別差異擴大化”則是“貧困女性化”形成的催化劑。
四、“貧困女性化”的治理策略
生物性別差異和性別分工是“貧困女性化”形成的邏輯起點,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是資源分配產生性別差異的四個基本領域。與之對應,“貧困女性化”治理亦需從生物性別差異和性別分工層面入手,從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四個領域聯合發力。
首先,分擔和轉移女性的家庭照顧責任。生物性別差異先天就已形成,自然無法消除。因此,只有打破性別分工,將女性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才能從源頭上扭轉“貧困女性化”趨勢。然而,打破性別分工同樣面臨諸多難以逾越的障礙。性別分工是始于自然分工的自發機制,正式制度干預缺乏足夠的合法性,而這一自發機制本身卻具有穩定性和延續性。經過長期的塑造和強化,性別分工已然深深嵌套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之中,成為了現代社會形態的重要基礎。從某種意義上看,女性的生理和性格特征確實更加符合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而不利于其進入身心壓力強度較高的勞動力市場。更重要的是,女性承擔著生育的直接責任,這意味著撫養子女和照顧家庭與女性存在天然的關聯。在打破性別分工乏力的現實困境下,家庭領域的“貧困女性化”治理需要尋求新的突破,通過國家機制和社會機制分擔和轉移家庭照顧責任,以減輕家庭對女性的束縛,為女性提供適當參與市場和社會互動的機會。
其次,厘清女性就業與貧困治理的內在邏輯。實際上,近幾十年來促進女性市場參與的努力從未間斷,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隨之產生的“貧困女性化”治理效應卻并不顯著。女性市場參與提高了個人收入和家庭地位,減輕了對男性的經濟依賴。但在這一“向上流動”過程中,女性的權利意識和獨立自主意識不斷增強,這又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家庭結構的穩定性,導致離婚、晚婚和不婚現象愈發普遍,女戶主家庭規模急劇增長,最終形成了新的“貧困女性化”誘因。此外,不少貧困女性實現就業后仍然需要承擔大量家庭照顧工作,進而面臨家庭和市場的雙重壓力,極易陷入“工作貧困”(working poor)狀態,單身貧困女性的處境甚至還有所惡化。①Daniel Edmiston,“Welfare,Austerity and Social Citizenship in the UK,”Social Policy & Society,vol.16,no.2,2017,pp.261-270.這表明,家庭和市場之間的性別分工根深蒂固,其內在關系也十分復雜。因此,市場領域的“貧困女性化”治理路徑并非單純、一味地提高女性市場參與率,其關鍵在于厘清女性就業與貧困治理的內在邏輯,明確女性市場參與的領域和程度,在此基礎上切實推動市場機制改革。
再次,探索性別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社會保障是最核心的再分配機制和貧困治理機制。在家庭和市場發力艱難的背景下,加強對“貧困女性化”的制度回應,為女性提供“去家庭化”和“去市場化”的福利保障,理應成為社會保障的當然責任。從社會保障體系看,社會保險遵循繳費關聯和市場關聯原則,其“貧困女性化”治理功能十分有限;社會救助屬于提供兜底保障的緩貧制度安排,缺乏防貧和脫貧效應,且家計調查和100%的邊際稅率會削弱貧困女性的市場參與動機,貧困治理功能亦較為有限。由此,“貧困女性化”的治理重任將更多地由社會福利承擔。社會福利應當引入社會性別視角,識別女性的特殊需求,調整和設計對應的福利項目。具體而言,既可以在現有福利項目中注入性別差異元素,對資格條件和待遇標準進行參數改革,也可以針對女性的特殊需求,設計專門面向女性的福利項目。在加快發展女性社會福利的同時,仍然應當通過適當改革增強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的“貧困女性化”治理功能。一方面,可以設計面向女性的低繳費型社會保險項目,如挪威的單身母親養老金制度;另一方面,應當踐行積極、發展型的社會救助理念,借鑒西方工作福利(workfare)政策,加強社會救助與就業的聯動。
最后,強化以社區服務為核心的社會支持,同時構建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的聯動機制,形成治理合力。社會支持不僅是非正式的“貧困女性化”治理機制,更是“貧困女性化”治理合力的載體。社會組織或社區機構為女性提供的幫扶具有公益性和選擇性,且無須正式制度加以約束,亦不存在過多利益因素的阻撓,因而在未來具有較大的“貧困女性化”治理潛力。強化社會支持尤其要引導社區服務體系向家庭護理、托兒服務等領域擴展,以分擔和轉移女性照顧家庭的責任,為其適當參與市場和社會提供更多的機會,從而提升家庭和市場的“貧困女性化”治理功能。同時,女性社會福利的供給與遞送可以考慮引入第三部門力量。第三部門具有較強的執行力和創造力,取得的行為效果能夠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應。更重要的是,第三部門擅長處理個案問題,這正契合了“貧困女性化”具有多樣性和異質性的本質特征。總之,社會支持與家庭照護、女性社會福利的融合,有助于統籌、協調多方資源,形成“貧困女性化”治理合力。
五、結論與討論
“貧困女性化”是一個復合概念,是資源分配不平等和性別不平等相融合的結果。本文以資源分配為核心維度,構建了“資源分配-作用領域-歷史演進”的理論分析框架,從生物性別差異這一原點出發,以性別分工為紐帶,考察資源分配的性別差異。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性別分工經歷了從自然分工到社會分工的演變,資源分配亦經歷了從單一領域到多個領域、從不存在性別差異到存在性別差異并擴大化的過程。雖然20世紀后半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變遷為“貧困女性化”刻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但“生物性別差異-性別分工-社會性別差異”這一“貧困女性化”形成的基本邏輯根植于原始社會,成型于資本主義社會并趨于穩定。在社會形態更替以前,時代因素顯然無法改變“貧困女性化”形成的基本邏輯,但可以影響貧困向女性傾斜的速率。
較之復雜的形成機理,“貧困女性化”的治理空間顯得略微狹窄且面臨內生性矛盾,主要限于從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四個領域減小資源分配的性別差異。由于不可抗拒的生物性別差異決定了貧困性別差異的客觀性和長期性,可以預見的是,家庭和市場領域的貧困治理將面臨諸多限制和挑戰,“貧困女性化”現象亦難在短期內得到切實扭轉。但家庭與市場的關系依舊存在調整空間,社會保障領域的性別空白仍然可以填補,以社區服務為核心的社會支持孕育著巨大的貧困治理潛力。因此,“貧困女性化”程度有望得到持續控制和降低。
“貧困女性化”是一個新現象、新命題,尤其是在中國。西方相關研究雖然積累了大量文獻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始終處于揭示“貧困女性化”現象、孤立分析其成因和對策的描述性和探索性階段。最近10年,一些中國學者如姚桂桂、王淑婕、寧滿秀、付玉蓮、張穎莉①姚桂桂:《試論美國“貧困女性化”——20世紀后期的一個歷史考察》,《婦女研究論叢》2010年第3期;王淑婕、解彩霞:《中國貧困女性化的社會制度根源——基于可行能力視角的分析》,《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寧滿秀、荊彩龍:《貧困女性化內涵、成因及其政策思考》,《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年第6期;付玉蓮、劉力永:《全球化與貧困女性化:賈格爾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思想解讀》,《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17年第6期;張穎莉、游士兵:《貧困脆弱性是否更加女性化?——基于CHNS九省區2009年和2011年兩輪農村樣本數據》,《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第4期。等,已經開始關注“貧困女性化”這一命題,但多限于介紹西方研究成果,本土化研究也并未突破西方研究的局限性。“貧困女性化”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現象層面,還需要在理論層面有所突破,這就需要構建清晰的理論分析框架,本文正是基于此而做出的一種嘗試。當然,必須承認的是,本文亦有諸多尚未涉及或取得實質性突破的關鍵領域,這些領域在未來研究中也需要進行更多的理論探討和經驗觀察。
第一,“貧困女性化”測量。既有研究測量“貧困女性化”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統計貧困人口中的女性占比,另一種是統計貧困家庭中的女戶主家庭占比。這兩種測量方法都存在局限性,前者容易受到人口性別結構因素的干擾,后者實際上改變了“女性”的定義,并且忽視了男戶主家庭中的女性貧困現象。因此,如何精準測量女性個體的貧困發生率是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第二,家庭與市場的關系。正如前文述及,平衡女性在家庭和市場領域的角色和作用,厘清女性就業與貧困治理的內在邏輯,明確女性市場參與的領域和程度,是未來研究打破傳統性別分工、走出“貧困女性化”治理困境的關鍵。
第三,本土化研究。“貧困女性化”既有其內在一般規律,又有較強的地區和國別差異。之于中國,在儒家文化的長期熏陶下,“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觀念在一些欠發展地區仍然占據家庭意識形態的主流。這表明,中國存在“貧困女性化”誘因,但“貧困女性化”事實又容易被傳統觀念所掩蓋。此外,中國女性較之西方女性家庭觀念更加濃厚,“女戶主”現象并不常見,但家庭決策和資源分配卻有著更為深厚的“貧困女性化”土壤,社會保障和社區服務領域亦存在性別空白。因此,在未來研究中,不僅要關注“貧困女性化”這一源于西方的前沿命題,更要基于“貧困女性化”的理論分析框架,立足傳統文化和現實國情,具體考察家庭、市場、國家和社會四個領域資源分配的性別差異及其互動,同時聚焦新時代背景下社會性別差異擴大化的潛在因素,揭示、應對抑或預防“貧困女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