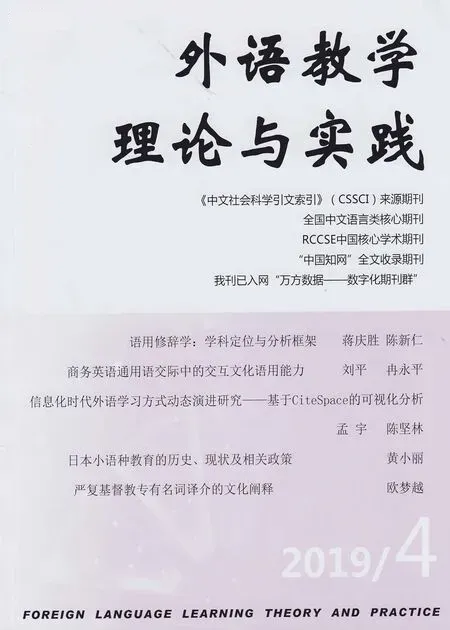嚴復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的文化闡釋
復旦大學 歐夢越
一、引言
嚴復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是指嚴復論及基督教的所有著述(包括譯著和論著)中的專有名詞譯介,包括人名、地名、著作名(書名、篇名、章節名)、流派名、重要概念等。目前學界關于嚴復基督教譯介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李安澤、李熾昌與李天綱、李熾昌與涂智進、任東升等學者的文章,主要聚焦于嚴復如何認識基督教,屬于一般的翻譯研究和宗教思想史研究。至于深入到詞語層面進行具體而微的細化分析,國內外學術界尚無專文研究。業師鄒振環先生《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多處論及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筆者深受啟發。嚴復所譯基督教專有名詞中,不少與同時代其他學者筆下的基督教專有名詞譯法不同,如“畢協”“波羅忒斯坦”“票利丹”,往往使讀者頗感費解。其實,“畢協”即通譯“主教”,“波羅忒斯坦”即通譯“新教徒”,“票利丹”即通譯“清教徒”。而一些專業辭典極少給出這方面的解釋,無法滿足讀者需求。本文以“溯源”式的考釋方法,從上下文具體語境中找出嚴復翻譯的英文原詞,在初步系統梳理考辨的基礎上,進一步予以文化闡釋,同時糾正學界錯誤的解釋,旨在為閱讀和研究嚴復著譯掃除閱讀障礙,同時提升嚴復譯詞研究的文化意味,這對拓展和深化、細化嚴復研究、基督教譯介史研究以及近現代語言史、翻譯史研究領域,具有不言而喻的價值和意義。
二、遵循基督教漢譯傳統與“別出心裁”
嚴復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和英國經驗主義、保守主義思想的雙重影響,十分尊重傳統,對傳統充滿敬畏之心,尊重前人的成果,重視知識的積累性。因此,他的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許多地方仍遵循基督教漢譯傳統。光緒三十四年(1908),嚴復時在上海,受“大英圣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即“英國及海外圣經會”總經理文顯理的委托,用文言翻譯《圣經·新約·馬可所傳福音》(僅完成前四章)。他基本上遵循教會的《圣經》漢譯傳統,即當時的通行譯法。上帝、基督、耶穌、福音、以賽亞、約翰、猶太、耶路撒冷、約旦、加利利、拿撒勒、西門、安得烈等,皆為當時通譯名。又如,嚴復將God譯為“上帝”,Gospel譯為“福音”,Holy Spirit譯為“圣靈”,等等。公元7世紀,景教傳入中國,“耶穌”音譯為“移鼠”“翳數”,同時期明教(摩尼教)將“耶穌”譯為“夷數”,自明末天主教耶穌會士來華傳教,Jesus的音譯多達“熱所”“耶書”“耶遜”“耶穌”數種,后改譯為“耶穌”,通用至今。上帝,通譯“耶和華”,漢語音譯分別有“耶和華”“雅威”“耶威”“亞衛”等。耶穌會士將Sacerdos(Priest)譯作“撒責爾鐸德”,簡稱“鐸”“鐸德”或“司鐸”,“神父”“神甫”是日常對“司鐸”的尊稱。相比其他不常見或已被淘汰的譯法,嚴復采用耶穌、耶和華、神父、神甫等通行名詞。嚴復受托譯《圣經》,不只限于提升《圣經》翻譯的品位,化淺俗為文雅,目的更是在于普及與接受,以期減少基督教傳播在士大夫文人階層中的阻力,故采取“吾從眾”的策略。
嚴復常將基督教(Christianity)譯為“景教”。光緒十八年(1892),他翻譯《支那教案論·教事篇》,曰:“景教西來,始于明季;定約容納,保護于本朝道咸間”(汪征魯等,2014:卷五,520)。光緒三十二年(1906),《論南昌教案》曰:“考基督教之來中國,最早莫如景教”(汪征魯等,2014:卷七,197)。《法意》案語說:“夫歐洲景教之禍,中古最烈:固迷信也”(汪征魯等,2014:卷四,572)。“景教”原名“Nestorianism”,于唐太宗貞觀九年(635)由波斯人阿羅本傳來中國,取名“景教”。“景”,光明之意,喻耶穌給人間帶來光明。古有景凈《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吳相湘,1965:62)。實際上,唐代傳入中國的景教只是基督教的一支(聶斯脫利派),用來指稱全體基督教,嚴格說來并不準確。
戴維·萊特認為嚴復用“景教”一詞來翻譯Christianity,是他傾向于有意選用古代漢語體系中的語詞將西方新詞直譯或者實現其本土通俗化的一個例證,因為“景教”實際上是出現在唐朝的一個名詞(Wright,2001:235-249)。嚴復在《原富》中介紹景教之國時,對自己的譯詞選擇做如下解釋:“考唐之《景教碑》,所謂景教者,實非基督教宗,乃教外別傳。今借用為教宗統名,以偏概全。古之命名,固有此法也”(汪征魯等,2014:卷二,125)。嚴復認為“以偏概全”是古已有之的譯詞“命名”方法,流行已久,故沿襲使用。可見,嚴復尊重譯詞的“約定俗成”,與此同時,他十分清楚“景教”作為譯詞的不準確性,為此還特意考辨一番,體現出科學而嚴謹的學術態度。實際上,“以偏概全”,即以部分代全體,本是古代漢語修辭格中的“借代”,是古人習慣的一種語言表達。從這一角度看,“景教”譯詞也無可厚非。戴維·萊特并未具體明確指出嚴復之所以襲用傳統譯法,是因為尊重古人“借代”修辭手法,他只是大而化之地用“本土通俗化”來解釋,說明他對嚴復譯詞選擇所蘊含的傳統文化信息的認識還不夠明晰。嚴復并非無知,而是尊重傳統積累的經驗,是退而求其次的有意為之。
嚴復一方面尊重傳統,另一方面又敢于并善于創新。在進行基督教名詞譯介時,他時而沿襲通譯,時而有意“別出心裁”創制譯詞。對于譯事,他內心有自己的標準與主張,他的譯名也往往有別于通譯名。
嚴復《論南昌教案》曰:
西班牙人,名羅曜拉,本為軍人,以傷出伍。至一千五百二十八年,學于巴黎大校。目擊舊教中衰,結合同志于一千五百三十四年創立新派,號耶穌軍,以勸轉信心,抵制新宗為要旨。教皇保羅第三嘉獎所為,于一千五百四十一年降敕,以羅為耶穌軍上將。(汪征魯等,2014:卷七,197—198)
伊格納修·羅耀拉(1491—1556),又名伊納爵·羅耀拉,嚴復譯為“羅若拉”或“羅曜拉”。1534年,西班牙貴族羅耀拉在巴黎大學創立耶穌會,仿軍隊建制,紀律森嚴,要求對宗座絕對忠誠。嚴復領會原詞的本質內涵,將通譯的“耶穌會”譯為“耶穌軍”,突出其半軍事組織的特征,十分合理。
Lutheran Sects,通譯“路德教派”,信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教義之教徒,嚴復譯為“路得宗”。《原富》曰:“所謂異宗者有二:一曰路得宗,一曰葛羅云宗”(汪征魯等,2014:卷二,545)。John Calvin(法語Jean Calvin,德語Johannes Calvin,1509—1564),通譯“約翰·加爾文”,又譯“嘉爾文”“喀爾文”“克爾文”“卡爾文”等,嚴復音譯為“葛羅云”。卡爾文派(Calvinists,Calvinistic sects),通譯“嘉爾文主義”“加爾文宗”,亦稱“長老宗”“歸正宗”,嚴復譯為“葛羅云宗”。《原富》曰:“葛羅云宗之用于蘇格蘭者,其制小有損益,而為伯理斯白特宗”(汪征魯等,2014:卷二,546—547)。嚴復譯“摩蒙宗”(Mormonism),通譯“摩門教”。“宗”,指宗門、宗派、派別,佛教名宗有禪宗等;“派”,派別,宗教或團體內因不同主張而形成的各種分支或門派。“宗派”連用,也可分用,宗即派,派即宗,并無本質區別。嚴復習慣以“宗”代替“派”,而“派”成為至今通行的譯名。
光緒二十九年(1903),嚴復譯《群學肄言》曰:“吾英三百年以往,固已有持其說者,呼刻爾《宗教群法》第一編,嘗舉此義,非所謂矚遐鑒洞者耶?當其世所謂科學,與一切科學之思想,闇汶無足言者,而呼刻爾氏獨具先覺如此,斯足異矣”(汪征魯等,2014:卷三,200)。呼刻爾,是嚴復對Richard Hooker(約1554—1600)的音譯,通譯“理查德·胡克”或“理查德·胡克爾”,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圣公會神學家,因與清教徒特拉維斯(Walter Travers)于1586年圣殿教會(Temple Church)辯論而名震一時。臺灣林載爵主編《嚴復合集·群學肄言》注釋說:
呼刻爾,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嚴復又譯福克爾,英國植物學家,曾到南極、印度、紐西蘭、北非、北美等地,發現許多新品種,認為植物變種與生長環境有密切關系,并在植物上證明“進化論”的存在,與達爾文是密友,著有《植物的屬》,書中收集植物7 569屬,約97 000種。(林載爵主編,1998:350)
按:《群學肄言》譯自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于1873年所著《社會學研究》(TheStudyofSociology)一書。斯賓塞于1873年明確說“吾英三百年以往,固已有持其說者”的呼刻爾(胡克),顯然絕對不可能是自己同時代的約瑟夫·道爾頓·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此Hooker非彼Hooker也。《嚴復合集》編者的注釋顯然是錯誤的。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學界無人發現這一錯誤,一直以訛傳訛。
三、“同名異譯”的得與失
近代中國處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識、新概念的草創期,許多譯詞的通行譯名尚未確定,不同譯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創制不同譯名,同一術語在不同譯本中的意義差距很大,甚至同一個譯者,不同作品、同一作品中也存在譯名的不統一現象。(1)同一名詞,往往存在多種譯法,即“同名異譯”,又稱“一詞多譯”。如society同時有社會學、群學、世態學等漢譯名;science對應漢譯有格致學、物理學、科學;philosophy有哲學、智學、愛智學、理學、性理學等漢譯并存;economy有計學、經濟學、生計學、理財學、財政學、平準學等漢譯并存;logic一詞的中文譯詞有名學、辯學、論理學、理則學,等等。名詞的繁蕪是近代譯本的顯著特征,正如《瀛寰志略》中所總結的:“十人譯之而十異,一人譯之而前后或異”(徐繼畬,1866:3)。嚴復筆下,“同名異譯”現象尤為突出,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也是如此,或有別于他人譯名,或是自己對同一詞有不同譯名,因此有必要專門論述。
嚴復常常音譯、意譯并用,造成譯名的多樣化。The Society of Jesus,通譯“耶穌會”“天主教修會”,嚴復襲用,《政治講義·第七會》曰:“諸公倘以吾言為疑,則請觀二百年來泰西之歷史,雖有極放任政府,其于耶穌會Jesuitism一宗,其驅逐無不至嚴。無他,惡其權盛而已”(汪征魯等,2014:卷六,59-60)。同時,嚴復又將Jesuitism音譯為“葉舒伊會”,《群學肄言》曰:“如西班牙之羅若拉,創為葉舒伊會,本以保教,后乃樹黨擅利,權傾國家,而終于屏逐”(汪征魯等,2014:卷三,21)。Protestantism,通譯“新教”,嚴復意譯為“修教”。《原富》曰:“蘇格蘭之布里必斯持,與瑞士之葛羅云大同小異,乃修教之一大宗,與羅馬公教異門者也,斯密氏特舉之”(汪征魯等,2014:卷二,第126)。《群學肄言·教辟》“教之為辟”一段眉批曰:“以下言歐洲通行基督教派之辟。加多力即公教,即羅馬天主,其舊者也。波羅脫斯坦即修教,即耶穌,即誓反,其新者也。二宗之外尚有特宗,特宗者不純主國教而樹義自立者也”(汪征魯等,2014:卷三,181)。“加多力”即公教的音譯,“波羅脫斯坦”即“修教”的音譯,嚴復還將“修教”音譯為“波羅忒斯坦”,《群學肄言》曰:“乃至加多力宗之謂波羅忒斯坦宗也,其不平亦然”(汪征魯等,2014:卷三,182)。
音譯法是近代中國人譯介西方新概念常用的方法和策略,嚴復也不例外,在其基督教專有名詞中,音譯詞所占居多。譬如嚴復譯詞“加多力”(Catholic,Catholic Church),通譯“天主教”;“托直斯特麥”(Methodists),通譯“衛理公會派教徒”;“摩爾底斯”(martyrs),通譯“烈士”“殉難者”;“亞達那獻”(Athanasian),通譯“信奉亞大納西教義之人”;“旁狄非加特”(pontificate),通譯“教皇職位”;“票利丹”(puritans),通譯“清教徒”。(2)光緒四年二月九日(1878年3月12日),嚴復與郭嵩燾論及張力臣《瀛海論》,張力臣提出十字架和天主教流傳自東方,嚴復批駁道:“不識所流傳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則羅孟克蘇力也,何處覓‘天主’二字之諧聲、會意乎?”(郭嵩燾,1984:497)。可見嚴復對該詞也主張音譯。至于何時用音譯,何時用意譯,合理的解釋是,在從事《圣經》譯介活動時,嚴復考慮到原著傳播教義的宗旨,故多采用“約定俗成”的譯法。而在翻譯學術性著作時,嚴復把讀者對象預設為飽讀詩書的士大夫文人,他便自如地根據所需采取不同的譯法。新詞的創制無非音譯、意譯和釋譯三種。音譯簡單直接,直觀感強烈,便于讀者誦讀,然而,音譯容易造成語義理解與記憶的困難,這一弊端也導致了嚴復音譯的絕大多數詞語后來被淘汰(參見黃克武,2012:97)。近代西學譯事活動中,關于音譯與意譯的討論也從未停止。(3)狄考文認為翻譯中過多使用西方文學中常有的描述性語言,不符合漢語的特點,相比冗長的表達或是詞不達意,音譯勝于意譯(Mateer,1904:1-2)。傅蘭雅則認為漢語不能夠適應西方的思想文化,單純的音譯或直譯也不利于記誦和理解,不應提倡。譯名應該采取意譯,或者必要時采取音譯與意譯相結合的方式創制新詞(Fryer,1890:534-538)。嚴復翻譯并未拘泥于某一種形式,而是音譯與意譯并用,并融入文化闡釋,旨在會通中西。
嚴復的“同名異譯”有得亦有失,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即使同一個名詞,他也創制多個音譯。abbot,通譯“男修道院院長”,他音譯為“亞博”和“阿勃”;Presbyterian Church,通譯“長老會”,他音譯為“伯理斯白特”“伯理斯白特宗”;pope,通譯“教皇”,他音譯為“樸柏”“樸伯”。Moses,通譯“摩西”,嚴譯“麥西”;Mecca,通譯“麥加”,嚴譯“墨加”;Monsieur Jourdan,通譯“約旦”,嚴譯“約但”。以上譯名并無本質差異,同為音譯,嚴復擇取相似讀音的不同漢字,繁衍出不同譯名,看不出有何深意,倒是徒增了譯名的繁蕪。此外,嚴復將missions譯為“居留所”,明顯不如通譯“布道所”準確。
盡管嚴復許多譯名最終未能走進現代漢語體系,但不少譯名本身仍具有學理性價值,甚至比通行譯詞更為合理,如以“畢協”譯bishop(通譯“主教”),音譯兼意譯,不失為一個好譯名。嚴復譯詞“華理”(Whalley),克服了通譯詞“華里”作為長度單位可能引起的歧義。再如“牛德階”(Newdegate)一詞充分體現了人名翻譯的“中國化”特色,比起通譯“紐德蓋特”,以中國人的姓氏“牛”對應“new”,凸顯本土文化的同時,也符合英文發音的規律。語言的通行與否,固然取決于其本身有無科學性,但仍有不少是遵從“約定俗成”的規律,摻雜著不少“非學理”性因素。通行的未必是最合理的,被淘汰的也未必皆不合理,今天對嚴復的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甚至嚴復創制、使用的所有譯詞也應作如是觀。
四、“本土化”理論自覺
唐代,儒、釋、道三教鼎立,景教傳入中國后,為了適應和生存,傳教士譯介時主動與儒、釋、道融合,探尋在華傳教策略,做了不少“本土化”的努力。(4)異質文化要想走進一種新的語言,在新的文化語境下得到重生,必須做出一定的“本土化”努力。明末清初的來華耶穌會士們制定“適應性”策略,在中國文化語境下譯介西方概念,促進了中西文化溝通與融合。(張國剛,2003:357—365)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載,景教傳入中國時,《圣經》譯述往往附會道家之言,如“天尊”本出道教,《序聽迷詩所經》以道家的“天尊”稱基督教的上帝(天主)(參見朱謙之,1993:117)。不僅如此,景教士也借用善緣、妙有、慈航、世尊、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等佛教概念術語,且“僧”字常用于景教中人物的漢譯,如“僧景凈”“僧業利”“僧行通”“僧靈寶”,等等(參見俞強,2008:70)。
嚴復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有明確的“本土化”理論自覺。他“以儒解耶”,即譯名采用傳統儒家概念。如disciples,嚴復譯為“弟子”,弟子,即學生,《史記》有《仲尼弟子列傳》。嚴復以“文士”翻譯scribe(猶太法學者,宗教導師),“文士”,指讀書人,知書能文之士。漢語中,“文士”并沒有宗教含義,但嚴復的“文士”譯名顯然讓正統儒生們滿意,雖然嚴格說來并不準確,但確實拉近了堅守傳統的儒生們與《圣經》的心理距離,也正符合嚴復對目標讀者的期待,即“多讀中國古書之人”(汪征魯等,2014:卷八,121)。
更多時候,嚴復選擇“以佛解耶”,即用佛教概念翻譯詮釋基督教概念。漢明帝時,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駝經來到中國,初止于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立白馬寺,后世“寺”遂指佛教場所,浮屠所居皆曰“寺”。故嚴復特以“(教)寺”翻譯西方的教堂,如以“圣波羅寺”譯“圣保羅教堂”(St.Paul),以“峨特教寺”譯“哥特式教堂”(Gothic Church)。嚴復又以“長老”來翻譯主教,如Archbishop Sumner,通譯“薩姆納大主教”,嚴復譯為“山蒙納長老”。“長老”,本指老年人,德高望重的年長者,佛教中尊稱釋迦上首弟子,如長老舍利弗、長老須菩提,或尊稱住持僧和僧人。
佛教名詞罪業,指身、口、意三業所造之孽,也泛指應受惡報的罪孽。嚴復借用佛教有關“罪”的概念,如以“罪業”和“罪過”對譯基督教的“罪”(hamartia),將罪人譯為“造孽者”。其實漢語本身沒有對譯的詞匯,嚴復做了“處境化”處理,這是一種“格義”(李安澤,2012)。嚴復將禁食譯為“齋而禁食”。在撒種的比喻中,他以佛教概念“善地”譯“好土地”,以“福報”譯“好莊稼”。這些譯法未盡準確,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西宗教文化差異。“格義”之法古已有之,更是近代中國學人最常用的意譯解讀西學的方法,即以中國傳統為坐標系,用比較、類比的方式解釋跨文化背景下的西學概念。這種帶有比附性的“格義”,嚴復著譯中多有存在。
嚴復常借助中國傳統作為參照物,即將漢語文化體系作為“中間人”,引介西方新知識、新概念,旨在會通中西文化。“基督”,意為“受膏者”,是一種名銜,而“耶穌”是名字。嚴復所譯《圣經·新約·馬可所傳福音》第一章中,將“耶穌基督”順序顛倒為“基督耶穌”,稱“上帝子基督耶穌,福音之始”,將個人名字置于后,符合中國傳統的人名表述習慣。與此同時,嚴復也能夠清晰地辨別出中西文化語境下同一名詞內涵的本質差異,他指出,西方的“教”“師”不同于中國,“中國君師之權出于一,而西國君師之權出于二”(汪征魯等,2014:卷二,550),“又其所謂師者,非止于授業解惑,與夫以善教人已也。必求其似,則猶古者之巫祝……其所業皆介于天人之際,通夫幽明之郵”(汪征魯等,2014:卷二,550)。西方的“教”是宗教,“師”是傳教士;中國的“教”本義是教育,上所施下所效,傳授文化知識,進行倫理道德教育,“師”是教師,皆與宗教無關。
嚴復對基督教的認識,帶有傳統文化的深刻烙印,傳統觀念作為“前理解”在其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中發揮前導性作用。(5)李安澤(2012:42)認為傳統文化是作為解釋基督教過程中的“前見”。嚴復采取“歸化”策略,創制新名詞,翻新古典語義,豐富擴大了近代漢語詞匯體系,盡管有些譯詞不盡完善,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局限性。勒弗維爾認為,翻譯就是文化“改寫”(rewrite),“改寫”就是一種“操縱”(manipulation)(Lefevere,1992:9)。改寫往往出于不同意識形態的需要,如果不同文化背景的意識形態之間發生沖突,譯者自然有必要進行一些“改寫”,讓原文和原作者更加走近讀者,滿足目的語群體的期待。“改寫”是一種文化“再創造”,它賦予原文以新的內涵和意義,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一方面,嚴復身為譯者,即翻譯活動的主體,他是一名“操縱者”,巴斯奈特認為,在文化功能等值的過程中,譯者有較大的主動權,可以靈活改寫,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學形式(Bassnett.&Lefevere,1990:10)。但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的“操縱”下,嚴復又是一名“被操縱者”,囿于權力話語,難以幸免。他的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的優劣皆由此造成。
嚴復強調指出:“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汪征魯等,2014:卷八,121)。他深受“桐城派”古文理論影響,對譯詞有明確的典雅化追求,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講究“雅潔”“雅馴”,以“雅言”來“達旨”,“雅”與“俗”相對,又有“古”“正”含義。嚴復以“桐城派”所推崇的漢以前單行散體古文來譯介西學名著,反對使用“近世利俗文字”(汪征魯等,2014:卷一,79)。古雅、簡潔的語言,是為了培養文化精英,即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而不是“市井鄉僻”之淺學者。中西語言相互溝通,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嚴復譯詞尤具古典美,如以傳統術語,將“司”譯為“太祝”,將“圣殿”譯為“神宮”。再如嚴復譯詞“神甫德黎”和“神甫竺薩穌”,分別對譯通譯的“神父特雷”(Abbe Terray)和“杜塞爾梭神父”(Father Ducerceau)。甫,古代男子名字下所加美稱,多用于表字之后,又作男性長輩的通稱,亦通“父”。嚴復所譯“神甫”比通譯“神父”更加雅馴。雖然英語文化中對神父的尊稱的確是父親的“父”(father),但嚴復選擇古漢語“甫”,更加符合傳統文人的審美文化心理,也符合他的傳統儒者的文化身份。
書名是一類特殊的專有名詞,嚴復的書名翻譯也十分講究雅馴。嚴復譯呼刻爾(胡克)《宗教群法》(EcclesiasticalPolicy),即《教會組織法》或《教會政制法規》(OftheLawsofEcclesiasticalPolity)。“群”是嚴復獨創的概念,群學,即社會學。嚴復譯《迦南錄》,即《迦南樂土》。“錄”,古代記載言行或事物的書冊,如唐李翱《來南錄》、宋文天祥《指南錄》,還有《景德傳燈錄》《碧巖錄》等禪宗語錄。BookofJob,嚴復譯為《喬布之記》,即《喬布書》。“記”,記載事物的書冊或文字,如《史記》《夷俗記》《列國變通興盛記》。嚴復譯詞承繼古人書籍命名之特點,極富傳統文化意蘊。
嚴復有強烈的承舊統、開新域的文化使命感,他選擇先秦典雅文言翻譯英文著作,實際上即是表明了自己的主體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場。他的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也不例外。嚴復對基督教專有名詞做中國化的“處境化”處理,即是主體文化融入和滲透的有力佐證。語言代表一種文化積淀,“詞語破碎處,無物可存在”(海德格爾,2015:217)。嚴復選擇“雅馴”文言,而不使用白話文翻譯英文,讓英文與古漢語對話,強調傳統文言的現代價值,強化對傳統文化的崇敬和承繼,不使母語“破碎”,極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歐夢越,2015)。
五、結論
嚴復基督教專有名詞譯介,首先遵循基督教漢譯傳統,采取“吾從眾”的策略,尊重譯詞的“約定俗成”,如沿用“景教”譯詞,但對其不準確性有清楚的認識。同時又“別出心裁”,獨創譯詞且多用音譯,帶有時代色彩。嚴復將Richard Hooker音譯為“呼刻爾”,通譯“理查德·胡克”,林載爵主編《嚴復合集·群學肄言》將理查德·胡克注釋為約瑟夫·道爾頓·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顯然是錯誤的。嚴復基督教譯名中,“同名異譯”現象突出,有得有失。其中不少雖在近現代譯名史上逐漸被淘汰,但有些譯名本身仍具有學理性價值,不可輕視。近代基督教專有名詞漢譯,因缺乏統一規范,譯者多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翻譯。嚴復譯詞雖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但不少專有名詞譯介具有明確的“本土化”理論自覺,如“以儒解耶”,特別是“以佛解耶”,儒、佛、耶三者會通,且譯詞追求典雅化,旨在不使母語“破碎”,極具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