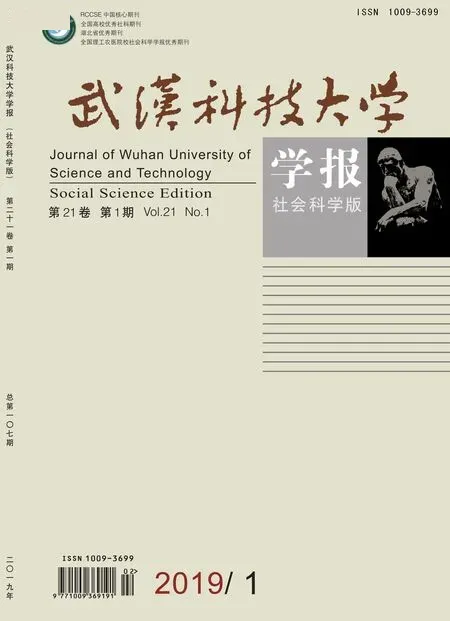楚地、楚風與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浪漫主義
——以海外湖北籍作家作品為例
鄒 建 軍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430079)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海外華文作家的文學創作引起了學界的特別關注,一是因為國與國之間的文學交流已經相當順暢,二是因為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異質性得到了特別的重視,三是因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公民中有大量人員移民海外,特別是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歐洲各國。在這一批新的移民中,許多都是知識精英與商業精英,其中包括不少在國內時就已經有影響的作家與藝術家(嚴歌苓、張翎、程寶林、王性初等在國內就開始了文學創作,并且有的作品在文壇上具有比較大的影響,如嚴歌苓在出國前就著有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人寰》等作品,享有廣泛的文學聲譽)[1]。當然,海外華文作家受到學界特別關注的最重要原因,還是因為這批新移民中的作家到了所在國以后,陸續創作出了杰出的作品,許多作品在國內發表以后,在中國以至于在世界上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在這些海外華文作家中,現在看來已經是一流作家的也不少,有的還超過了當代中國大陸的作家。嚴歌苓、張翎、劉荒田、陳瑞琳等作家和評論家,就其文學成就和文學地位而言,與國內的一流作家相比,一點也不遜色,并且略有超越,為國內學界所公認。以嚴歌苓為例,其旅美后的作品善于從“他者”文化視角審視、表現東方文化,具有更加廣闊的格局與深度。所以,改革開放40年來,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確正在成為國內學術界與批評界關注的一個熱點。這種情況的出現,正是我們今天討論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浪漫主義與楚地、楚風關系的重要前提。如果海外華文文學創作本身沒有什么起色,如果從湖北移民到海外各國的作家沒有創作出什么像樣的文學作品,在中國或者世界當代的文學史上沒有占一席之地,我們討論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浪漫主義,也就沒有基本的對象,討論本身也就失去了意義。然而,如果沒有具有創新意義的文學理論,也不足以說明特定地域的文學現象,因此,援用現有的文學地理學批評理論,以中國學者自己建構的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來觀照海外的華文作家及其文學文本,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本文擬討論以下四個問題,以供方家批評指正:一是地理記憶與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時間敘述;二是地理感知與海外華文文學的審美意識;三是地理思維與海外華文文學的空間建構;四是時間與空間距離與海外華文作家藝術構想之間的聯系。
一、地理記憶與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時間敘述
在海外華文文學體系的三大部分中,占據主體地位的當然是移民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是一個龐大的體系,一般認為包括早期的臺灣留學生文學、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新移民文學和第二代、第三代華人用英語所創作的華裔文學三個大的部分,其中移民文學特別是新移民文學占有比較大的比重,作家眾多,作品數量大、質量高,影響也在不斷擴大。當然,早期的臺灣留學生文學中有許多一流作家作品,華裔英語文學也有許多一流作家作品,成為了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與作品[2]。在海外特別是在美國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比利時及東歐諸國,那里的華文文學創作與評論,相當活躍與繁榮。第一代華人肯定是移民,第二代以及之后的華人,由于受教育的原因和社會環境的限制,基本上不再用漢語進行寫作,雖然有一些華人后代由于家庭的原因,會產生深厚的中國情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然而,他們用英語或其他語種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不屬于海外華文文學系列,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范圍。因此,所謂的海外華文文學,主體部分就是所謂的移民文學或新移民文學。
移民文學是對世界上由于移民現象而產生的文學現象的統稱,針對世界上所有的語種與所有的國家,并不只是限于華人移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本身是移民國家,第一代人所創作的文學肯定是移民文學,因此,這些國家所謂的移民文學就不限于來自于中國的移民所創作的文學。而“新移民文學”是一個特定的術語,是指改革開放以后,從中國大陸或從臺灣、香港、澳門移民到海外各國家的作家所創作的文學。無論是移民文學還是新移民文學,都存在一個時間的問題,并且,他們在所有的文學作品里所表達的時間,往往與作家的地理記憶有關。所謂“地理記憶”,就是作家自小開始的對特定地理的印象而產生的記憶,隨著自然時間的流逝而形成的種種印象,這樣的記憶也許前后并不一致,疊加起來就成為了作家地理記憶的主要內容。如果一個作家其出生地、成長地、發展地、祖居地是同一個地方,地理記憶也許會相對簡單一些;如果它們不是同一個地方而是相距很遠的多個地方,這位作家的地理記憶則會比較復雜,甚至于相當曲折與繁復。如果一個作家移民海外的時候十八歲,剛剛完成高中學業,或者晚一點如大學畢業的時候,較少機會去到更多的地方,那么他的地理記憶會相對單調一些;如果一位作家在移民海外的時候,已經是人到中年,在人生的中年以前就已經因為讀書、服役、經商或從政等原因,到過國內的許多地方甚至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并且所到過的這些地方在地形、氣候與物候方面差異甚大,那么,他的地理記憶就會更加復雜,甚至十分曲折。所以,一個作家的地理記憶,不但與所到過的地方有關,并且與在某一個地方所呆的時間長短有關。出生于武漢、祖居湖北廣水的作家聶華苓女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在從事文學創作之前,因為當時中國已經發生抗日戰爭,社會動亂不堪,加之外出求學的原因,她已經到過重慶、恩施等諸多地方。解放戰爭結束之后她先是到了臺灣,后來又到了美國,繼續從事文學創作,這些作品在中國大陸和海外文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們說她的地理記憶比較復雜,她的作品主要寫過去在中國大陸的生活,值得全面研究與深入探討。聶華苓到了美國以后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在對時間的敘述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許多從前的地理記憶,當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記憶,成為了其小說敘述的主要內容。她在美國創作的《桑青與桃紅》等長篇小說,回憶自己早年在楚地的生活與青春時期的情感,具有重要的地理意義與文化價值。她在臺灣創作的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敘述的是發生在宜昌三斗坪的故事,小說中對具有恩施地區和三峽地區濃郁特點的地理風景的描寫,總是使人想起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描寫并不比沈從文作品遜色,反而更有特色與味道。至今為止,這部描寫鄂西自然山水與三峽地區人文風情的作品,仍然是20世紀以來關注三峽地區自然風情與人物生活最好的小說之一。她在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中,表現自我在抗戰期間三峽地區的生活經驗以及一批知識分子在大時代里的沉淪與憂慮,保存了特定地理環境之下所產生的地理影像以及那個時代所可能產生的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出生于湖北沙洋的詩人程寶林,在老家上了小學、初中與高中,留下了真切的、復雜的地理記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以后,他曾經在《四川日報》做副刊編輯多年,20世紀80年代后期移民到美國。在美國,他主要從事詩歌創作與散文創作,其中許多作品是寫他小時候在荊門鄉下漢水邊的生活,以及那里的山形水勢、民俗風情、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化,所以,地理記憶對于他而言就會簡略一些,主要是一種少年記憶和青春期的人生經驗與生命歷程,沒有像聶華苓及其作品中保存的那么復雜。當然,文學作品里的地理記憶也是因人而異的,有的人對地理因素特別敏感,有的人對地理因素不太敏感。對于時間的記憶也是一樣,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記憶,然而作家對于時間與空間往往都會比較敏感,不然就創作不出全新的作品。
海外華文作家的文學作品在對于時間的敘述中,存在今天的故事、昨天的故事、昨天以前的故事三種類型。時間越長,也許地理記憶就越模糊,但也許地理記憶就越是清晰、越是深刻,這都是因人而異的,但地理記憶會成為文學作品的重要內容,地理記憶也會影響作家對于自然地理與人物命運的敘述,則是自然而然的、絕對肯定的和有規律性的。任何作家都不可否認自己的創作所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任何海外華文作家也不可否定早年的地理記憶對于文學創作所產生的影響,甚至具有重要的意義。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少年記憶,而時間記憶與地理記憶是兩個重要方面,同時,時間記憶也不可離開地理記憶,因為地理記憶總是一種實體性的存在,而時間記憶往往是抽象的,如果沒有地理記憶,時間記憶就沒有依托。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時間記憶與地理記憶往往是一體化的存在,并且成為文學作品中的基本內容。每一位作家都會存在地理記憶的問題,然而海外華文作家特別是少年時代與楚地、楚風關系密切的作家,與一般作家相比就會有不同的表現。因為時間因素與空間因素會拉得越來越長、越來越大,地理記憶與時間記憶會變形,當它們進入特定的文學作品之后,所能夠爆發出的力量,非一般文學作品可以相比。雖然不能說海外的華文文學作品全都是浪漫主義的,然而在他們所創作的許多作品中,不論是詩歌還是小說,亦或包括散文和戲劇,浪漫主義色彩的確是比較深厚的,也許正是在于時間上的距離與空間上的距離,如果沒有距離則絕對是現實主義的。而由于移民海外而產生的比較廣闊的時間距離與空間距離,則讓作家的想象展開了巨大的翅膀,讓作家對過去生活的回憶、對人生少年時代的回顧,變得深情而美好。多數作家對過去生活以及生活過的地方的向往,特別是與自然山水環境相關的描寫,讓許多作品和作家都與浪漫主義產生了必然聯系。彭邦禎的詩歌絕對是浪漫主義的,他出生于湖北黃陂鄉下,解放戰爭后期去了臺灣,后來又去了美國,還與一位美國詩人結婚并生活了很長的時間,早年的地理記憶在他的詩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詩歌的形式、語言、詞匯、技巧等,與早年的楚地生活存在直接的對應關系。
二、地理感知與海外華文文學的審美意識
地理感知是地理記憶的來源,沒有地理感知就沒有地理記憶。當然,對于一位作家或者一般的個人來說,地理感知是與生俱來的,不需要經過特別訓練,雖然每一位作家的地理感知能力并不相同。地理感知作為文學地理學批評理論術語之一,意義重要。中國歷史上關于地理感知的論述是相當早的。陸機的《文賦》里就有與地理感知相關的論述,并且作了特別強調。《文賦》有云:“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3]揭示了文學藝術對客觀世界的依賴關系。四季更替,光陰荏苒,乃至萬物變化,都是文學作品內容的來源。作家對地理的感知是從事文學創作的基本條件。作家應該靈敏地感知自然萬物的變化,并從中捕捉到萬般思緒與感情變化。在時間上筆觸靈敏、思緒萬端,在空間上要有整體的把控,唯有如此,才能夠在整體的關照中更好地認知自然萬物。海外華文作家的地理感知,如果沒有其移民的經歷,與中國大陸本土作家之間就沒有什么區別。然而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變化,就是因為作家從原地出生又移民到異地事件的發生。海外華文作家與一般的作家在地理感知上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一個作家沒有比較豐富的地理經驗,一生去過的地方不多,或者行走的地方本來不少但缺乏對地理的觀察,或者對地理認知沒有很大的興趣,也不會因為地理感知的不同而發生重要的文學事件。如果一位作家在國內生活,他沒有移民到國外的經歷,然而喜歡去各國各地跑一跑,注重地理觀察與地理感知,那么地理因素對于文學創作的影響,就會特別顯著。海外華文作家對于地理的敏感度,也會因人而異、因時而異。然而,由于他們到國外生活產生了空間上的距離,同時也會由于生活得比較久而產生時間上的距離,對于他們的創作而言,就形成了雙重的距離,強度相當顯著,就會因此而導致一些文學現象的發生。這種文學現象的意義與價值,首先體現在作家的審美意識上。作家的審美意識,是對于表現對象的一種綜合性反映,是作家的主體與自然客體之間的對話,是作家的內在思想對自然客體的能動反映。從不同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審美意識,主要是由以下因素所造成的:第一是自我的民族傳統;第二是自我的家庭環境與家族遺傳;第三是自然環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地理感知。
地理感知與作家審美意識之間的關系,在海外華文作家及其作品中特別顯著。旅美作家呂紅出生于湖北武漢,在這里讀完了小學、初中與大學,并開始了文學創作,后來移民美國,繼續從事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的創作。在美從事創作期間,她又回到華中師范大學讀博士,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在武漢出生并長大,呂紅是一個標準的武漢女子。她對于人物與事件的認識,就帶有楚地與楚風的特色,從她的長篇小說《美國情人》、中短篇小說集《午夜蘭桂坊》等作品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她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一波移民潮中就到了美國,并且長期生活在美國西部大城舊金山,審美意識中又有了一些舊金山因素,熱情、開朗、精明、強悍。旅居新加坡的作家孫志衛,出生并成長于武漢,也是一位楚人。《武漢諜戰》是一部以抗戰為題材的長篇歷史小說,敘述1938年武漢淪陷之后,潛伏在敵后的軍統武漢特區和武漢特委組織,分別在李國盛和王家瑞的領導下,與日寇展開殊死的斗爭。小說以真實歷史事件為線索,將武漢當時的文化傳統及歷史遺跡自然地融合在故事情節與風景描寫中,具有鮮明、濃郁的藝術特色。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武漢的自然風光與風土人情的描寫,準確細致、生動形象,具有一種地理上的真實性和時代上的可靠性。地理因素在一個作家的審美意識中占有多大比重,因人而異。即使在現代交通便利條件之下,有的作家可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對于自然地理與人文環境沒有什么觀察與感知,有的作家則表現得相當突出。如果一個作家離開了大的環境,只封閉在自己的小圈子而了無生趣,如何能創作出杰出的作品呢?能創作出傳世作品的作家,總是敏感于自我的環境,包括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因為從文學的發生與起源而言,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內容總會有一個由外而內再由內而外的過程。沒有外在世界的激發,內心世界的成熟都沒有可能,還談什么思想的深刻呢?出生于山地的作家,其性格中往往會有比較高挺的一面;出生于平原的作家,其性格中往往會有比較開闊的一面;出生于盆地的作家,其性格中往往會有比較封閉的一面;出生于大海邊的作家,其性格中往往會有比較空靈的一面。一般來說在二十歲以前,作家的心智就比較成熟,也比較定型。何以為美?何以為丑?取向于正?取向于偏?喜歡男性風骨?喜歡女性風韻?大致已經有所設定。呂紅還是比較喜歡明朗一些的東西,而歐陽昱則比較喜歡晦澀一些的東西,這樣的風格,與他們從小就開始的地理感知具有一定的關系。所以,地理感知與作家的審美意識的關系不是一個偽命題,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作家的審美意識主要體現在文學作品里,作品的藝術風格來自于作家的審美創造,作家的審美意識之內涵與特點,與他從小所處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具有直接關系。出生于楚地的作家,自小生活在楚地與楚風之中,而楚地楚風總體而言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古老的楚國就具有崇火、崇鳳、崇巫的傳統,不僅在民間文化與文學中得到了保存,并且在屈原與宋玉等人的文學作品得到了保存。楚國的文化傳統基本上是浪漫主義的,在民族文化傳統中相當特殊,而海外華文文學里的湖北籍作家,也具有同樣的風韻與特征,其來歷與來源,可以從地理感知得到合理解釋。楚地并不具有統一的、固定的界線,現在的湖北與湖南肯定是楚國的腹地,其文化傳統具有代表性與典型性。因此楚地出生的作家,自小開始了自己的地理感知,與其他地方出生的作家就不太一樣。古老的楚地,大江、大河、大湖、大澤、大山、大谷,四周高山環繞,中間大河穿行,林木參天、江水流海、云蒸霞蔚,形成了楚地的特有風韻。作家受此地理環境與人文風骨的感染,在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就會通過自己的想象、語言、藝術體式、藝術技巧等融合到文學作品中來。旅美詩人彭邦禎的系列詩歌與散文作品,是海外華人文學的重要部分。雖然他一生到過許多地方,包括中國臺灣、美國、東南亞國家、法國、英國、德國等,然而他的審美眼光與審美趣味主要還是受到楚地的影響,早年生活所積存起來的地理感知及其內化經驗,讓他的詩歌想象豐富、空間闊大、情感洋溢、語言華美、長于鋪排、氣勢宏大,形成一種不可阻擋之勢,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楚人的祖先敢于到周天子那里問鼎中原,三年不鳴而一鳴驚人,向往來自天上并不存在的九頭鳥圖騰,形成了深厚的浪漫文化傳統,而這些特性在彭邦禎、聶華苓、呂紅等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中,得到了相當的繼承與發展。沒有當年對于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全方位感知,就不會有這樣的審美情趣的形成及其審美意識形態的產生。地理感知是地理記憶產生的基礎,而地理記憶則可以成為審美意識的主要內容。因此,對于楚地的觀察和對于楚風的感知,往往轉化為他們文學作品的思想與情感,體現了作家獨有的審美意識形態,成為海外華文文學浪漫主義的內在證明。
三、地理思維與海外華文文學的空間建構
地理思維同樣是來自于地理感知,如果沒有長時間的地理感知,不僅少有地理記憶,也不會有地理思維的完整建立。地理思維是指建立在地理基礎上的思維,或者說以地理為主要對象和重要內容的思維。一個人有沒有地理思維,首先是看他有沒有空間感,其次是看他有沒有地方感,再次是看他有沒有方位感。如果一個人的思維中沒有這三個層面,或者三個層面的東西都比較弱,地理思維就是缺失的、不完整的。當然,一個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哪個地方的人,完全沒有地理思維,也是不可能的。一個人不知道一個城市或一個地方的東西南北,完全沒有方位感,只是缺失了一定的地理意識。地理思維是指在一個人的心目中有了地理概念,有了比較明確的地理觀念與地理意識。如果一位作家對于自己的出生地周圍一百公里范圍內的山脈與河流,進行過不止一次的實地考察,如果一位作家到過除出生地之外的五個以上的地域,并且對于每一個地方的地理形態有所感知與認知,就具有了比較明確的地理意識,同時也具有了比較強大的地理思維。如果一位作家到過除自己出生地之外的世界上三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并且對于所到國家或地區的各種地理形態比較敏感,他就會具有明確的地理意識和地理思維。為什么呢?因為在他的身上,空間距離會對其意識與思維發生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在海外華文作家那里,地理思維的擁有是不存在問題的。因為他們從自己的出生地、成長地,來到了自己的發展地,而他們現在的發展地,就往往是其文學作品的寫作地。因此,許多海外華文作家的空間感與地方感是比較強烈的。時間的距離越大,空間的距離就越大,在這樣的時間與空間中作家展開自己的審美過程,創作出自己的作品,就有別于國內作家。歐陽昱出生于湖北黃州,旅居澳大利亞多年。他的英文長篇小說《東坡紀事》,敘述一位海外華人回到故鄉時的所見所感,對黃州自然山水的描述是大量的,對家鄉面貌及其變化的敘述是顯著的,對家鄉當年那種落后、貧窮現狀的反思,給人以許多重要的思想啟示。在歐陽昱大部分作品中,源于時間與空間距離所產生的意義是相當明確而顯著的,不論是寫湖北黃州過去的生活,還是寫自己在澳洲的生活,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對于其藝術想象與審美構想,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表現出明確的地理思維。出生于湖北武漢的周愚,許多作品是寫華人在美國的生活,然而對江漢之間的地理環境相當熟悉,包括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地理思維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開始完整地建立起來的。如果沒有江漢大地的開闊與神奇,如果沒有長江漢水的浩蕩東去,其作品就不會有那么宏大的氣象與繁復的結構。早年形成的地理思維也因為他移民美國產生了重要的變化,然而這種變化是由于時間的距離與空間的距離而發生的。在進行藝術想象與審美構想的時候,橫跨太平洋的空間與橫跨中西文化的時間,都會產生重要的意義。從中國到北美、到澳洲、到歐洲,從過去到現在,從歷史到現實,一個作家的地理思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許多時候都是決定性的。并不是說沒有地理思維就不可以從事文學創作,然而沒有地理思維而創作出來的作品,恐怕就沒有具體的空間感,或者空間感弱小,對文學審美與文學閱讀會造成很大的限制。對理論問題的思考也不可離開具體的文學現象,特別是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文學現象。海外華文文學作品之所以與中國本土作家的作品有所不同,地理思維是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一個是本有的地理思維,一個是處于海外的地理空間,絕大部分文學作品的空間形態就特別顯著。彭邦禎詩歌《月之故鄉》里的意象,“天上一個月亮,水里一個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不是一種想象而是一種寫實。還有如《花叫》這樣的華麗之詩,正是一種當代的楚辭:“而春天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天空說藍不藍,江水說清不清,太陽說熱不熱。/總是覺得我的舌頭上有這么一只鷓鴣,/不是想在草叢里去啄粒露水,/就是想在泥土里去啄粒歌聲。//叫吧,凡事都是可以用不著張開嘴巴來叫的。/啊啊,用玫瑰去叫它也好,/用牡丹去叫它也好,/因而我乃想到除用眼睛之外還能用舌頭寫詩:/故我詩我在,故我花我春。”[4]浪漫的情思、瑰麗的意象、出人意料的想象,貫穿全詩。在他所創作的系列作品里,詩人以自我的情感為基礎,想象奇特、空間獨立,與楚國的自然山水之間產生了必然的關聯。顯然,這樣的作品是具有浪漫主義精神的,因為它們產生的基礎是自然地理,并且是在自然地理基礎上所形成的強大地理思維。
四、空間與時間和海外華文文學的總體格局
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完全不同于中國大陸或臺港地區作家的文學作品,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體現在嚴歌苓與張翎的作品中。他們的文學作品視野開闊、思想深刻、格局宏大、藝術精湛,即使寫唐山大地震的作品,寫20世紀早期美國華人底層生活的作品,寫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新移民現實生活的作品,思想與藝術創造也十分明顯。就他們自己而言,為什么他們在國外的文學表現,與他們早年在國內的文學表現有如此大的區別?為什么在移民之前與移民之后的文學表現,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不是因為他們的思想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也不是因為他們在藝術上得到了多大的提升,主要是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與環境,與中國大陸過去的生活拉開了很大的距離,一個是時間上的距離,一個是空間上的距離。不要小看這樣的距離,它對作家的審美意識與在創作時的藝術構想,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以至于可以改變一些根本性的東西。從海外回望中國,很容易是全景式的,當然,也可以是局部性的。他們的藝術視野可以縮小再縮小,也可以擴大再擴大,收放自如,選擇的余地很大。所以,文學作品在藝術構想上往往格局很大,同時也有很細小、很深入的地方,感人至深。從現在回望過去,多少年以前的東西都可以回到眼前,并且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明確,可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筆者出生于四川盆地中南部倆母山地區,二千平方公里的穹隆地區。小時候生活在當地,許多事情都看不明白,而當我來到江漢之間,在近40年后的今天,所有的事情都看得相當明白,大部分文學作品的主要內容都來自于對那個地區的人、物、事的重新審視①。如果沒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距離,許多作品也許就不會產生,因為不會有獨特的感覺與獨立的認識。而海外華文文學作家,他們與故土之間的時間距離與空間距離比筆者與家鄉的距離要大得多,時間與空間對于他們所產生的影響,可想而知。張翎從加拿大回過頭來看幾十年前發生的唐山大地震,嚴歌苓在美國回過頭來看“文革”舊事,格局就完全不一樣了。有的人可能會說可以想象,把自己置之度外,似乎是在海外之類的,其實這樣的想象是沒有用的。一個作家的創作產生于什么樣的真實生活,如果想象可以解決根本性的問題,那就不需要我們再來討論時間與空間。程寶林從中國去到美國,從美國的角度來回顧從前在江漢大地的生活,時間讓他產生了美好的情懷,空間讓他產生了闊大的視野,在中國所創作的作品與到了美國之后所創作的作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就是一種格局的變化:一是集中于某一方面的題材,二是集中于某一類人物,三是想象的成分加重了,四是對于過去的人與事之性質看得特別清楚。閱讀這樣的作品,浪漫主義的情懷左右了讀者的視線。從表面上來看,每一個作家藝術格局的大小,與時間、空間不會有很大的關系,倒是與自己的人生經歷與見識有關,但關鍵就在于海外的華文作家天然地具有這樣的經歷與見識,并且由于空間的拉大,讓時間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距離產生美,并且距離產生大美,產生更加豐富、更加特別的美,是中國本土的作家所不具備的,這就是地理基因在文學創作中所生發的重要意義。海外華文文學在改革開放40年時間里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一流作家越來越多,杰出作品也越來越多。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每一次會議,我們都可以看到許多海外華文作家的身影,同時也感受到他們對于文學的極大熱情,這與他們的移民身份有很大的關系,當然也與他們所在國的社會環境有直接的關系。地理上的空間距離和時間距離以及時間上的地理距離和空間距離,對于他們而言是需要直接面對的,每一天、每一地,都是如此。因此,他們的創作格局與從前在中國大陸的時候相比,就更加宏大、更加深厚,并且總是有一種文化上的比較與歷史上的混雜,也容易產生對于相關的哲學與美學問題的思考。
五、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浪漫主義
楚地的特點、楚文的優勢與楚風的傳統,與海外華文文學之間也具有重要的聯系。許多作家與學者一生都生活在江漢之間,楚國的腹地,是楚文化的核心區域。楚地的特點是南北東西大山,幾條大河四面奔來,皆從武漢流出,而直至長江下游的廣大地區。上游的長江、北來的漢水、南來的湘水,以至于所有的江河都流過江漢平原,滋養了長達五千年歷史的楚文化與楚文學。這里的地理環境特別,古之云夢大澤,今之洞庭大湖,以至于湖北的千湖與武漢的百湖,都不是沒有意義的名稱。自古以來,雖然自然地理環境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然而云蒸霞蔚、湖光山色、猿嘯山林、漁舟唱晚的基本格局,并未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雖然填湖很多,森林砍掉不少,然而這些年來退田還湖、退耕還林政策的落實,自然環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山環水繞、山水相濟、森林密布的基本格局,仍然在對這里的文化與文學發生作用。正是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之中,楚風、楚俗之特別,自然而然;楚地多巫風、信鬼神,自古而然。在湖北與湖南的許多地方,儺戲的傳統還是保留了下來,并且在最近一些年來,又有了很大的發展。對于人的生老病死,地方上有一整套的儀式,不會因為時代的變化而完全丟掉,在這種儀式中往往都伴有鬼神色彩,是中國人古老的信仰所致。同時,地方信仰的范圍還是相當廣泛的,一個小小的地方都會有自己的寺廟,對于山、水、樹、石、溝、谷、火、鳥等,都會有所信仰,稱之為神。如果說到楚文,那么它與楚地、楚風是密切相關的,楚文是對于楚地、楚風的文學與藝術的表達。所以,浪漫主義的精神與氣度,在楚文化與楚文學這里就是自然而然的,似乎也沒有人故意地要去追求,或者專門進行打造。楚文化的傳統就是浪漫主義的,浪漫主義這個詞雖然來自于西方,但對于楚文化與楚文學而言,是比較恰當的一種歷史概括。我們從戰國編鐘、青銅器、漆器與臺榭的風格中,從屈原、宋玉的辭賦中,都可以得到切實的證明。
這樣一種相當的浪漫主義精神,是不是被湖北作家帶到了海外,并且在海外華文文學中得到了保存與發揚?根據筆者有限的閱讀,可以肯定的是,從湖北去到海外的作家的作品,的確顯示出了與其他地方作家不一樣的藝術風格與美學追求。我們可以從聶華苓、王默人、呂紅、歐陽昱、歐陽海燕、張勁帆、程寶林、楊恒均、彭邦禎、孫志衛等人的作品中,找到有力的證明。彭邦禎的大部分作品,其文辭的華美、情感的真摯、想象的豐富與藝術上的大起大落,與屈原的浪漫主義文學是一脈相承的。程寶林的散文主要寫其少年時代在老家的所見所聞,在對于楚地、楚風的記錄中,體現的也就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情懷。聶華苓、孫志衛等的小說,對于情的表現和對于景的營造,與楚地文風是完全相通的。其他地方出生的海外作家,就少有或沒有這樣的特點。嚴歌苓出生于上海,所以其作品就不是浪漫主義文學,而是以現實主義風格為主的。張翎出生于浙江溫州,她的作品也不具有浪漫主義風格,而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兼具。所以,楚地出生的作家與詩人,雖然他們的作品也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大體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超強的想象力、空間的開闊性、文辭的典雅華美、激烈不已的文風,這就是楚地、楚文和楚風給他們帶來的獨到的東西。
海外華文文學是一種極其獨特的存在,無論從生存方式還是從其本質而言,它們都是外國文學的一個部分,而不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部分。就像中國也有英語、法語文學一樣,我們沒有把這樣的文學當成外國文學,而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因為作家生活于、工作于、創作于哪個國家,就屬于哪個國家的文學,從其性質而言,它們是中國文學向海外的一種延伸、一種擴展。海外華文文學的構成與發展,與中國本土的地理與文化具有很大的關系,因為作家是從中國出去的,并且在中國留下了重要的生理與心理的烙印。本文從地理記憶到地理感知,再到地理思維與地理時空,以文學地理學批評理論術語為工具,分析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特點,特別是出生于湖北的作家在海外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從邏輯上而言是嚴密的,從根據上來說是可靠的。海外華文文學中存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傾向,其中的浪漫主義傾向的確與楚文化的浪漫主義傳統有著重要的關聯性,具體體現在從湖北出去的一些作家作品上。在今天的世界,移民文化是一種值得探討的重要文化現象,通過對海外華文文學作品的分析與對海外華文作家的探討,說明一種傳統文化的移植是可能的,文化在另一個空間的發展也是可能的,但與原生地的自然形態與內在影響也是不可分割的。海外華文文學的構成與發展,正是世界各國移民文學產生與建構的典型標志。
注釋:
①十五年以來,筆者創作了散文八十篇、賦一百篇、十四行詩九百首、擬寒山體七百首,至少有一半作品的題材和人物來自于早年生活和反思早年所見所聞。參見鄒惟山:《時光的年輪——鄒惟山十四行抒情詩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鄒惟山:《鄒惟山十四行抒情詩集》(長江出版社,2012年版);鄒惟山:《鄒惟山十四行詩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