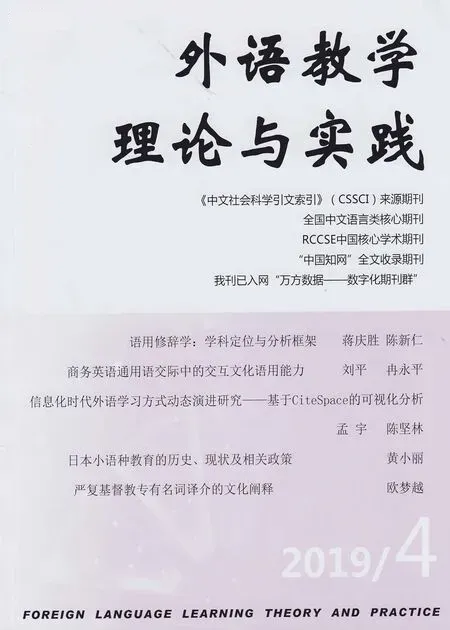商務英語通用語交際中的交互文化語用能力*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劉 平 冉永平
提 要:商務英語通用語(BELF)交際受到商務機構和多元文化語境雙重制約,語用能力在資源利用及知識建構方面有獨特性。本研究從單語言、單文化到多語言、多文化發展變化的角度,梳理商務語境下的語用能力,討論交互文化語用能力的概念,旨在對BELF交際中的語用能力重新概念化。在探究BELF的四大特征后,基于實例分析,發現BELF交際中交互文化語用能力體現為以完成任務為取向的語言資源利用,以及以尋求與創造共知基礎為取向的交互文化建構。
1.引言
商務英語通用語(business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簡稱BELF)指商務交際中母語非英語的交際者,為完成特定任務,選擇英語作為共享交際代碼進行的語言使用(參見Louhiala-Salminen等,2005:403-404)。BELF研究吸收跨文化商務交際學和英語通用語(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ELF),并已有成果。它質疑傳統應用語言學和跨文化交際研究中存在的偏見,不再認為文化差異和非母語者對交際具有消極影響(Charles,2007),而是把語言文化差異當作可用資源。BELF研究還把交際的有效性、適當性與商務機構特征結合起來,強調意義的表達與理解產生于個體參與的交際互動中,在此過程中,交際者選擇英語,甚至創造性利用各自的母語文化知識,通力合作,建構共知基礎(common ground),達到交際目的(Kecskes,2013;武繼紅,2017)。
伴隨BELF使用場合和機會的增加以及對其研究的深入(Murata,2016:1),學界對BELF本質的認識達成一定共識。BELF研究不再專注單一“霸權”英語,而關注在不同交際情景下的英語變體和相對頻繁出現的語法和句法特征(參見Murata,2016;Mackenzie,2014)。最早進行BELF研究的Louhiala-Salminen等(2005:403-404)指出,BELF沒有固定使用者,具有中立性和共享性。也正因為此,BELF與其他場合使用的ELF一樣,不存在實體,而是扎根于不同文化互動中的一種語言實踐活動、功能或交流模式(Mackenzie,2014;Kecskes,2015;冉永平,2013),具有高度的動態涌現性(Kecskes,2013)、特異性、包容性和混合性(Kankaanranta &Louhiala-Salminen,2013),然而目前對這些特性在商務情景中的表現揭示不夠。
針對具體商務場合下的BELF交際,前人有的探討不同商務活動中策略與技巧的使用及效果,如商務談判(如Planken,2005)、會議(如Pullin,2013)、廣告(如Nickerson &Camiciottoli,2013)、電子郵件(如Millot,2017)、年度報告(如de Groot,2008)等;有的從宏觀上探究交互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Kecskes,2013;Zhu Hua,2014)和交互能力(interactional competence)(Kecskes等,2018);有的專注BELF中的具體問題,如理解與誤解(如Pitzl,2012;2015)以及語言使用對人際關系的影響(如Millot,2017;Pullin,2013);還有的考察制約話語產出和理解的不同語境因素(如Nickerson,2015)。總體而言,從交際效果看,盡管BELF交際受到多元文化和商務機構語境的制約,然而交際中出現曲折比預期要少得多(參見Pitzl,2015:95)。ELF,包括BELF交際,與其他任何人際交際一樣既有成功也有失敗(Kecskes,2013),因此,交際者語用能力的特征和表現值得深入探究。
以往對BELF中語用能力的研究多采用靜態視角,把它看作包括多元文化知識、商務知識和全球交際能力等的靜態知識(Kankaanranta,2010;Kankaanranta &Louhiala-Salminen,2013),語用能力的發揮受到文化背景知識和語言水平的影響(Du-Babcock,2013),研究多致力于比較不同文化背景交際者的差異(如Kankaanranta &Lu,2013)。然而這些研究未能揭示語用能力的動態性和涌現性等特征。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在多維視角下對語用能力重新概念化,然后在描述BELF機構特征的基礎上,探究BELF交際者交互文化語用能力的表現,旨在增加對BELF交際特征及其機制的認識。
2.交互文化語用能力
語用能力的概念源自Chomsky(1965)對語言能力與語言行為的區分。前者指語言知識或內在語法,后者指具體語境中語言使用。在談及語言使用的意圖問題時,Chomsky(1980:59)指出語言行為承載著使用語言知識達到某一目的的能力,也即語用能力,是“了解語言如何與其使用的情景相關聯的能力”(Chomsky,1980:225)。從應用語言學角度,Hymes(1972:281)提出更為寬泛的交際能力與交際行為,前者指語法能力與社交語言能力,后者指語言的實際使用能力。Canale &Swain(1980)則認為交際能力包含語法能力、社交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可見,語用能力屬于社交語言能力范疇,具體指語言形式的正確性及所表達意義的恰當性(冉永平,2006:48),可進一步細分為語用語言能力和社交語用能力(Leech,1983;Thomas,1983)。前者指在特定語境中正確使用語言形式以實施某一交際功能的能力,后者指遵循語言使用的社會規則進行得體交際的能力。
跨文化語用學(cross-cultural pragmatics)對語用能力的探究多采用靜態視角發現和描述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際者在語用語言能力和社交語用能力方面表現的異同(參見Thomas,1983),加深對多語言和多文化背景下語用能力認識,但無法揭示交際中語用能力的動態性特征。此外,研究專注交際沖突和失敗的現象,把偏離目標語的語言使用視作“錯誤”或“語用失誤”(Boxer,2002;Thomas,1983),試圖發現語用原則和準則在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遵守和違反程度,從而了解其普遍性(如House,2000;Thomas,1983;Wierzbicka,1991,2003),旨在“提升對語言交際中語用語言現象和社交語用現象的解釋”(何自然&冉永平,2009:92),避免交際失敗。然而,許多學者對此提出異議(如Lantolf,2000),認為跨文化語用對語用能力的討論存在“單語化偏見”(monolingual bias),將本族語者與非本族語者相對立的區分以及以本族語為標準的思想也存在缺陷(Firth &Wagner,1997)。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對文化差異的對比是在國家文化層面上進行,多以靜態視角把語用能力看作某種知識或以某種知識為前提的能力,并假定靜態的知識與特定功能和語境相匹配,那么一旦擁有某種知識,就能進行得體交際。總之,跨文化語用學的思想和研究不能有效揭示交際中意義建構的動態性和涌現性,也忽視了語用能力在亞文化群體和不同交際個體層面的差異。
鑒于此,針對ELF背景下語言使用的交互文化語用學(Intercultural Pragmatics)(Kecskes,2013)從跨文化語用學和語際語語用學(Interlanguage Pragmatics)中獨立發展起來,重新審視多元文化交際中的語用能力。其創始人Kecskes(2013)聚焦社會文化因素和交際主體的個人意愿或偏好對語用能力的影響,探尋雙語和多語環境下語用能力的表現與發展。此外,交互文化語用學對語用能力的研究不僅重視語言手段和語用策略的選擇(Bj?rkman,2014;Cogo &Dewey,2012),還重視交際者在特定語境制約下對交際內容和過程的調解和相互協同(Baker,2011)以及和諧關系管理能力(Pullin,2013)。
交互文化語用學視角可以揭示BELF交際中語用能力的獨特性。在該視角下,英語本族語者的語言范式和社交規約不再是衡量和評判語用能力的標準,即語用能力不再體現為一種自上而下的靜態規約性能力,而體現為交際互動過程中自下而上涌現的、混合的復雜系統。冉永平和楊青(2015,2016)探究ELF背景下語用能力的重構,認為語用能力體現為特定語境下語言選擇、信息建構、關系管理等多元語用能力。本文把這種多元語用能力重新概念化為交互文化語用能力(intercultural pragmatic competence),具體指來自不同語言文化的交際者,選擇英語作為媒介進行交際中所體現出的在語言資源選擇與利用、信息建構、關系互動、文化和背景知識的調節和適應等方面的能力。該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凸顯交際者選擇的語言手段與語境之間動態調節的適應性和創造性,以及不同文化之間互動融合產生的交互文化性。
3.商務英語通用語的機構交際特征
首先,合作共贏是BELF交際的首要目標和共識。從所有權看,BELF使用具有中立性和共享性,因為英語不屬于交際中任何一方,其成員是獨立的語言使用者,不再是與本族語者相對的所謂非母語使用者或外語學習者,他們使用英語具有很強的目的指向性(goal-oriented)。交際者通過協同合作,高效完成任務是交際的首要目標(Kankaanranta &Planken,2010:381),在此過程中信息傳遞是否有效,任務是否完成是衡量成功交際的關鍵(Firth,1996;Kecskes,2013)。同時,由于母語文化背景不同,交際者之間缺乏集體共知基礎(Kecskes,2013),英語水平也很可能參差不齊,BELF交際往往要花費更多時間表達同樣思想(參見Hincks,2010),然而在共同目的和利益驅動下,當信息交流受阻,會設法利用各種資源尋求和建構涌現(emergent)共知基礎(Kecskes,2013),設法成功交際(參見Cogo &Dewey,2012;Mauranen,2012;Seidlhofer,2011)。據研究,以英語為工作語言的國際會議總體上是“有意義的、井然有序的、和諧的”(Rogerson-Revell,2008:349),交際在相互協調、競爭、調整和再協調過程中涌現為各種動態表現和多元化融合(Baker,2015:53)。當然,BELF交際以完成任務和信息傳遞為取向并不意味著人際關系不重要,與其他任何人際交際一樣,BELF同樣關注和諧關系的建立與維持(Pullin,2013),很多時候甚至表現出更高程度的相互理解、包容和支持(Kankaanranta &Louhiala-Salminen,2013),只是關系管理一方面出于對彼此相似境遇的同理心,更多是為完成任務。此外,交際中也存在競爭(參見Angouri,2012),因為商務交際,特別是談判和協商一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沖突。
其次,BELF注重交際效能及各種資源的共享與利用,甚至創新性利用。英語在BELF交際中是實現商務溝通的工具,不再是一門需要學習和掌握的外語,交際者不需要,當然也不太可能完全遵守英語母語規范,即使對規范有所偏離或違背,也不會被視為語言能力不足或交際失敗,因為英語在此交際語境中使用的重點在于其功用性,而不是形式的準確性(Kecskes,2015)。除傳統的直接、明晰策略外,他們還創造性利用語言資源,努力傳達信息,并隨時根據交際對象的語言水平和專業背景調整語言使用,旨在建構和擴大共知基礎。因此,BELF研究不再致力于識別英語變體的共核特征,而是探究交際過程的功能性、多元互動性(Kecskes,2013)以及創新性(Pitzl,2012),即關注不同母語背景的商務交際者如何相互協調適應,容忍甚至利用多元文化差異,提高效率,完成任務。
此外,BELF交際過程具有不確定性和涌現性。BELF參與者一般具有很大流動性,他們為某一特定任務和目的建構臨時言語共同體,可能將各自母語文化的影響帶入其中,因此交際過程充滿不確定性(Kankaanranta &Louhiala-Salminen,2013),會涌現出既不完全等同于交際者自身母語文化,也不等同于英語文化的臨時性知識,即交互文化(interculture)(Kecskes,2013),這是多元文化之間互動的必然結果。交互文化的產生說明BELF交際者的流動性,文化的多元性和交際過程的動態性成為一種交際資源,為來自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英語使用者呈現或凸顯自我文化提供了新的語境空間(冉永平&楊青,2016)。當然,某個言語共同體在交流互動中完全有可能形成相對穩定的群體規范(group rituals),規范性程度取決于BELF交際者共同參與的跨國商務活動、共同的行業知識和雙方建立業務關系的時間長短(Kankaanranta &Planken,2010)等因素,但一旦該群體解散,這些建立起來的群體規范也將隨之消失。
最后,BELF交際體現機構權力或角色任務分配的不均衡性。與日常ELF相比,BELF具有顯著機構特征。在會議協商、談判等活動中,會議主席或部門領導對日程與話題安排,意義澄清與內容總結,會議起始與結束等具有更多權力與責任(Handford,2010等)。這種不均衡性除了由于機構角色不同外,還與對BELF的語域特征的掌握,商務背景知識的共享程度以及在崗時間有關(Louhiala-Salminen等,2005:391),主要體現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前者主要包括專業背景知識和語言水平;后者包括機構權力,人際關系史,語言表達能力和策略能力以及文化背景差異等。
4.商務英語通用語交際中交互文化語用能力的體現
1)以完成任務為取向的語言資源利用
BELF交際中交互文化語用能力在語言資源利用上體現為以簡單、直接和明晰為主,并有一定程度的創造性或創新性。如前所述,BELF交際主要以完成任務為取向,由于交際者英語水平不一,較少使用本族語者經常使用的慣用語、習語、諺語、情景限定語(situation-bound utterance)等程式化表達,即使使用,也存在形式的準確性與用法的適當性問題。雖然這些表達受到本族語者的偏愛,恰當使用可以提高交際效率、流利度以及本族語相似度(nativelikeness)(Kecskes,2013),但因為它們大多承載特定的社會文化知識,成分具有不可分析性,語義具有不透明性,容易造成理解困擾和記憶偏差,影響意義的表達與理解。有研究發現,實際上,BELF交際者并不期待對方擁有熟練的英語語用能力,這被認為不切實際(Charles,2007等),交際成功的關鍵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英語語用語言及社交語用規約,而在于各方是否能達成共知和互解,即使使用偏離英語規范的表達。
在商務機構語境制約下,為完成任務,BELF交際者時常創造性使用語言資源。這種創造性或創新性一般是臨場為了維持持續交流的一種“生存機制”(survival mechanism)(Carter,2004:98),不是蓄意而為之。Pitzl(2012)把ELF使用中的創新分為有意(intentional)和無意(unintentional)創新以及規范遵循(norm-following)和規范發展(norm-developing)(Pitzl,2012:30,32)。語料分析發現,BELF中的創新多屬無意創新,是一定程度上規范的發展或變異。下面的例子來自VOICE語料庫(括號中是英語規范用法):carved in stones(carved in stone);pieces by pieces (piece by piece);sit in the control of (be in control);in the right track (on the right track);remember from the head (off the top of your head);a bigger share of this pie (a slice/share of the cake/pie);two different sides of the same coin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在跨文化語用和中介語語用研究中,這類偏離規范的用法被認為是錯誤的,但交互文化語用學認為這是創造或創新,體現交際者的交互文化語用能力,雖然動機很可能是為了臨場填補詞匯和語義表達空白。在方式上,以上例子顯示,新的形式部分偏離規范表達,然而語義普遍變得更加透明,成分更具可分析性。下面看一個交際互動中的例子。
例(1)(S1和S2,韓國人,物流經理,S1年長;S3和S4,母語為德語的奧地利人,S3,銷售人員,S4,銷售經理。)

雙方在討論各自公司的上班和休息時間。當S1用“bi-bi-e:r takes off”時,S4似乎對此沒有理解障礙,盡管英語中不存在該搭配,屬于臨時創造的結構。交際中有關工作日和周末休息的集體共知,以及現實情境語境中有關兩國工作日和周末安排等信息為理解該搭配提供背景和線索,此外“bi”和“take off”的字面意思分別是“雙,兩個”和“休息”。這些共同創造了涌現共知基礎(Kecskes,2013),確保交際順利推進。BELF交際中的語言創造性體現為語言結構構成成分的可分析性和詞語搭配的臨時性,因此意義的表達和理解多基于字面意義,并具有較強的語境依賴性。
2)以尋求和創造共知基礎為取向的交互文化建構
BELF交際中交互文化語用能力體現為在共知基礎尋求和創造過程中涌現的交互文化。交互文化和交互文化性是Kecskes(2013)在語用學研究的社會-認知視角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交際中不同語言文化的互動和融合的過程與結果。交互文化指交際者基于已有的文化背景知識和臨時涌現的情景因素共建的臨時性知識。交互文化性則是包含相對固定成分和臨時涌現成分的臨時性知識系統。交互文化具有動態融合性,不是靜態的知識或技能,不是某個言語社區語言文化知識的單向傳播,也不是不同文化的交際范式和規則的簡單組合與呈現,而是交際者在共知基礎建構中創造的涌現知識。
共知基礎指“人們共享的包括世界觀、價值觀、信仰和情景語境在內的所有信息總和”(Kecskes,2013:151),分核心共知和涌現共知。前者是針對某一語言社區而言,相對靜態的(歷時變化的)、普遍的、共有的知識,包括常識、文化意義和形式意義(Kecskes &Zhang,2009);后者是針對交際個體而言,在交際過程中建構的,由現實情景語境觸發,相對動態的、特殊的知識,主要包括交際者之間共享的個人經歷和交際者對當下情境的判斷和看法。這兩種共知在交際中相互作用且互相轉化。BELF交際者之間缺乏核心共知,因此更多尋求和創造涌現共知,在此過程中涌現的交互文化主要是相關的語言文化和商務背景知識。下例中與會者就展示材料中英語單詞“gullible”的意思進行討論和協商,涌現出與該詞相關的交互文化,在共同努力下最終創建了理解該詞的共知基礎,體現交互文化語用能力。
例(2)(S1,S2,S3和S4的身份見例1中背景介紹,S5和S6是母語為德語的奧地利人,S5是銷售助理,S6是研究者)


這段互動大致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開始到2288行,S1先提出話題,確定討論內容,就展示材料中出現的“gullible”一詞,S4表示從未聽說過,于是大家各自表達對該詞的了解,一同努力,尋求和嘗試創造共知基礎。S1聽說過該詞,但不確定其含義,其他人都表示不清楚該詞的意思。在語言知識方面,S1似乎具有專家權(expert power)(Thomas,1995),此外S1也比S2資深,表現出更大的機構權力和責任意識,一直主動引導和推動討論進行,體現商務機構交際中不均衡權力的制約。S1嘗試用元語用話語“gullible means not English word”推測該詞意思,認為可能接近“greedy”,其他人隨聲附和,并無異議,有關該詞的共知基礎開始創建,此階段涌現的交互文化是:該詞不常用,可能不是英語單詞,詞義接近“greedy”。
第二階段從2288到2309行,與會者繼續創建共知基礎。S4和S6積極配合,都表達了想知道該詞意思的態度和立場,出謀劃策,鼓勵S1繼續猜測,體現與會者和諧關系維護的意圖和努力(參見Pullin,2013)。同時,S1多次使用元語用表達明示不確定性和主觀性,調控和管理意義的表達和理解以及試圖弱化責任,維護面子,如“i’m bit confused”,“i’m not sure”和“if i’m correct”,體現自返性和自我監控意識(Verschueren,2000)。在此階段涌現的交互文化更新為:該詞的詞義可能是“greedy”或者“easy to be deceived”。
第三階段從2310行到最后,共知基礎創建完成。S1首先對gullible可能意思是“easy to be deceived”提出質疑,用疑問句“why”試圖澄清理解(Pullin,2013:5),提出為什么要欺騙孩子。S5試圖解釋,S4再次提議查字典。這時S1再次修改為“easy to be influenced”或“easy to be deceived”,S2和S4對此都表示同意。此外,S1從材料的上下文找證據證明這次是正確的,并為之前沒有解釋清楚道歉,當S4再次提到從未聽說過該詞時,S1用“it’s a bit American”解釋原因,其中模糊限制語“a bit”可以緩和主觀性,并修正之前“not English word”的說法。在此階段涌現的交互文化是:gullible是美國英語用法,意思是“easy to be influenced”。到此為止,經過與會者合作努力終于完成建構有關該詞的共知基礎。
以上互動中交互文化語用能力體現為選擇適當的語言手段和策略調節信息的產出和理解,同時關照和協調人際關系,利用交際中涌現的交互文化創建共知基礎,完成任務。在機構權力和語言文化背景知識的制約下,交際參與者的作用和貢獻不同。來自韓國的S1(資深經理)和來自奧地利的S4(銷售經理)引導討論方向,主導交際進行,在共知基礎的創建過程中是主要和直接參與者。S2和S3象征性地參與交際,雖然對信息內容沒有實質貢獻,但對各自的上級,即S1和S4的發言隨時回應并表達支持,體現參與共有基礎創建的積極態度以及對人際關系的協調能力。級別較低的S5和旁參與者S6只是偶爾插話,參與程度最低。最終有關英語單詞“gullible”的用法和詞義的共知基礎創建完成,期間涌現的交互文化為:該詞不太常用,是美國英語用法,用在商業廣告中意思是“easy to be influenced”或“easy to be deceived”。
5.結語
相比單語言和單文化交際語境,BELF交際在交際目的、資源利用、知識建構、交際過程等方面的商務機構特征制約交際進行,同時也為交際提供供用性。在交互文化語用學視角下,本文提出交互文化語用能力的概念,試圖對BELF交際中的語用能力重新概念化,以凸顯其動態涌現性,并以VOICE語料庫中的實例分析語用能力在語言資源利用和知識建構方面的表現。分析發現,在資源利用方面,BELF交際多使用簡單、明晰的表達方式,并創造性利用可用資源設法交際;在知識建構方面,交際者在商務機構和多元文化語境制約下,選擇適當的語言手段和策略建構交互文化,創造涌現共知基礎。對BELF機構交際特征以及交際中交互文化語用能力表現的探究提升對商務機構情境下多元文化互動的認識。然而交際中涌現交互文化的類型和主要特征以及參與者受到的語境制約如何影響交互文化語用能力的表現等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