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靈魂的弦歌
余孟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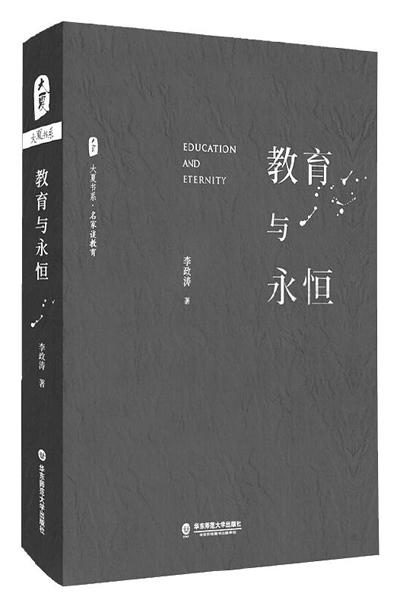
看慣了那些長篇累牘、鴻篇巨制式的教育學著作,當我拿到李政濤教授的《教育與永恒》一書時,如遭遇了一場難得的漫天飛雪,那些簡短細膩的語句,正如一片片晶瑩剔透的雪花,純凈、美好、耀眼。
在我們的印象中,李政濤一直是一位專業的教育理論研究者,他的《表演:解讀教育活動的新視角》《教育科學的世界》等著作以及大量的學術論文,都嚴謹、規范、系統、深刻。然而,他為什么又會出這樣一本隨感集?他在序言中說,是周國平的靈思火花點燃了他對教育和永恒的思索,才有了這部“教育靈魂的私人記錄”。
追問自己是否配得上從事教育
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30年后,我依然記得1989年的某個冬夜,那具從未豐腴過的肉身,蜷縮在贛南師院那間凄冷的教室里手抄此書時的場景:窗外是茫茫黑夜,沉寂如鐵,我的內心交織著澎湃與安寧,這是一種奇妙的矛盾的交融……”這段“真情告白”深深地觸動了我,于是我在書的空白處寫了這樣兩句話,一句是:“一個人的成功絕不是無緣無故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早在30年前就埋下了種子。”另一句是:“真正的聰明人,其實都是下笨功夫的。”
《教育與永恒》整本書都是靈魂的私語、直覺的捕捉和生命的體悟。與其說作者是把教育放在人生中、時代中、自然中、社會中、學校中、家庭中去感悟、品味、追問和沉思,不如說作者是以教育為靈魂和眼光,去看待人世滄桑、天地萬象。作者對自己靈魂的叩問,尤其令人動容:“我的靈魂,是否配得上從事教育?我的精神生活,是否配得上從事教育研究?”這是對自我生命的深徹反思與反省,是“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真切踐行。對于廣大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而言,的確需要這種反省意識:不是去詢問從事教育工作能給自己帶來什么,而是去追問自己是否配得上從事教育工作。
塑造立體的教育精神世界
閱讀《教育與永恒》,我獲得了一種特殊的體驗和勇氣。所謂體驗,就是讓人進入一種立體的教育精神世界;所謂勇氣,就是敢于在教育中追尋永恒、把握永恒、體會永恒。從具體內容來看,《教育與永恒》一書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其一,是豐富的教育隱喻。隱喻大量存在于教育實踐領域和教育思想領域。翻開中西方教育經典名著,可以發現里面充斥著大量的教育隱喻。比如,《學記》中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比如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中不斷出現的“太陽”“種子”“樹木”等。這些教育隱喻為人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教育提供了思想工具。然而,從近年來出版的各種教育論著來看,似乎有渲染教育產業化的傾向。而《教育與永恒》一書很明顯還原了教育的本質,作者用了很多隱喻手法,堪稱“神來之筆”,每每令人眼前一亮、思路大開。比如,“教育是神秘的黑森林”“教育本身就是‘十字路口”“教育是對人生的擺渡,人人都是擺渡者”“教育即采掘”“學校是終身學習的中轉站和加油站”……這些隱喻從不同角度將教育真諦形象化、生動化、通俗化,讓人感到親切、信服。
其二,是富有詩意及智慧的教育格言。教育格言是關于教育的簡潔、凝練、富有美感的語句,比如,陶行知的“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就是典型的教育格言。李政濤在后記中說,那種培根式的帶有教化目的的“格言”時代已然過去,自己的文字更多的是一種自我傾訴、自我審視和自我教化。作者憑著對教育飽滿的激情和敏銳的詩心,流淌出一句句充滿詩意、美感與智慧的“教育格言”,比如:“教育,旨在見證人生和生命成長的可能性。教育學,是求證這種可能性的學問。”“教師與學生共同終身學習,是終身教育充分實現的條件之一,甚至是首要條件。” ……這些“格言”富有理論色彩、哲思品位和生命關懷,而且讀來朗朗上口。
其三,是虔誠的教育信仰。馮友蘭在《新原人》一書中根據人對宇宙、人生的理解程度的不同,將人的生命狀態分為由低到高的四種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教育人的生命狀態也可以分為這四種境界:自然境界的教育人,是把教育視為職業,只是滿足和維持自己生存需要的一種手段;功利境界的教育人,是把教育視為事業,努力從中尋求功名利祿;道德境界的教育人,是把教育視為使命,在教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和精神通道;天地境界的教育人,是把教育視為信仰,以教育為生命存在的根基,與教育共同存在。《教育與永恒》實在是一部教育信仰之作,是作者以教育為生命信仰而發出的多重弦歌。李政濤說:“人在,教育在。人的生命與教育同在。”“教育在,我在。”“今日我的靈魂,是教育的靈魂。”“我的一生,從此成了皈依教育的一生。”這些“生命告白”以及整部書散發的濃郁人文氣息,深刻地表現了作者與教育合二為一的生命狀態和人生境界。
生命的真正意義就在于超越有限。那么,教育何為?教育與人同在,教育與永恒同在。因此教育人不能回避永恒,不能排斥永恒,而要有面對永恒的勇氣和引導人追尋永恒的勇氣。
(作者單位:湖南《新課程評論》雜志社)
□責任編輯 萬永勇
E-mail:jxjywyy@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