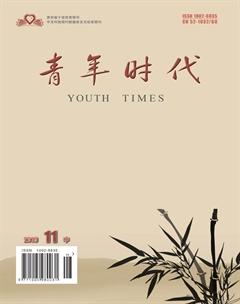略論20世紀上半葉的王安石研究史之研究
郭賀英
摘 要:20世紀上半葉對于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風云激蕩的時代,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這一時期的中國內部的階級矛盾與外部的民族矛盾皆異常尖銳,這與王安石變法所處的時代——內憂外患并存的北宋中期的時代背景多有相似之處。在20世紀上半葉時期,一位長期以來被主流史學界忽視、否定的歷史人物——王安石,自梁啟超《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1908年問世始逐步成為了史學界研究中的熱點歷史人物,其形象亦經歷了由傳統的變亂祖宗法度的“奸臣”到“大政治家”之轉變。在該時期,學界涌現了眾多的王安石研究論著,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王安石研究更是達到了高潮期。20世紀上半葉王安石研究史的研究這一領域,目前已有部分學者予以關注,本論文旨在論述目前國內學界在該研究領域的研究得失。
關鍵詞:20世紀上半葉;王安石研究史;梁啟超
一、引言
筆者以為,考察20世紀上半葉的王安石研究史至少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對該時期出版問世之王安石研究論著做切實之收集統計及精讀;另一方面,切實總結前人之研究得失為后來者之研究提供指導;有鑒于此,故而本文以史料狀況及研究現狀為切入點對目前國內學界在該領域的研究得失略作討論。
二、史料狀況
據筆者了解,20世紀上半葉的王安石研究史這一領域可供參考引用的史料是比較豐富的。對于該時期的史料狀況李華瑞先生指出:“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發表論文一百余篇,出版王安石傳記及其變法的單行本著作(不含詩文選注及介紹)近10種。”[7]朱瑞熙先生的統計與李華瑞先生有所不同,他指出:“20年代至40年代,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受到重視;據統計,著作有七種;這一時期發表在各地報刊上的文章共有93篇,其中關于王安石本人及其政治思想有20篇,關于變法29篇,關于王安石經濟思想、政策18篇,關于哲學6篇,關于詩、文18篇。”[1]對于1912-1949年間的國內外學術界王安石研究的學術成果,張保見和高青青在《王安石研究論著目錄索引(1912-2014)》一書中作了比較完整的整理,這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史料指引。據本書所提供的1912至1949年間的研究、論著整理,筆者發現,20世紀三四十年代王安石研究論著之豐富程度遠勝于1912至1929年間的研究成果,以民國初年1916年出版的研究論著與處于20世紀30年代1936年出版的研究論著為例進行比較,1916年出版的研究論著統計數據僅為2,而1936年出版的研究論著統計數據則為44,這亦從側面映證了20世紀30年代是王安石研究的高潮期[2]。據筆者統計,20世紀上半葉出版的關于王安石研究的史料(含圖書類、期刊類、報紙類,統計數據未含國外學者的論著)總計有三百六十多矣,其中圖書類有91部,期刊類文章有217篇,報紙類文章有56篇,這為筆者的研究提供了較豐富的史料來源①。由此可見,前輩學人對于史料狀況的統計雖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亦存在較明顯的遺漏待補充完善之處。
三、研究現狀論述
國內學界對于20世紀上半葉的王安石研究具有一定的關注度,已有不少論著出版發表,班將對此作系統梳理、評述。
早在1935年,鄧廣銘先生就曾專門撰文《評柯昌頤編〈王安石評傳〉》,對這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王安石研究專著進行評議,他指出:“《王安石評傳》共為二十四章,其規模大體脫胎于梁任公之《王荊公》,而其敘事之順序,考證之資據,議論之張本,也幾乎無一不出自該書與蔡氏的《年譜考略》,且對該二書反見其有抄襲割裂之勞,而不見其有補苴罅漏之功,凡經其以己意增刪的處所,非失之于泛而寡當即失之于簡不扼要。”[3]除此之外,鄧廣銘先生在其專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序言中亦曾對梁啟超的《王荊公》作出過評價:“梁啟超于清朝晚年戊戌(1898)變法失敗之后所寫《中國六大政治家》中之《王荊公》,則是全從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脫化而來,既未再作新的考索,自然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意見。”[4]對比《王荊公》與《王安石評傳》,他認為:“在梁書刊印之后,雖還有繼起評述王安石的著作,如柯昌頤的《王安石評傳》等,更屬‘自鄶以下,不足置論了。”可見,鄧廣銘對于這兩部著作評價均較低。
1959年,漆俠先生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角度對梁啟超、錢穆、胡適的王安石研究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認為:“近幾十年來,資產階級學者(其中包括外國的特別是日本的)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亦做了一些工作。他們擺脫了封建主義的一些缺陷,搜集了較多的材料,提出并敘述了若干有關王安石變法中個別的和局部的事實問題,寫出許多文章。他們比封建主義的學者的研究邁進了一步。但是,他們的研究,充其量僅是對若干孤立現象的說明。”[5]漆俠認為:“梁啟超最先把王安石作為歷史上的政治家加以研究,盡管他的著作材料很不充實,但他首先沖開封建主義的史學局限,給王安石變法以多方面的說明,因之在資產階級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上,是有其開創之功的。不過,這本書的觀點和方法,亦同樣貫穿了唯心主義思想體系。”漆俠對錢穆用南北地域之說來解釋變法派同反變法派斗爭的原因和實質進行了激烈批判,他認為錢穆把新舊思想歸結到南北地域上也是一種唯心論的觀點。對于胡適《記李覯的學說》一文將王安石變法的淵源歸結于李覯,因為李覯及王安石都談《周禮》且同為江南西路人,漆俠認為:“胡適慣于把事物的表面的、偶然的、沒有任何本質聯系的現象,硬是綴連在一起,妄圖說明事物的‘變和‘因的關系。”
“梁啟超的王安石研究”是這一研究領域中的熱點議題,近年來有不少學者予以了關注。
蔡崇禧從寫作動機、取材方法、內容思想三個方面探討了《王荊公》一書,他認為:“由于梁氏的思想‘流質多變,此書正好成為他在1908年的一道思想碑記”。蔡崇禧將梁啟超撰寫《王荊公》的動機歸結為政治方面,關于《王荊公》一書的取材方面,蔡崇禧認為:“是書的資料很大程度上沿襲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然而這并不代表它在王安石研究這個范疇內無關重要。”關于該書所反映的梁啟超之思想內容,蔡崇禧總結歸納為4個方面:一是君主立憲思想;二是干涉主義思想;三是社會主義思想;四是以學校代替科舉的教育思想[8]。
蔡樂蘇和劉超則從政術、學術、心術三個方面比較論述了梁啟超、嚴復二人的王安石研究,在政術方面,梁啟超對王安石新政褒為主貶為輔;在學術方面,梁啟超的關注點在于王安石之經學思想,特別強調“求大義以經世”,嚴復的關注點則聚焦于文學與哲學兩方面,從哲學的視角探析王安石之思想;在心術方面梁啟超對王安石“稱頌不已”,嚴復則對王安石褒貶皆有[9]。對于梁啟超、嚴復二人對王安石研究差異形成之原因,蔡樂蘇和劉超總結認為:“其根源在于兩者性格、文風、思想、學術乃至人格上的深刻分歧。”梁啟超之思想風格為“求用”,而嚴復之思想風格為“求是”,對王安石研究的差異,亦是二人不同思想風格的反映。
吳孟雪認為:“梁啟超之研究王安石,并非是為了釘載籍,純而好古,而是有他本人的事情和目的的。近代史上的變法家要向古代史上的改革家獲取精神營養、經驗教訓,自有其心靈相通之處。”[10]
徐靜主要從梁啟超的新史學思想的視角考察論述了梁啟超的《王安石傳》一書,她認為:“梁啟超所著《王安石傳》,突破了舊史學的‘四弊與‘二病,體現了他的‘注重情感抒發‘敘議結合‘對比研究等新史學思想。”通過解讀《王安石傳》一書徐靜對梁啟超的史學觀也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觀點,徐靜認為:“他的史學觀存在著歷史局限性,他把史學與政治聯系得過于緊密,在方法上以偏概全,他以西方‘進化觀點來解釋歷史現象,尚未形成自成一體的理論體系。”[11]
“民國時期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也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議題,近年來也有學者對該議題作了一定的研究。楊勝寬認為:“郭沫若對宋代社會政治紛爭、王安石變法的性質與得失,乃至對王安石《明妃曲》的闡發都值得重新審視一番,有些失誤是應該駁正的。”[12]他批評郭沫若對王安石《明妃曲》“煞費苦心的階級分析,不僅不合詩的原意,也無助于抬高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家形象”,還批評了郭沫若在未成形的歷史劇《三人行》中對王安石形象的建構設想,即“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識”。馬玉臣的研究總結了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有兩大特色:一是把握宏觀問題的特色,二是學以致用的現實主義史學思想特色,即郭沫若“研究王安石就是為了現實斗爭的需要”[13]。馮錫剛則從以史學研究服務于現實政治斗爭的濟世致用的功利觀念、被研究者作為杰出歷史人物對于研究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及高度評價王安石還顯示出作者的人格追求三個方面論述了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動機[14]。
史學家呂思勉先生一生著述頗豐,在其出版于民國時期的史學著作中對王安石變法這一重要歷史問題,也多有論述。虞云國認為:“自梁啟超著《王荊公傳》,學界對王安石的成見頗為改觀。呂思勉對王安石變法的關注,與此直接有關。”[15]他從對王安石個人的評價、王安石變法的必要性、王安石變法的內容、熙豐時期的新舊黨之爭、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五個方面論述了呂思勉的王安石研究。
這些就是對20世紀上半葉王安石研究成果的專題性研究。近年來,開始有學者對20世紀初以來的王安石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的總結梳理,目前已有李祥俊、朱瑞熙、李華瑞三位學人的研究成果出版發表。
李祥俊在《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一書中從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的視角對20世紀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成果作了比較系統的回顧。對于本論文所考察的20世紀上半葉這一歷史時期,李祥俊主要分為“梁啟超與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的興起和民國時期的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兩個部分進行了學術史回顧。在梁啟超與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興起部分,李祥俊重點論述了梁啟超《王荊公》一書的內容,他認為梁啟超“以西方的學術思想、政治思想來詮釋王安石變法和‘荊公新學,從總體上為王安石其人、其政、其學翻案”。對于梁啟超的《王荊公》一書的學術史地位,李祥俊認為,“他的《王荊公》一書是王安石研究的開風氣之作,為以后的研究定下了基本范式,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許多學者加入到王安石研究的行列,沿著他開辟的方向作了更加廣泛深入的研究”。關于民國時期的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特點,李祥俊總結認為:“呈現出百家爭鳴的態勢,一大批學者繼承梁啟超會通中西的研究方法,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和不同的評價標準出發,對王安石學術淵源、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6]
朱瑞熙先生在《20世紀中國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一文中對清末民國時期的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成果作了總結梳理。他分為清代末年和20世紀20至40年代兩大部分進行了概述性的介紹。他認為:“受梁啟超的影響,中國學術界開始從正面評論王安石,基本肯定王安石的新法。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視。”[16]對于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成果,朱瑞熙先生羅列了該時期的一些較有代表性研究論著,如柯昌頤的《王安石評傳》、熊公哲的《王安石政略》、錢穆的《國史大綱》、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張騰發的《王安石變法之史的評價》及蒙文通的《論北宋變法與南宋和戰》等,進行了概述性的介紹,但并未進行深入剖析。
李華瑞先生《王安石變法研究史》一書從學術史的視角對南宋至20世紀末八百多年來的王安石變法研究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該書是國內首部系統總結王安石變法研究成果的學術性著作。李華瑞先生將南宋以來的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史劃分為南宋至晚清、20世紀前半葉、20世紀后半葉三個階段。他認為:“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遵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20世紀初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評議一改數百年之否定面為肯定,實際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著20世紀前50年的社會氣候,這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首先當梁啟超奮起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之時,中國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其次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特別是他的民生主義與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多有吻合之處;其三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為其訓政尋找歷史經驗和教訓而倡導研究王安石變法;其四二三十年代傳入我國的社會主義思潮對重新認識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影響巨大。”[7]在本書的正文部分設有專章論述20世紀上半葉的王安石變法研究成果,從6個方面論述了20世紀上半葉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其一,嚴復、梁啟超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其二,對王安石變法時代、動機及其指導思想的討論;其三,對王安石新法的討論;其四,關于反變法派與變法派的斗爭;其五,關于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及意義;其六,關于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及教訓。”對于梁啟超《王荊公傳》一書,李華瑞先生認為,“梁啟超的《王荊公傳》是20世紀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議一直以否定性評議為主,直到梁啟超的《王荊公傳》才改變南宋初以來的這種局面,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了案從而突破了封建主義的藩籬”。李華瑞先生進一步指出:“梁啟超是20世紀初推動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變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新史學思想的指導下,梁啟超首先沖開封建主義史學的局限,給王安石變法以多方面的說明,因而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是具有開創之功的。”筆者以為李華瑞先生對20世紀上半葉王安石變法研究的系統性及深度方面均超越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