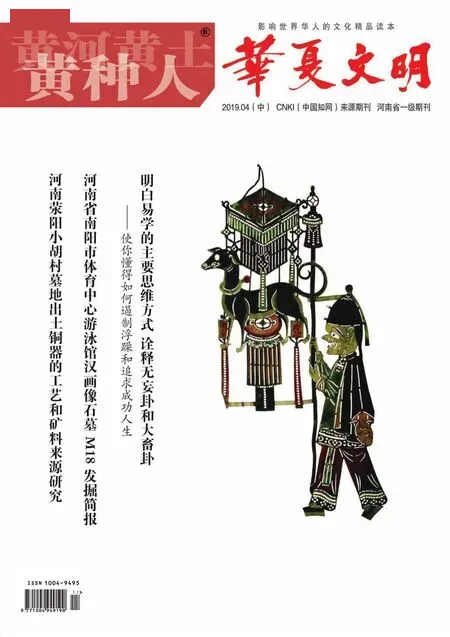試析早期都邑貨物流通與商業形態
□師東輝
一、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這種貿易方式在氏族社會晚期即已出現。《易·系辭》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孟子·公孫丑下》云:“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史記·夏本紀》載,禹受舜帝命,開發九州土地,疏通河道,修治大湖,測量大山,明確各地所交貢賦,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貿易和交換的發展。
氏族社會晚期,社會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高,氏族內部形成以農業經濟為主,包含漁獵、家畜飼養,以及制陶、制骨等在內的經濟結構。在此基礎上,人們通過在“市”進行貿易活動,調節彼此所缺,滿足自己的物質生活需求。
商王朝時期的貿易與交換在其先公時期已經發展起來,《周易·大壯》載:“(亥)喪羊于易。”亥在與有易部落進行牛羊交換時,被有易部落搶奪殺害。于是其子上甲微為其報仇,滅了有易部落。《管子·輕重甲》載:“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鐘于桀之國。”商湯之時,商族手工業發展起來,伊尹通過自己國家生產的“文繡纂組”去交換夏人的糧食,滿足其國家所需。《尚書·酒誥》載:“……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
張衡《西京賦》曰:“商人屢遷,前八后五。”商人因其早期游牧部落的性質,加之考慮自身安全,頻繁遷徙。遷徙過程中出于生活需要,就與其他部落進行牲畜、糧食等的交換,隨著這些交換的不斷發展,交換區域、范圍不斷擴大,商業逐漸開始萌芽。
物物交換作為滿足人們生活需求的一種貿易方式,在早期都邑的都市生活中已經存在,是以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作為經濟基礎而衍生出來的。商代后期隨著貝幣的大量出現,物物交換這種貿易方式依舊存在,但已不是主流的貨物流通與商品交易方式。
二、貨物配給
貨物配給,即將緊缺的生活必需品定量分配給消費者。氏族社會時期這種貨物流通方式即已存在。對其了解,還主要限于文獻資料。
《史記·夏本紀》載,禹“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余相給,以均諸侯”。
商王朝時期,農業、手工業、畜牧業都為國家直接經營,各項產業中的勞動者和為商王朝服務的有專門的技能的武裝人員,他們通過為國家服務,得到一些國家供給,以此來維持其生活。
甲骨卜辭中就有關于這方面的記載,如《甲骨文合集》第31900片卜辭載:“□巳,貞禽佳……食眾人于濘。”這條卜辭的意思是:讓禽在濘地供給眾人的飯食。國家采取供應飯食這種方式,讓人民在不同的地點從事農業勞動、作戰等,以此來保證國家各項機制的正常運轉。
《詩經·豳風·七月》載:“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意思為:七月里可吃瓜,八月到來摘葫蘆,九月里收割那青麻子。采摘些苦菜,砍伐臭椿樹作為柴火,以養活那些為我種田的農夫,把心安。這里的農夫指的就是那些被奴役的仆人,他們吃的也只是一些主人吃剩下的食物。《詩經·小雅·甫田》載:“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意思是:就是這片一望無際的田地,每年打的糧食數也數不清。我只需拿出往年的庫存糧,就能養活我治下的老百姓。主人將一些陳谷子爛米供給“農人”食用,其實這里的“農人”指的也是為其耕作的奴隸。《詩經》中所記載的這兩件事與甲骨卜辭中所記載的應為同一種情形。
由此可以得出,早期都邑內貨物配給這種流通方式是普遍存在的。國家對偏遠地區、窮苦人民的生活補給,是貨物配給的一種方式;“食眾人”是貨物配給的另一種方式,即自己通過勞動為王室服務,得到一定的衣食補償。這兩種方式都是為了滿足大眾的基本生活需要,維持其生計,維護社會穩定。
三、進貢與賞賜
進貢與賞賜是早期社會貨物流通與商業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式。貢納制度是先秦時期的一個重要制度,其產生的原因是當時實行的封建諸侯制的政治制度。進貢與賞賜這種貨物流通方式,早在氏族社會時期就已經存在,夏商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
《史記·五帝本紀》載:“軒轅之時……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摯……”“遍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堯乃賜舜衣與琴,為筑倉廩,予牛羊。”
氏族社會時期,不同階層的人(主要是諸侯、卿大夫、士等貴族)都要向王室進貢,進貢的物品也都有所規定。逾期或未進貢的,王室會出兵征討。各王會賜車馬、衣服給那些有業績、品德好的人。一方面可以鼓勵被賜者更加努力;另一方面可以滿足其生活所需,維護社會安定。
《史記·夏本紀》載:“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冀州:……鳥夷皮服……”“雍州:……貢璆、琳、瑯玕……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這是我國地方上貢金屬鑄鼎的第一次記載。
夏王朝時期,進貢與賞賜這種貨物流通方式已經發展起來,取決于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條件。相比氏族社會時期,其更加有條理性、規范性。對待不同地方的貢賦,因地制宜,具體考察后規定所繳。夏王朝時期的進貢與賞賜模式不僅吸收了氏族社會時期的經驗,也為商王朝時期進貢與賞賜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礎。
商王朝時期,對于其進貢與賞賜制度的了解,還主要限于古代文獻,多種古代文獻都有記載。《伊尹朝獻》載:“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請令以橐駝……為獻。湯曰:善。”商王朝規定各地所獻之物,現在已無法全部對應,但其可反映商王朝時期貢賦制度的完善。各個方國都有自己所貢之物,均是由當地地勢、所盛產之物所決定。
還有一些文獻也可反映商王朝時期的貢賦制度。《詩經·商頌·殷武》載:“昔有成湯……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歌頌了成湯建國后,各諸侯王來朝見、朝貢的盛世場面。”《詩經·商頌·玄鳥》載:“龍旗十乘,大糦是承……四海來假,來假祁祁。”這首詩歌頌了商王朝時期武丁在位時的盛世場景,各諸侯王紛紛來朝貢。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也有反映商王朝時期進貢制度的部分記載。甲骨文中涉及進貢活動的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為甲骨文中對有關進貢活動詞語的記載,另一方面為貢物品種的記載。如:
1.登羊三百。(《合集》8959)
2.貞呼取馬。(《合集》8814)
3.癸丑卜,王,丁秫入,其登于父甲。(《合集》27455)
進貢制度經過氏族社會的產生,夏代的發展,到商代已經基本完善。其發展是由政治、經濟等一系列因素所決定的,完善的政治、繁榮的經濟、規范的法律,無疑是進貢制度完善的助推器。
商王對有功之人的賞賜,甲骨卜辭也有記載。賞賜品的種類比較豐富,有婦女、牲畜、谷物、兵器、貝等。如:
1.庚寅卜,□,貞賜多女又貝朋。(《合集》11438)
2.……征不死,賜貝二朋。(《合集》258)
一些銅器銘文上也有關于王賞賜貝的記載。如:丙午,王賞戌嗣子貝二十朋,在闌宗,用作父癸寶鼎。(《戌嗣子鼎》,見《集成》2708)
進貢與賞賜制度經過氏族社會的萌芽與產生,夏代的發展,到商代已逐步完善,這些發展都離不開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進貢與賞賜的逐漸發展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貨物的流通、商業的萌芽與發展。
四、戰爭掠奪
氏族社會至夏商時期,各氏族、方國之間為爭奪土地、掠奪物資、穩定統治等而征戰不斷。《史記·五帝本紀》載:“蚩尤作亂……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史記·夏本紀》載:“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獲勝方四處征伐,一方面強化了自己的權威,另一方面也獲得了大量的戰利品。
1974年,河南省博物館在鄭州商城東北部商代壕溝的填土中發現近百個殘人頭骨,不少頭骨存在鋸痕[1]。有學者認為這些人頭骨應是被遺棄的廢物,并且通過與殷墟祭祀坑的人骨鑒定結果相比較,推測這些頭骨為商人從其他方國俘虜的異族戰俘的頭骨,異族人被俘后,商人將其作為戰利品帶回,殺祭于先祖,并且將人頭骨鋸開作為飲器[2]。小雙橋遺址發現長方形方孔石器40余件[3],有學者認為這種方孔石器與部分岳石文化方孔石器相同,是一種用于對動物宰殺或食肉分割的切割器具。認為這些方孔石器并不是文化正常交流的產品,而是商征東夷的戰利品,亦是一種祭品[4]。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武官村北地王陵區進行了鉆探和發掘。發現250座商代祭祀坑,發掘191座,出土奴隸骨架1178具[5]。學者對100座祭祀坑進行鑒定,發現無頭祭祀坑的人骨都為男,是介于15~35歲的青壯年[6]。學者認為殷代人種存在類似現代北亞、東亞和南亞種系成分。這些人應為殷人與周邊的方國部落征戰時,虜獲的周邊的異族戰俘[7]。
商王室對四周方國進行征伐的過程中,將戰爭中俘獲的貴族、方伯帶回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甲骨卜辭中就有這方面的記載。
1.羌二方白(伯),其用于且(祖)丁,父甲。(《京津》4034)
2.癸巳卜,祝,貞并來歸,惟侑示。(《合集》41023)
另外,卜辭中還有一些關于戰爭結束后,用從敵方繳獲的牲畜祭祀祖先的記載,如:
1.甲辰卜,集又俘馬,自大乙。(《合集》32435)
2.乙巳,集又俘羊,自大乙。(《屯南》4178)
考古發掘和甲骨卜辭都可以證明,在商王朝時期,商王通過征伐四方,獲得大量戰利品,而這些戰利品又可分為“人”和“物”兩類。俘獲的人多為敵方的貴族、首領等,繳獲的物品有牛、羊等牲畜。商人會進行隆重的祭祀活動,將這些戰利品呈祭于先祖,不僅可以反映自己戰功的卓越,而且也可以滿足自己對祖先的崇拜。
氏族社會到夏商時期,各部落、國家通過對外征戰獲取戰利品,這些戰利品被帶回后,一方面可顯示自己國家的強大,另一方面可用來祭祀先祖。各地之間的互相征伐也促進了各地之間物品的交流往來,對商業的萌芽與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五、商業的萌生
商代是中國先秦時期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農業、手工業等都得到充分的發展,各部門分工明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物物交換的貿易方式逐漸被以海貝為貨幣的貿易方式所取代。商代后期,以海貝為貨幣進行商品交換的商人逐漸出現。
《說文·貝部》載:“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貝主要產生于我國沿海及更遠的地區,其在流入中原地區后,因稀少而珍貴。貝最初傳入黃河流域應是作為裝飾品存在的,其主要用途是作為頸飾或佩戴的飾物。仰韶文化時期的一些遺址內就已經發現了貝。
新砦遺址出土1件屬于新砦二期的蚌貝,以蚌殼切割、磨制而成[8]。二里頭遺址發現有海貝和蚌貝,還有仿制海貝制作的骨貝和石貝[9]。望京樓二里頭文化時期城址出土1枚蚌質幣,形似海貝[10]。此時由于貝的數量較少,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貝僅作為裝飾品存在,還無充足的證據證明其已作為貨幣。
商代許多城邑內都有海貝的發現,數量明顯增多。鄭州商城發現的貝C5.1H118:8,系用蚌殼磨制而成,較光滑[11]。1955年鄭州白家莊M7出土460多枚海貝[12]。東下馮商代遺址發現貝飾1件,標本H35:37[13]。老牛坡遺址88XLI2H35中出土12枚貝,墓葬出土海貝106枚[14]。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內也發現有貝[15]。
殷墟發掘出土的貝數量更多。1932年E181井中發現大貝2枚、小貝163枚[16]。新中國成立后在大司空、小屯西地、苗圃北地等地都有發現。由于殷墟發掘的貝數量太多,在此只簡單地列舉一些。如:1958—1959年后岡南坡的一座殺殉坑中清理人骨54具,有貝飾和隨葬貝的7具,少者1枚,多者達300枚[17];1976年小屯M5發掘海貝6800多枚,6枚綠松石質的仿海貝[18];1992—2001年花園莊東南地M54出土海貝1472枚,M60出土海貝53枚[19]。
商代后期已出現將貝作為賞賜品的現象。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載:“庚戌……貞賜多女又貝朋”(《合集》11438);“……征不死,易貝二朋。一月”(《合集》40073)。商代后期的青銅銘文中亦有賜貝的記載。如《戌嗣子鼎》銘云:“丙午,王賞戌嗣子貝廿朋。”
卜辭中朋作兩串貝形,數目不詳,多少貝算一朋,學者們各有說法,有二貝一朋、五貝一朋、十貝一朋等不同說法。1959年,殷墟的一個晚商時期的圓形坑中,發現3堆海貝,報告里說:“其中有一堆,可以看出確是十貝為朋,連成一組。”[20]加之殷人計算數字多用十進制的情況,所以商代十貝為一朋應接近事實。有學者認為:“當以朋作為賞賜單位和貨幣單位時,一朋就必須有固定的數量,即‘十貝一朋’。因此,可以把十貝一朋制的出現,看作是貝由裝飾品轉為貨幣的標志。”[21]
如果以十貝一朋制度的確立看作貝作為貨幣的標志,那么貝作為貨幣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后期,在夏代貝是否已作為貨幣,還有待研究。自貝流入黃河流域到商代晚期,貝的功能已由最初的裝飾品轉化為貨幣,十貝為一朋。商代晚期貝作為貨幣存在時,依舊可以作為裝飾品存在,但不一定是十貝一朋。加之晚商時期商王朝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貝作為貨幣出現也不無可能。
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高度發展,加之貝幣的出現,在商代后期,逐漸出現了以經商貿易為主要職能的商人。考古發掘中出土了許多非中原地區所產的遺物,如新疆的玉,沿海地區的龜、貝,南方的錫等。這些遺物有可能是通過進貢或者戰爭掠奪所獲得,但也不排除商品貿易這種獲取方式。陜西省博物館所藏的“荷貝簋”上鑄有一幅一人肩挑貝到外地進行貿易的圖像;上海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商代饕餮紋鼎上,鑄有一人挑著許多貝站立在船頭,另一人在后面劃槳到遠方做生意的圖像,形象地反映了商代的行商大賈懷揣“巨款”去外地進行大額貿易的情景[22]。而這些行商大賈,即為商代后期出現的商人,懷揣的“巨款”,即為貝幣。
商代后期的商人,其足跡東北可達渤海沿岸乃至朝鮮半島,東南可達今日江浙地區,西南可達今日川渝地區,西北可達今日陜甘寧乃至遠及新疆。可見,當時各地都已遍布商人的足跡。
商代后期不僅存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還存在以海貝為貨幣進行交換的貿易方式。商人通過貿易與交換,促進了商族同四方的經濟發展,也促進了商族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豐富了商族的文化。
六、結語
早期都邑內的貨物流通方式可分為物物交換、貨物配給、進貢與賞賜以及戰爭掠奪等。這些貨物流通方式促進了各地之間商業的萌芽與產生,加強各地的聯系。早期都邑內的商業活動并不明顯,龍山文化時期和夏代,發現的海貝都不多,貝作為裝飾品的功用大于交換。商代后期,海貝具有貨幣的功能后,加之商人的出現,使商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商業活動還處于初始階段。貝幣和商人的出現促進了各地之間貿易的往來,這些貿易交往不僅促進了商王朝經濟的發展,也帶動周邊四方的經濟發展,促進商族同周邊民族的文化交流。
本文為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早期都邑的形成與都邑形態研究”(批準號:15AKG00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