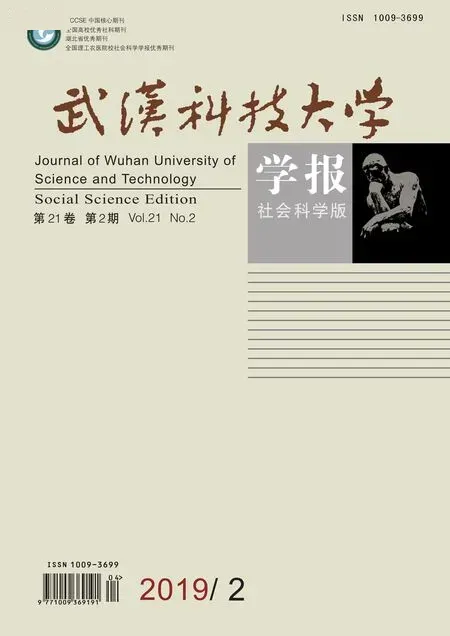戲劇演出的“非特有”媒介屬性
胡 一 偉
(南昌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戲劇演出媒介不是特意為演出而存在的,其“非特有性”是指演出的文本符號載體與人們日常生活經驗中所用之物沒有什么不同的特性。T·考弗臧(柯贊)(Tadeusz Kowzan)在論戲劇的十三個符號系統時,道出了此種“非特有性”:
“戲劇充分地利用那些在現實生活和藝術活動中的以人們間的交流為目的的符號系統,并不斷地從自然界、從社會生活、從各行各業和藝術的一切領域中提取符號加以運用”[1]。
趙毅衡不僅將演出媒介的這種“非特有性”視為演示敘述體裁的一個重要特征,還闡述了身體以及日常物品轉換成了演示媒介的前提條件——經由框架隔斷,或帶上了框架標記。換言之,戲劇演出所用的媒介體現了它從物(事)到符號(物-符號)、從“尋常”到“特用”的轉換,這一轉變過程影響了符號文本的意義生成。
一、作為物-符號的戲劇演出媒介
大多數符號媒介都有其物質性源頭,一旦該符號媒介被使用,它便帶有了“物-符號”的功能(兼具使用性和表意性),可以向任何一端(物或符號)靠攏。演出媒介亦是如此,其“非特有性”正體現了它與現實生活中事、物之關聯——舞臺上的事、物與日常生活經驗中的事、物沒有差異,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很少會像舞臺演出一樣來使用演出媒介。關于這一點,諸多學者早已察覺。
于貝斯菲爾德在比較文學劇本與演出劇本中的物體功能時,揭示了演出媒介由“物”到“符號”的轉換:
“物體是具體的存在,既不是舞臺外客體的某一方面的圖像造型,也不是客體本身。它不是某一現實的圖像,而是具體現實本身,如演員的身體及其產生出來的一切結果,它表演(它動、它跳、它表現),戲劇的絕大部分便存在于身體這個表現——演出體,不管戲劇文本是否明確地考慮到這一點。同樣,物體也有戲可做,它被表現、被展示、被構成或被毀掉,它是炫耀物體、表演物體或生產物體。戲劇物體是游戲物體。它還是重新注入語義的對象,這種語義重注工作在我們看來是戲劇獲得意義的關鍵過程之一。如此,用一物體來表演,比如一支武器,可以產生意義。”[2]
這即是說,實存于日常生活中的物,可被重新注入語義存于舞臺之上。
柯贊在分析戲劇符號系統時,指出了演出媒介的“非特有性”——戲劇所用之媒介符號,包括自然事物和人工符號。一旦它們呈現于舞臺之上,就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意義,這也是柯贊從自然符號與人工符號兩個方面,對演出媒介符號的意義作進一步闡述的原因。
俞建章等在分析藝術符號與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時,也提到了媒介的“非特有性”(盡管他所比較的是語言符號與藝術符號,但筆者認為它同樣適用于藝術符號與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造成二者的區別在于,它們所處的意義系統不一,所處的“位置”、組合的“順序”以及展示的方式不同。就語言與藝術在符號形式上的區別進行具體說明:二者之不同與其所處的不同符號系統的意義有關,在語言系統中,涉及到詞序、詞法(詞匯限定);而藝術系統則強調“表現作用”,即需要對符號文本周邊的意義進行聯想與想象,它沒有明確的指涉(就語言符號系統相比較,它的指涉是間接的、衍生的,需要被補充、被修正),也不受句法秩序限定,并在交流作用之下重新建構文本,以傳達意義[3]。從對語言與藝術符號系統之間的比較,以及對藝術符號系統表意功能的闡釋中,我們也可推出藝術符號(戲劇演出符號)與日常事物之間的差別。
在媒介材料問題上,海德格爾(M.Heidegger)則從更廣泛意義上給了我們較為透徹的看法:他認為,一件藝術作品首先是一件物,正如一幅繪畫作品可以像煤、木料等運來運去一樣,與其他事物并無根本性區別(均有物的特征,且其物質性十分“穩固”)。因而,藝術作品與事、物之間的關系也可以反過來說:
“建筑存在于石頭之中,木雕存在于木頭之中,繪畫存在于色彩之中,語言藝術存在于話語之中,音樂存在于聲音之中。盡管藝術作品是被制作出來的,但它表達的并不僅僅是物,它將某種有別于自身的東西公諸于世,它明顯是種別的東西,尤其明顯是種隱喻。在藝術品中,制作物與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希臘人稱之為sumballein,作品是一種符號。”[4]152
盡管海德格爾很少提到藝術作品的形成(“創造”)過程,但他承認了藝術作品是一種“制作物”,而從物轉為藝術品需要經過一個“去蔽”(unconcealedness)的過程。此處,海德格爾所指的“去蔽”并不是指對多余物的剔除,而是類似一種原始崇拜——“神廟站立之地即真理發生之地,這并不意味著這里正確表現或再現了某物,而是所存在之物作為一個整體被導入去蔽性之中,并繼續保持在那里”[5]56。這即是說,海德格爾所說的“去蔽”并不耗盡(耗費)媒介材料,只是將材料納入形式中——“雕塑家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石塊,就像石匠使用石塊一樣,但雕塑家并不耗盡石塊……畫家使用顏料,也不耗盡顏料,而是像說話者或書寫者那樣隨用隨忘,使詞句在詩中成為真正的詞句”,此時,材料與形式早已融為一體(物的因素“進入”了作品),材料退隱了,“沒有留下任何作品材料的痕跡”[5]47-48。
筆者認為,海德格爾棄絕過度地技藝化,強調媒介的自然屬性(作為自然物、日常生活中的物),同樣也可說明演出媒介的“非特有性”。此外,當代一些藝術理論在媒介材料上所持有的三種不同態度,在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媒介的“非特有性”——馬塞爾·迪尚對媒介所持有的“憎惡”態度(反對為藝術而對媒介材料進行特意加工);約翰·凱奇對媒介材料所持有的“奉承”態度(希望噪音等自然聲響也變成音樂);克羅齊對媒介所持有的“中立性”態度(強調心理形象的啟示作用,物質載體對傳達心理形象只具有輔助性的作用)。
不論是反對制作加工媒介,直接將日常生活中的物納入藝術文本中,還是強調將日常生活中的物進行轉化,它們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藝術(戲劇演出)媒介“非特有性”的妙處。由此,在一些藝術作品中,迪尚常用“現成物品”代替對媒介材料的加工;凱奇在《4分33秒》中不讓鋼琴發聲,而“奉承”劇場中的自然聲音(用其替代鋼琴之聲)。不論是自然物還是日常生活中的物,它們均可以不被加工、雕琢而成為藝術的媒介,即體現出媒介的“非特有性”。
上述揭示演出媒介符號的物質屬性的論斷還可進一步地勾勒出非特有演出媒介本身經歷著的一些轉變——從物(自然物、日常生活中的物)轉變為符號(符號-物),從使用意義轉變為實用意義,也即演出文本中存在著物(事)的功能、意義相轉換的過程。這一演變轉換的“動作”既是歷時性的,亦是共時性的。如,于貝斯菲爾德從物體不同的表現階段(產生與消亡)總結出在不同時代、流派的戲劇展出時,“物”的功能是不同的:古典戲劇中的物體多是“功能的”,很少是修辭的,也從來不是生產性的。只是到了近現代,物體才在生產中得到了表現,它不止具有生產性,甚至是一種“產品”——尤其是在當代,“物體總以‘自然’的方式被表現,對取自自然的物體和文化使然的物體(即人類生產的結果)并不作區分,直到近幾十年來(布萊希特)才看到物體與原始用途脫離,轉向生產功能”[4]160。
近代劇本和導演對物體運用中可體現這種轉變,如從產生人際關系(物左右人物關系)和產生意義(重新注入語義或制造某種規約性,顛覆物體作為“產品”出現的事實,使它反過來成為意義的源頭,成為勞動和勞動者關系的一種比喻)。兩方面來看,日常生活中的物一經轉變,“臺上的人不再被動地接受物體,不再將它看做環境、布景或者提供給他的工具,他制造它、運用它,并改變它、摧毀它……比如對垃圾的運用、作為無產者從中撈取可資利用的這一現實的圖像,又如改變物體的用途(“梯子”變成“橋梁”)、或將日常生活中的物體運用于戲劇”[4]160-161。此時,“物體”呈現出其流動性意味——變為其他媒介,傳遞作為現實生活中的物所不具有的意義,或表現人與事物之間的特殊關系,這就比原有的實用物更具有多義性和創造性。
柯贊則是從橫向(共時性)來比較同一物(事)在不同世界(自然世界與舞臺世界)中的功能與意義。他基于安德烈·拉蘭德對符號的劃分方法——自然符號(其與物、事的關系,由嚴格的自然法則決定,它不是有意圖發生、參與而存在的,而是因人們對它的感知、解釋而成其為符號的)與人工符號(其與所指物、事的關系,基于人類意圖,為指示某物、事或以交流為目的的),得出戲劇表演所用的媒介符號均屬于人工符號的范疇(是有意圖的產生的)。
這是因為“即使所謂的自然符號,也需要觀察者‘有意識’的推理活動,以便連接符號-工具與所指。不管怎樣,在系統闡述更進一步的原則時,即闡述舞臺上明顯的自然符號的‘人工化’問題時,它對科贊是有用的:觀眾把自然符號轉化為人工符號(如瞬間的閃電),這樣,他就能使符號‘人工化’。即使那些符號僅只反映在生活中,它們也會成為劇場中的人工符號;即使它們在生活中沒有交流功能,在舞臺上它們也必然會獲得這種功能”[6]。但僅從符號的發生是否有意圖性這一依據并不能清楚地解釋所有問題,即不能因此就說在演出中不存在自然符號:
“戲劇的手段和技巧是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所以,把自然符號從戲劇中整個地排除是不可能的。在演員的語調、發音和表情中,嚴密的個人習慣是與有意圖地創造出來的情調緊緊相聯的,有意識的動作是與反射運動混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自然符號與人工符號是混和著的。”[1]
在柯贊看來,舞臺上可以同時出現按照人物角色設定要求或由導演意圖而生成的符號(人工符號),以及由演員即興、遇突發狀況呈現出來的符號(自然符號)的,此處,他是以扮演老人的青年所制造出來的顫抖聲音,與高齡演員自身所具有的顫音作對比,揭示出二者之間的關聯。
由于它們均與戲劇符號的意指作用有關,柯贊在分析符號系統時,對動作、發型、小道具等意指層次問題展開了說明。其中,動作符號系統可以代替、指涉其他事物,成為第二層次的符號;揭示與人物有關的文化背景及所處情景狀態的發型,具有多種意指價值;小道具在發揮生活中的實用性時(第一層次意指作用),也有第二層次意指作用。舞臺裝置亦是如此,但它們往往不是單獨起第二層次意指作用的,需要在多個符號媒介的組合作用下構成“物-符號”。
不論是從符號客體或意指角度出發,還是從自然符號與人工符號角度對戲劇演出的媒介符號系統或性質展開分析,他們先將目光投向了戲劇演出媒介符號的構成——符號的物質性源頭,它主要包括自然事物、人工制造的器物和“純符號”這三類。受戲劇演出敘述體裁特征的影響,原本不是為了“攜帶意義”的自然事物可通過演出中某些不可預測情況、即興情況進入演出文本(呈現出來);原本不是用來“攜帶意義”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物可以在被展示的情況下變成演出的一部分(被賦予意義);而為了向觀眾展示并與觀眾交流互動,演出文本中也充滿了純粹表意符號,如語言、表情、姿勢等這類不需要接收者加以“符號化”的媒介,它們可以是實用的或非實用的,但均與人的身體性密切相關。
由此可以說,演出文本中的各種媒介符號并非特制的,因為它可與日常經驗中的事、物一致,具有使用性;即使它單純地作為意義載體被制造出來,但它是具有身體性的媒介符號,也并非是特制的。演出媒介的這種“非特有性”,使媒介符號具有多層意義價值——使用性意義(作為物)、實用意義(物-符號)、藝術意義(作為符號),并在無形中豐富了演出文本的意義。
然而,多種意義的實現以及不同意義價值之間的轉換,與敘述隔斷(展示框架)是有關聯的。海德格爾在論媒介材料(尤其是對“物”的理解)與藝術品形成(藝術作為無蔽的真理而發生的一種方式)時,從某種更為抽象的角度提及到了類似隔斷或框架的作用,并以梵高的《農鞋》為例展開了說明。
在海德格爾看來,處于畫框中的農鞋沒有確定的空間(鞋無所歸屬、非勞動所用,非農婦所注意),我們無法說出它在哪里(田野還是家中),一旦將畫框中的農鞋作為現實中的農鞋去看待時,藝術作品中的物則成為經歷著光照中的物,它的存在也就愈“真實”(這種“真實”并非模仿的真實,“不意味著因為它正確地描繪了某些東西,而在于農鞋作為器具的存在顯示出所有的東西作為一個整體——世界和大地處于它們的反作用中——所達到的無蔽性”),最終真正地顯示出了“僅僅是物”的物[5]56。
這里,海德格爾所強調的對“物”的理解不應停留于“像它們所是的那樣存在”(to let a being be as it is)的表象,而應接近那種躲避思想的“質樸之物”(unpretentious thing),畫框中的物便屬此類。而無論是對真正“僅僅是物”的物的呈現(或藝術品),還是對于一種意義的構成(或真理的構成),這一具有框架隔斷性質的畫框發揮著巨大作用——可以更好地讓物體“去蔽”(自然不事雕琢),并重構意義(不同于現實世界)。
筆者認為,阿爾托的殘酷戲劇,格洛托夫斯基提倡的“藝乘”、質樸戲劇,布魯克的“空的空間”中對媒介的實踐、運用與海德格爾在媒介技藝方面的抽象論述,有其共通之處——哪怕是畫面留白、舞臺空間空無一物,還是畫面滿格、舞臺上擺滿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在類似框架隔斷的作用下,它們被重構著意義,或真正地呈現“僅僅是物”的本真。換言之,戲劇演出(甚至整個演示敘述)中的物-符號關系的轉換也經歷了“去蔽”的過程。即非特制的物/符號一旦帶上了框架標記(再現中的進一步再現、被二度媒介化[7]),會改變其意義。比如,進入一度框架具有實用意義,進入二度框架帶上了藝術意義。
二、媒介“特用”與意義生成
在分析了媒介符號的非特有性后,自然物如何符號化,帶上實用意義或藝術意義,以構建演出文本的意義,是接下來需要考慮到的問題。先從幾類常見的媒介談起,論述舞臺實踐中事、物的“特用”與意義構成。
(一)被“特用”的事、物
演出體裁所用的媒介均具有“非特有性”,即都可視為被“特用”的媒介,這里主要從以身體為中心展開的媒介類型說起,來看單個媒介符號的“特用”與意義生成問題。
關于身體及其延伸的媒介。從身體自身的功能來看,演示框架中的言語、歌聲、吼聲等功能與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不同。譬如舞臺上重復的慢動作或者類似“上吊”“殺戮”等舉動不會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無故上演,卻時常通過敘述框架呈現出來,如目連戲《男吊》《女吊》《調無常》中,演員使用吊繩的表演讓人膽顫心驚,同時也為其精湛表演叫好。而這些舞臺上頻繁發生、顯而易見的行為(被轉換后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將敘述框架凸顯出來。即使有時演員會走下舞臺來到觀眾當中,與觀眾接觸,他們的犯框之舉也會將原有的敘述框架標顯出來。例如,《狄俄尼索斯在69年》中曾有過一個場面:穿著十分暴露的女演員走到觀眾當中,身體躺在觀眾的旁邊并開始撫摸他們,并延伸觸摸的部位。雖然演員將其行為延伸到了舞臺之外,但展示維度會隨著演員行動范圍的擴大而擴大。而其撫摸的動作與日常生活中撫摸的含義自然也有所不同,正如臺上“咬”的動作區別于日常生活中的“咬”一樣。
從以身體為中心展開的媒介功能來看亦是如此,燈光、場面、道具、衣著等演示性媒介與日常經驗所用之物無異,但它們在演示性敘述中的作用卻與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在演出中,導演會利用光影對身體的投射制造特殊效果——從舞臺空間投射到屏幕(幕布上)可以是平面抽象的線條,也可以呈現3D立體的動態效果,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不會時常這樣使用。在實驗戲劇或雜技魔術表演時,我們可與動物一起演示,雖然動物依舊是動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僅不常見到,也更不會與其共處,特別是在與蛇、叢林狼、熊等具危險性的動物“合作”的情況下。在身體的配備上,我們不會在平日的生活中使用面具、化舞臺妝容或裝扮成特殊人物(女扮男裝等)。
關于身體的承載。承載身體性媒介的空間同樣屬于演出的媒介符號系統。空間是人的空間(活動的空間),但這個空間的范圍是抽象意義上的。即承載身體性媒介的空間并非指實體的空間(建筑空間、劇場空間或舞臺空間),而是活動的、會發生變化的空間,是以演員行為顯現出來的空間。這即是說,“特用”不僅包括以身體為演示性媒介之“特用”,還包括承載著身體性的演出空間之“特用”。其中最常見的媒介“特用”方式便是巧妙利用或布置空間場景,通過作用于觀演距離(關系),使得原有空間(尤其是實體空間)發生質的變化。譬如:重新安排或改造演出空間,使觀眾和演員可以隨意活動,表演者和觀眾角色轉換的可能性將達到最大。以法朗克·卡斯托爾夫(Frank Castorf)導演的《記錄列車機車號》為例。演出是在舞臺上進行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后臺為觀眾搭建了一個腳手架。觀眾若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必須橫越舞臺(而此時舞臺上已裝上了建筑用的燈)。先到“觀眾席”的人可以觀察到后來的觀眾如何踉踉蹌蹌穿過舞臺,甚至把一些臺上裝牢的建筑用燈扯斷的舉動。也就是說,早在進入劇場時,觀眾就各自在扮演角色了:后來進場的觀眾,在早已安頓就坐的觀眾的面前,擔當了表演者的角色(不論他們是否愿意擔當這一角色)。為了能成為觀眾,他們先必須成為表演者,但在舞臺的后臺上,他們曾經也被人當作過觀眾。該例中的演出場地未曾變形,“舞臺”依舊是演員“經典的”行為場地,但是觀看區域與展示區域發生了變化。
在《狄奧尼索斯在69年》中,觀眾可以決定自己與演出中心區的距離——隨意調節他們與表演者及其他觀眾的距離,選擇觀察事件的視角。演員也不只局限在過去的汽車工廠的中間部位(圍著黑色橡膠墊子),而是必須在整個演出場地走動。因此,整個演出空間的走動易使觀眾占據演出中心區的位置,并“加入到故事中去”。當然,展示空間的縮小也能使觀眾轉換為表演者,如理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的《公社》(1970-1972)(該戲講湄萊發生的偶然事件)一劇中,一位演員(詹姆士·格雷弗斯)偶然地選出15名觀眾,讓他們走進演出場地中間的一個圈子作為湄萊的村民。倘若觀眾走進圓圈,演出繼續,倘若不聽指揮,演出等待中止。該劇把演出空間縮小到舞臺上的一個圈,觀眾一旦踏進圓圈,轉瞬成為表演者。不管是讓觀眾和演員隨意活動,或試圖讓觀者卷入戲中,上述三例所占用的實體建筑空間并未發生變化,但在展示空間的布局安排上有意模糊生活區與舞臺區的界限,改變了原有舞臺空間的使用性甚至實用意義。
在媒介“特用”方面的大致概括中,我們可以發現,諸種巧用(“特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使之轉換為演出的媒介符號的方法均有異曲同工之效——讓尋常事物帶上符號修辭意義(尋常事物作為像似符號、指示符號、規約符號存在于演出符號文本之中)。奧塔卡·齊克在《戲劇藝術美學》中也有過類似結論,他認為戲劇藝術在方方面面都是形象的藝術,演員代表戲劇角色,布景代表故事發生的地點,燈光亮度用以表示晝夜更替,聲音代表事件或心情,縱使是實體的建筑結構物——舞臺,也是為了代表其他東西(草地、集市、廣場等)而存在,即舞臺的形象功能并非由其作為實物的建筑結構所決定。其中,敘述框架是媒介從“尋常”到“特用”的關鍵一環,它不僅能把身體和物件這些日常物品轉換成演示媒介(“脫離了它們的‘實在’語境,轉換為符號”成為被敘述的故事的一部分,即“特用”),還能將演出空間被“特用”(如展示空間的特殊利用——混淆日常生活與演出舞臺界限等)的情況呈現出來[8]。
(二)“帶表情的”媒介與意義生成
“帶表情的”媒介指一種容易卷入人們情感的媒介。這一理解受麥克盧漢對媒介的分類(冷熱媒介是麥克盧漢關于媒介劃分的標準,在麥克盧漢的理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及對視覺媒介和聽覺媒介的論述影響,盡管國內對其關于冷、熱媒介劃分的標準有諸多爭議,但本文主要從其對媒介指標的考察來看“帶表情的”媒介問題。先從麥克盧漢對冷熱媒介的定義講起。
麥克盧漢對冷熱媒介的劃分主要以感官作用(可感知渠道的種類)、數據飽和程度(信息飽滿或匱乏,清晰與模糊)、卷入或參與的程度、媒介特性(排斥與包容)以及社會作用(“部落化”與“非部落化”)這幾方面為依憑。且不論他在劃分媒介類型、與對具體媒介性質的理解上,是否和現代人理解媒介有一致性,其劃分的指標——媒介的感官作用、參與度和媒介特性對筆者論述“帶表情的”媒介均有啟發性意義。比如,媒介的感官是延伸一種感覺還是多種感覺;參與程度的高低;媒介的排斥性與包容性對意義的生成有直接作用,而多種感官的延伸、參與程度高、媒介的包容性則容易卷入人們的情感,促使媒介“帶上某種表情”。由于視覺與聽覺是人類感官渠道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兩類,且諸多學者在論演出的媒介系統時,已經涉及到從視覺與聽覺角度考慮媒介性質(如在對戲劇演出系統展開分類時,將語言、語調,音樂、音響效果歸為聽覺符號;表情、動作、調度、化妝、發型、服裝、小道具、裝置、照明為視覺符號,等等)。因此,下面主要從視覺媒介與聽覺媒介來論述由媒介引發人們的情感卷入情況與文本意義生成問題。
1. 視覺媒介
演出中,視覺媒介的作用是最為直觀和突出的,這一媒介包括演員在身體上的一些表現(肢體動作、表情等),演員的外形(妝容、發飾、服裝等),舞臺的環境(道具、裝置、燈光照明等)。它們通過自身的形狀、線條、顏色等因素影響情感,以及作用于人們對媒介文本意義的解釋。
例如,在服裝方面,它對卷入人們情感的作用與儀式有關。最早的戲劇性服裝實質上是禮儀式的衣服。具體來說,早期演員們所穿的類似長袍一樣的服裝,起源于酒神贊美詩歌里,牧師吟唱時穿的山羊皮,這一服裝源自許多原始的以神為中心的儀式;而喜劇演員的服裝和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神的森林之神的服裝,需要顯露陽具,也說明了儀式對戲劇服裝的影響作用。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演員為增強儀式化的效果,穿了增加他們高度的厚底鞋;中世紀歐洲扮演圣經故事的牧師,穿上了他們的神圣的白長袍,亦是同理;經典的日本能劇的演員服裝直至今日都是來自宗教精神。此時,服裝那古老和原始的作用,恰好使得演員和觀眾分開,讓演員一穿上,就有了不同一般的身份[9]147。可見,服裝所具有的儀式性作用能引發人們的某些特殊情感,如信仰、迷狂等,一旦情感浸入,則很可能會影響演出文本的意義生成過程。
當然,現代的服裝也有此功能。周寧在論述現代服裝設計的四個獨立作用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服裝通過卷入觀眾情感作用于文本意義的生成這一現象。即,他總結現代的服裝設計有四個獨立的作用:
“首先,和它古老的起源一樣,它至少保留了一點古老的牧師和巫師召喚儀式的魔力。哪怕是今天的服裝,總是要給人看出一種最基本的劇場感。第二,總的來說,一場戲的服裝要告訴我們臺上是個什么樣的世界,不僅要表明劇情的歷史時期和地點,還要含蓄地體現出有關的社會和文化價值。‘服裝’(costume)一詞的詞源含有風俗和習慣的意思,同樣,服裝顯示出居住在不同世界的人穿衣服的習慣。第三,個別的服裝能傳達人物細微的個性,讓人一眼就能看出角色的職業、財富、年齡、階段身份、愛好、自我形象。更微妙地,服裝還能暗示角色的罪惡、美德,以及隱藏著的希望或恐懼。”[9]149
無疑,這里的服裝是被“特有”了的,它所具有的“召喚儀式的魔力”“最基本的劇場感”以及暗示習俗價值觀、隱藏情緒等特點,會通過觀眾的情感感知作用于文本意義生成的過程之中。
在燈光照明方面,媒介也有類似功能。導演R·威爾遜曾用光線計算機①改變演出現場的氣氛,以達到演出預期的效果。他所用的這類燈光(亮度、變化的速度和頻率)是不及人感覺到光線變化的程度的。人的有機體對光線的反應特別敏感,而這種光線,不僅作用于眼睛,也作用于皮膚,即光線通過皮膚而突入到觀看者的身體,通過觀眾的身體影響他們的心理狀態。也即,隨著光線的變換、頻率的改變,觀眾的心理狀態經常斷斷續續地變化。對于這種變化,觀眾自己可能暫時無法察覺,也不會有意識地注意到它,更不會去控制它。威爾遜利用光線的這種特性,是因為觀眾在看威爾遜的演出時喜歡進入這樣的氣氛,這種氣氛在演員有意的和明顯的緩慢動作的基礎上,具有很大的心靈影響力,觀眾進入這一氣氛的傾向也會得以增強[10]173。
2.聽覺媒介
演出中,聽覺媒介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它是無形的,是觀眾閉上眼睛不看演出也無法回避的一類媒介。這一媒介包括由演員說出來的文本(語言、語調等)以及來自其他聲源的聲音效果(音樂、音響效果等)。其中,音樂就被亞里士多德視為戲劇的第五項要素——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戲劇也是要吟誦的,雖然吟誦這種表現形式現在幾乎銷聲匿跡了,但是遺留下來的音樂成分,仍然可以在現今大部分戲劇中直接找到,其余的少數戲劇中間接地保留了這一因素[9]40。
當樂聲直接出現在戲劇中時,它的表現形式是千變萬化的。戲劇演出中最常見的方式是插入歌曲,過去常見于莎士比亞戲劇中,現代在樂于采用表現派技巧的作家(如布萊希特)的作品中也比較普遍。許多自然主義作家喜歡巧妙地把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歌曲寫進他們的劇本,有時甚至不惜讓他們的角色在舞臺上彈奏其中片段。契科夫和田納西·威廉斯也曾在他們的劇中大量使用背景音樂,加強效果。比如在契科夫的《三姐妹》中,觀眾可以聽到場外軍樂隊演奏的進行曲,威廉斯在《欲望號街車》中涉及了從隔壁舞廳里傳來的舞曲,在《蜥蜴之夜》中也安排了從小酒吧傳過來的音樂。另外,導演也頻繁地臨時加進一些音樂——有時是為了在中場或者開演之前制造一種氣氛,有時則是為了烘托劇情本身。在劇場演出過程中,音樂能發揮的渲染力是眾所周知的,它在調動觀眾深層情緒方面發揮的效用,也就是編劇和導演們不敢掉以輕心的原因之一[9]40。
當然,音樂并不只限于既成的歌曲、曲調,還包括某些聲音的“混響”——“間接地講,音樂存在于所有戲劇作品中,存在于所有聲響的節拍中。這些聲響即使不成調,也能交雜混響而構成一個特殊的‘樂譜’——不是音樂的協奏,而是聲音的交響。演員發音的聲調、腳步聲、唉聲嘆氣聲、大呼小叫聲,以及火車鳴笛、鈴聲大作、隱隱約約的擊鼓聲、槍聲、鳥獸叫聲,甚至隔壁房間里的交談聲和夸張的特效音響(如心跳聲、喘息聲,或者冥冥之中的天外人語等),常常都是作者、導演和音響師在情節、人物、對話、主題之外偏愛運用的手段,譜寫成舞臺交響曲,烘托劇情”[9]40。從更為廣義的角度來看,戲劇的可說性、可演性、流暢性也可視為聽覺媒介達到的一種特殊效果。譬如,劇作家在創作時,須盡可能地要求聽覺效果協調一致,因為聲音的節奏韻律能幫助實現輕重緩急。在組構人物對白時,時常使用搖籃曲般輕柔的聲音、快速急切的妙語、低沉的悲嘆、閃光的警句、致命的詛咒、重要的停頓、撩人心弦的竊竊私語等手段營造出一個獨特的時空感受[9]95。
在諸多聲音的環繞下,觀眾的身體會變成所聽到的聲音的共鳴體,與所聽到的聲音一起振蕩。并且,一定的聲音還能消除掉身體上存在的疼痛,這一點儀式聲音的作用最為明顯。因此,“對于聲音,觀眾或聽眾只能自我防衛,比如把自己耳朵捂住。觀眾對于各種聲響(就像對各種氣味一樣)一般來說是沒有抵抗能力的,同時,身體的界限也不存在了。當聲響/噪聲/音樂使觀眾(或聽眾)的身體變成它們的共鳴體,在觀眾(或聽眾)的胸膛里共振,給其添加身體的疼痛,使觀眾(或聽眾)起了雞皮疙瘩或導致內臟的混亂,這時,觀眾(或聽眾)不再把他聽到的當作傳入到他耳朵中的東西,而是把這一切聲響當作一種內部生理的過程來感覺了,而這經常會釋放出‘海洋般的’感覺”[10]173。聲音通過“入侵”觀眾的身體,以共振的方式形成了一個聽覺場域,在這個過程中,觀眾的情感被媒介卷入其中,演出文本意義的生成也在無形中受這一聽覺場域的影響。
概言之,在視覺、聽覺媒介構成的視聽場域(或空間)中,觀眾的接收方式與意義建構的方式是不同的。借用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的“統一場”概念,來說明這種意義建構方式之不同。海森堡的“統一場”與整個場域中各個要素之間的關聯和作用有關,即各要素之間的聯系可以隨時發生改變,是“共時的”“即時的”,并非事先安排好,按線性排列的;要素之間的關聯,會使得它們所發揮的作用通通訴諸于“感性”(又稱為“有機性的”“神經性的”作用)[11]。以此來看視覺媒介,我們會發現人們對視覺媒介的接受過程是呈線性發展的,是有先后順序的,其空間場域是由線性關系組織成的連續體,“屬于統一和相互關聯的那一類”[12]。聽覺媒介形成的空間場域則與其不同,因為聲音的傳播是流動的,不存在聚焦點,它可從任何一處向人們涌來。所以,聽覺的場域,是海森堡說的那一類“統一場”,它可任各種感覺在其中相互碰撞、激蕩,它是非線性的、斷續的、流動的[13]。此時,在不同媒介場域的作用下,尤其是媒介渠道對觀眾的感知作用(如“直接的感覺到情感形式”[14]),將作用于演出文本的意義生成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