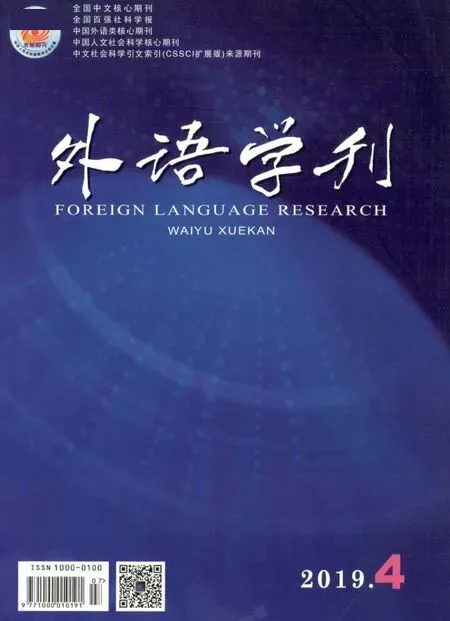詩學征用與文學變異:美國漢學家華茲生英譯蘇軾詩詞研究?
林嘉新 陳琳
(廣東財經大學,廣州 510320;同濟大學,上海 200092)
提 要:華茲生對蘇軾詩詞的譯介是漢詩西傳史上的重要個案,其代表性成果《宋代詩人蘇東坡詩選》是現今最具接受性、流傳性與影響力的英譯蘇詩選集之一。本文通過考察華茲生學術交往與翻譯活動的軌跡,并聯系美國當時“逆向文化”運動的文學思潮,發現其翻譯策略對中國古典詩學進行詩學征用,在譯文雜合中產生中美詩學的碰撞、妥協與再生,使譯詩產生文學變異現象,從而形成新語境下的蘇軾詩詞闡釋。這種文學變異現象是文學跨文化傳播的內在規律使然,也是文學翻譯的本質屬性。同時,該闡釋也契合當時非學院派的詩學理念與譯詩傳統,豐富蘇軾詩詞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譜系與維度,展示出原詩的文本開放性與詩學張力。考察其譯詩的文學變異現象,有助于加深我們對文學譯介內在規律的思考,對中美文學關系研究也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英語世界對蘇軾詩詞的譯介已有百余年歷史,最早進行譯介的譯者可追溯到1853年魯米斯(Loom is,A.W.)(戴玉霞 成瑛 2016:104),主要譯者包括華茲生(Watson,B.)、王紅公(Rexroth,K.)、孫康宜(Sun Chang Kang?i)、朱莉葉·蘭道(Landau,J.)與梅維恒(Mair,V.)等。其中,華茲生是譯介蘇軾詩詞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譯者。總計譯詩近一百五十首,超過其他4位譯者譯詩數量的總和,主要見于《宋代詩人蘇東坡詩選》(1965,86首)《中國抒情詩風》(1971,6 首)《哥倫比亞中國詩選》(1984,20首)《蘇東坡詩選》(1994,116首)等譯詩選集或專輯中。其中,《宋代詩人蘇東坡詩選》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代表性著作叢書》(UN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Chinese Series),《蘇東坡詩選》榮獲1995年美國筆會翻譯獎(PEN Transla?tion Prize),產生較大的文學影響,堪稱“蘇軾詩詞英譯與出版的成功者”(同上)。
以往關于華茲生譯介蘇軾詩歌的研究大都忽視一個根本問題,即華茲生譯介的蘇軾詩詞是一種因詩學征用而產生的文學變異現象,其中摻雜譯者本人的禪道思想、詩學理念與中國想象等,是歷史性社會文化因素聚焦于個人并通過翻譯活動外顯化的產物。因此,對華茲生譯詩的討論必然不能脫離其生成語境。本文將運用描寫譯學與譯介學的研究方法,描寫華茲生譯介蘇軾詩詞的語境,重點觀測譯者如何與語境進行聯系與聚焦,以及譯者秉持的詩學征用理念如何影響其譯詩策略,并通過譯例說明譯文的文學變異表現形態,以期最終解釋其譯詩的文學變異現象。
1 “逆向文化”運動與華茲生的詩學因緣
在描寫翻譯學研究框架中,“翻譯應解釋為什么譯作會出現在那特定的社會時代和地點,即翻譯史應解答翻譯的社會起因問題”(Pym 2007:xxii)。具體而言,“在研究翻譯的過程、產物以及功能的時候,將翻譯置于時代中去研究。廣而言之,是把翻譯放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之中去研究”(Tymoczko 1999:25)。因此,考察華茲生譯詩活動的“歷史現場”需要探究譯者與語境、譯者與原文關聯的起因與途徑。
華茲生的詩學因緣發軔于其在日本期間的修禪活動,此階段美國的社會文化形態和詩學背景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表現出對東方文明與文化精神的訴求。二戰后,美國陷入精神上的荒原,戰爭的創傷、對機器文明和壟斷資本主義的厭惡,使得一批對種種現實不滿和失落的年輕人開始走出西方文明的中心,轉而向處于邊緣文化地位的東方文明尋求精神上的依托。對東方思想的吸收和追求成為“當時的一種時代風氣”(鐘玲2003:85),尤其推崇禪宗。當時,有不少美國青年,如凱格(Kyger,J.)、科爾曼(Corman,C.)、斯奈德(Sny?der,G.)、金斯堡(Ginsberg,A.)等,不遠萬里來到日本學禪、坐禪、交游、創作,華茲生亦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此期間,上述詩人都曾審閱并編輯過華茲生的譯詩手稿,并對其譯詩方法有過指點。受此影響,華茲生接受非學院派詩學及其譯詩理念的洗禮,并在實踐中采取相應的譯詩策略。
2 譯詩選目與蘇軾詩歌的山水禪意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一批反學院派詩歌運動和文學團體也在“逆向文化”運動中涌現出來,例如“垮掉派”“舊金山詩歌文藝復興”“黑山派”等。“反學院化”的本質決定運動從一開始就以抨擊學院派詩學主張為主要議程。“美國詩不僅要擺脫英語文學正統的壓力,還要在一定程度上松動歐洲文化正統的束縛”(趙毅衡1983:21),故他們期冀于在東方文學,尤其是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精神內涵中尋求改變詩學格局的力量,不僅“反對艾略特的影響帶給美國詩歌的形式主義、保守主義和古典主義傾向……立足美國本土”(彭予 1995:214);而且還反對非個人化、重視格律、客觀晦澀的學院派詩學原則。此次文學運動尤其青睞對中國古典詩的自然山水精神與道禪思想,并在譯詩中尋求創作靈感。
20世紀50-60年代西方興起的“綠色運動”為生態譯詩小傳統的后期發展與最終確立提供精神支持。二戰后,相對“穩定”的世界政治格局為西方經濟的迅速復蘇提供外部保證。經濟迅速增長帶來的物質社會繁榮也為環境生態危機的出現埋下伏筆。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森(Carson,R.)出版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正式拉開西方“綠色運動”的序幕。該書列數人類在發展中對大自然肆意索取的暴虐行徑,痛斥人類對大自然生態平衡的破壞。“綠色運動”在此后的五十多年里繼續發展,世界各地關于環保議題的示威、游行、集會、演講和宣傳活動隨處可見,這為全球生態意識的形成提供源源不斷的思想動力。
“逆向文化”帶來的中國想象與“綠色運動”的影響合流,為西方學界吸收中國古典思想、文學和文化的樸素生態意蘊提供精神滋養。這段時期,美國社會失望于混沌、喧囂的現實文明和文化精神,轉而從追求心靈寧靜的東方文明和文化中尋求精神的救贖。這批詩人不僅進行詩歌創作,還參與許多譯詩活動,創作和翻譯的作品也大多體現出對中國禪道意境、寓情山水、清靜無為、閑適雅居等生態文化精神向往。他們從詩情畫意的中國山水詩、禪意詩以及充滿禪宗意趣的禪詩中尋求到撫慰和精神與心靈的共鳴。“此傳統的譯文之共同特色是通常選擇典故少的詩,或省略其典故而不譯;為了英文之優美不惜曲解原意,而且為了符合西方人對古中國的想象,或為了譯者之偏好,中國古典詩中的隱逸詩、山水詩、友誼詩特別受到注重,較少譯詠物詩。”(鐘玲2010:292)華茲生深受該群體譯詩理念的影響,在社會交往與理念灌輸的作用下,華茲生逐漸感知、認識與習得該譯詩傳統的預備規范,使其選譯的古典詩也大多具備樸素生態意蘊與內涵。
華茲生的譯詩選目意圖較為清晰明確:為了傳遞原詩的各種意象,營造出詩人(詩文)山水禪意、靜籟雅居、閑適生活的審美旨趣,其選目傾向于體現蘇軾詩詞的“生態性”,甚少選錄其他主題。蘇軾“深受北宋學禪之風的影響。在詩詞創作中溶進佛教禪宗圓融、清靜的思想,排除雜念,專注于一境,將自身與山水、自然融為一體,使心靈得到寄托、精神得到開釋,達到身心‘輕安’、觀照‘明凈’的境界”(張琪 2012:210)。這些文學特質都有與生態文化精神契合或相通之處,譯本選目多為禪詩、哲理詩、山水詩,顯然有意過濾掉政治批判與社會現實等嚴肅主題,使蘇軾表現出山水佛禪、悠然自得的審美意趣,遮蔽蘇軾憂國憂民、心系家國的政治情懷。
3 譯詩方法與“非學院派”詩學理念
“逆向文化”運動時期,美國譯壇對中國古詩的興趣已不再滿足于表面、淺層的文化征用層面,而是極力追求中國古詩精神實質,“他們都希望更深入到中國美學的核心中去”(趙毅衡2003:279)。與龐德、洛威爾等第一代譯者借鑒中國古典詩歌進行形式上的試驗和創新不同,以王紅公、斯奈德和威廉斯等為代表的第二代譯者“不是表面上采用東方的事物、意象、典故,而是挪用中國古典詩的內在經驗、結構與思維模式”(鐘玲2003:279)。即開始“由形式上模仿化用轉入文化精神上的汲取、融會”(江嵐 2009:278)。這批詩人嘗試通過對中國古典詩的詩學手法與思想理念的跨文化闡釋,尋求美國詩歌本土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以使其擺脫僵化的學院派詩歌傳統的桎梏。在這些文化和詩學動力的合力下,中國古典詩再次走入美國文學視野,這一代詩人和譯者借鑒中國古典詩短小精悍、明朗清晰的詩學手法和風格,立足美國詩歌本土化,賦予中國古典詩自由開放的新形式——自由詩。
由于該譯詩傳統下的譯者群體普遍主張吸收、借鑒中國古典詩的文學技法(如詞序、句式或韻律),努力使其英譯文擺脫歐洲學院派詩風的桎梏,為當時本土派詩學主張注入新意。但因中英詩歌在格律、韻式和體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種文化傾向性主要以譯文雜合①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當西方形式與本土現實(原文)相遇,必然會帶來結構性的妥協……同樣,妥協的表現形式也具有多樣性”(Moretti 2000:62)。
受當時的譯壇風氣與詩學流變的影響,華茲生也秉持“借力中國古詩”的譯詩傳統,主要體現在譯詩形式(包括韻律、體式與修辭)與內容上。他認為“中國詩的詞序與英語詩十分近似,詩行在表達上相當具體,譯者在翻譯時通常會受其引導,甚至受制于原詩”(Watson 2001:6),因此改變原詩行文順序的做法還有可能會使譯文生硬拗口、詰屈聱牙。對此,他提倡適當模仿漢語原詩形式,例如,“在譯詩中,我盡可能省略代詞,因為中國詩中很少使用代詞(日語詩亦如此),且盡量不使用冠詞”(同上:4),“盡量緊貼原詩的措辭與行文結構”(同上2002:xxii)。但因中美詩藝的巨大差異,原詩的源文化不可能全然不變地進入譯詩,而往往會采用折射性翻譯的形式進入譯語文化,從而產生譯文雜合的現象。有鑒于此,華茲生將原詩的節奏、疊詞與對仗融入英語自由詩中,具體表現為譯詩借用中國古詩短小精干的特點,采用逐句翻譯,詩行與原詩對應;將原詩的對偶、疊詞等文學手法化入譯詩,啟用英語口語體,表現為漢語格律詩與英語自由詩的譯文雜合。
3.1 韻律翻譯
在韻律方面,“雖然華茲生英譯中國古詩沒有顧及尾韻,但他對節奏還是把握得比較好”(魏家海2009:64)。華茲生譯詩使用自由詩,以英語詩歌節奏為基調,使用“以逗代步”展示原詩的平仄節奏,譯詩保留部分疊詞的聲韻特色。譯詩中,漢語格律詩的韻律技巧得以“化”入英語譯詩,展現出原詩韻律技法與特點,豐富美國詩歌韻律形式的表現力與張力。
在翻譯蘇軾的七言律詩《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時,譯詩在自由詩的基礎上,以漢語原詩的平仄停頓為依據,在對應的譯詩行相對語義位置后加逗號做頓,再現原詩平仄停頓。

表1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漢英對照
英文詩歌節奏由輕重或重輕音步掌控,其音步的基本形式為抑揚格或揚抑格,除語法要求或其他特殊目的外,一般不會輕易在詩行中添加逗號以作停頓,因為這樣會割裂詩行句法與語義的連貫性。在譯詩中,第1、2、4、7句以原詩停頓為基礎,“加逗做頓”以顯示原詩的節奏特點。這種翻譯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詩歌翻譯中“韻律不可譯”的遺憾,顯示出部分原詩停頓,且譯詩以原詩的停頓為依據,僅在完整的語義單元之后作逗,保持原詩與譯詩之間的語義完整與連貫,減少譯文語義碎片化的傾向和邏輯順序混亂的風險。
華茲生譯詩雖然沒能展示原詩尾韻,但特別強調疊詞的翻譯。疊詞是漢語中常見的修辭方法,也是除尾韻外加強詩歌節奏感的重要手段。事實上,由于“漢語長期以來朝雙音節的方向發展,疊詞運用起來覺得不十分費字累贅”(陳文成1991:44),中國古典詩也常用疊詞來增強節奏感和音樂性。但英語中,除一些口語和套話外,疊詞一般不輕易使用,因為“重復有時表明語言資源的匱乏……將一件事反復言說僅表明(說話者)沒有能力將所要表達的意思一口氣說清楚”,若使用疊詞一定是為了獲得特定的藝術效果(Leech 1969:79)。華茲生的譯詩有意保留原詩的部分疊詞用法,展示原詩的聲韻技巧。在翻譯蘇軾《無錫道中賦水車》的前兩句詩時,華茲生對疊詞翻譯技巧的運用表現得淋漓盡致,充分展示出原詩的音樂性藝術效果。
蘇軾的這兩句詩運用4組疊詞,聲覺效果十分明顯,形式上也很有氣勢,展現出原詩疊詞使用的藝術特色。譯詩運用 whirling,whirling和round,round兩對頭韻疊詞來翻譯第1句的“翻翻”與“聯聯”,形成與原詩完全一致的AA+BB疊詞形式;在譯第2句詩時,使用lump和bump這對低沉尾韻音/?ump/來翻譯“犖犖”與“確確”,既有疊詞的音韻效果,也是對原詩描繪的水車運作時低沉聲音的擬聲(onomatopoeia)。這種韻律翻譯方法所產生的效果也堪稱“詩學奇跡”,因為“中文韻部少(押韻比較容易)使格律詩相對比較自由。英文韻部上千,押韻在創作中都是比較難的事,翻譯找韻當然更是取巧用奇。用自由詩反能譯出中國古代格律詩的精神,本無足怪”(趙毅衡 2003:207)。

表2 《無錫道中賦水車》前兩句漢英對照
3.2 對仗翻譯
華茲生在譯詩中強調對仗的翻譯,用英語的平行結構將原詩對仗譯出,使得譯詩表現出原詩修辭的特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將原詩的所有對仗都一并譯出,而是要避免平行結構繁復出現,以突顯原詩的修辭,也使得譯詩自然流暢。如在翻譯蘇軾的《過永樂文長老已卒》時,華茲生在處理平行結構時表現出明顯的取舍。

表3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漢英對照
在翻譯頸聯時,華茲生卻未用任何平行結構,僅將原詩直譯成英語,其目的正是在于避免平行結構過多而造成譯詩生硬牽強。由于對仗翻譯的取舍得當,譯詩既表現出自由詩的自由成章和樸實自然,也凸顯原詩對仗修辭的平衡藝術美感。由于華茲生譯詩采用英語自由詩,原詩中的平仄停頓、疊詞與對仗在進入譯詩后呈現出譯文雜合的現象,即漢語格律詩與英語自由詩的雜合。
3.3 譯詩用語
“逆向文化”運動中,美國譯者通過翻譯實踐美國詩歌(尤其是“本土派”)的語言觀,主要表現為在譯詩中使用美國日常語言,尤其是口語體。華茲生翻譯的蘇軾詩詞也使用大量當代英語口語,并不拘泥于語法與書面語的框架,省略、俚語、重復、呼語等經常在譯詩中出現,譯詩語言具有極大的表現力與張力。他認為,“在翻譯使用日常習語的詩歌時,如若為使譯詩更有趣而使用夸張的措辭手法,無異于違背譯者倫理……我所翻譯的語言——古代漢語在表達上十分簡潔,在翻譯時,我完全同意應盡可能使用簡潔的英語來表達。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檢查我的翻譯,以找出可以刪除的詞語,或以更簡短的形式傳達意義的方法”(Watson 2001:4)。現以《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其一)為譯例進行分析。

表4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其一)漢英對照
原詩是一首題畫詩,蘊含清凈禪機意趣,風格樸實,古雅里透著清和、明凈。華茲生的譯詩卻語言曉白、措辭簡單,并未使用任何古雅用語或詞匯,還使用縮寫、語氣轉換、會話建構等自然語流的用法。如 never peop le,Chuang Tzu no longer with us等省略句的使用,模仿日常口語;使用I,he,himself,us等人稱代詞將原詩中不明晰的交際關系明晰化;第3句與第4句建構出會話模式,具有自問自答之感;第8句用疑問語氣發出感嘆,表現出自然語流的真實性,口語化傾向明顯。
盡管劉若愚對華茲生譯蘇軾詩詞所采取的通俗語言(尤其是口語體)的做法頗為不滿,認為這樣會極大地影響譯詩的文學性,但正是使用通俗化、日常化、口語化的譯詩用語才使中國古詩得以跨越語言的藩籬,為英語世界普通讀者接受;美國漢學家白牧之(Brooks,E.)與白妙子(Brooks,A.)也稱“華茲生的譯文具有眾所周知、備受公認的優點——即翻譯用語平易口語化,內容通順連貫,以至于幾乎不需要解釋”(Brooks,Brooks 2009:165);漢學家畢曉普(Bishop,J.)也稱華茲生的譯詩“值得信賴,且可讀性極高”(Bishop 1965:478)。
4 文學變異與譯詩的闡釋性
文學變異是文學跨文化傳播的本質規律,華茲生對中國古典詩學的征用,與美國文學傳統產生碰撞與回合,在譯者翻譯中產生內容或形式“他國化”的文學變異,并賦予蘇軾詩詞新的闡釋。
首先,文學變異體現在譯詩形式上。在翻譯蘇軾詩詞時,華茲生將漢語格律詩的平仄停頓,疊詞與對仗融入英語自由詩中,創造一種迥異于前人譯詩的韻律與詩體,這種譯詩形式既非美國詩歌特有,也不屬于中國詩歌傳統,革新美國英譯中國古典詩的翻譯詩學。在韻律上,華茲生譯詩雖然也跟隨自由體譯詩的潮流,但對中國古典詩的詩律也非常強調,主張將原詩的平仄停頓與疊詞適當地譯入英語自由體,使原詩的部分韻律在自由詩中顯身,產生譯文(詩律)雜合的現象。這與前人用英詩格律譯中國古典詩(如翟里斯、理雅各)或自創新的格律形式譯詩(如龐德、韋利)的做法顯著不同。此外,華茲生還翻譯格律詩的對仗句,使其以英語平行結構的形態進入到譯詩中,展示漢語格律詩平衡美,彌補前人譯詩忽視對仗句的缺憾。
其次,文學變異還體現在譯介內容上。其譯詩選目附和“逆向文化”運動下的譯者群體對中國古典詩山水禪意的偏好,嘗試通過傳遞原詩的各種意象,營造出詩人(詩文)山水禪意、靜籟雅居、閑適生活的審美旨趣。但蘇軾詩詞并不是“生態性”可以完全概括的,而是立足于美國語境的文學變異。華茲生重點選錄蘇軾的禪詩與山水詩,甚少選錄其他主題,使蘇軾表現出山水佛禪、悠然自得的審美意趣。經過文化過濾式的翻譯詩學闡釋,譯本中的詩人形象與藝術風格均發生變異現象,蘇軾的創作維度、詩藝風格都被線條化與簡單化,呈現出與源文化不同的文學面貌,成為譯者在美國語境下的新闡釋。這種闡釋是中美文化、中美詩學相遇而發生折射性翻譯的必然結果。通過文學變異帶來的全新闡釋,華茲生的譯詩也使得中國古詩第二次作為“他者”,在美國文學舞臺上展示出樸素生態意蘊與精神的特質。
5 結束語
華茲生譯介蘇軾詩詞所發生的文學變異現象,是當時美國文化語境的內在要求,也是文學跨文化傳播的規律使然。這種新闡釋使蘇軾詩詞在美國的世界文學場域中得以豐富、延續與流傳,譯詩釋放出原詩的話語張力與藝術活力,再次表現出原詩的意義不確定性、文本開放性與多元闡釋性,使原詩文本在新語境架構下得到拓展轉換、重獲重生,展示出蘇軾詩詞歷久彌新的生命活力。
注釋
①譯文雜合是指“譯文不可避免地會包含一些來自原文的語言、文化或文學的成分,而且這些成分都是譯入語文化中所沒有的,如一些新異的詞匯和句法、具有異國情調的文化意象和觀念以及譯入語文學中所缺乏的文體和敘事手法等等”(韓子滿20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