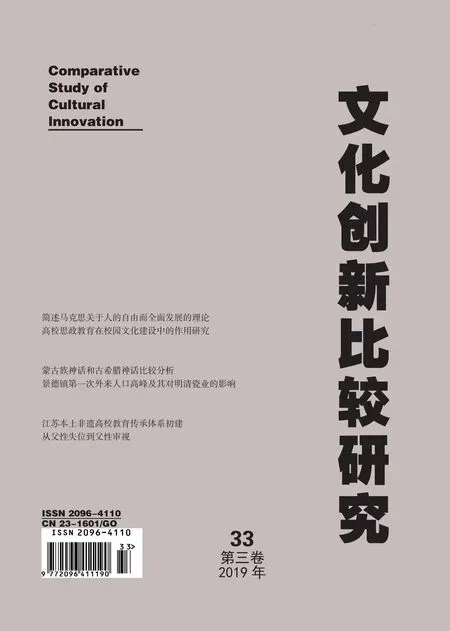從父性失位到父性審視
——論東西小說中的父性主題
潘頌漢
(百色學院,廣西百色 533000)
在家庭倫理中,父性的存在象征著秩序與威權;在歷史、文化以及社會運行的秩序中,父性又象征著傳承。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新生力量的不斷涌現,父性的存在卻成為逐漸成長的新生力量——兒子的桎梏與阻礙。在卡夫卡的不朽名著《變形記》里,就通過一則現代性的寓言,敘述了父親/舊秩序與兒子/新秩序之間相互依存、相互矛盾,同時也是此消彼長的錯綜復雜的關系。
廣西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東西的小說中同樣投注了作家對父親、父性的深刻思考。和同時代的作家不同的是,東西將時代的轉換和社會的轉型融入到對父親和父性的解讀與審視之中,借助于夸張和怪誕的手法,將轉型期家庭倫理以及社會存在形態中的父親形象結合起來,進而闡述了個體在社會轉型時期的現實際遇和心路歷程。父親以及父性在現實生活中的失蹤,導致了家庭和社會出現了極為荒誕的失序現象,而“尋獲”父親之后,對父親和父性的審視與反思,又顯示出強烈的時代性,凸顯了社會轉型時期瘋狂生長的歪斜之力以及由此導致的文化斷裂感。那么,在此過程中,父親以及父性存在的意義就值得讀者們的深思。
1 父親的失蹤與父性失位
從東西小說的敘事脈絡觀察,《耳光響亮》是作家系統地將父親以及父性在歷史際遇和現實生活中的意義和價值進行充分探討的開始。作品的敘事時間設置在“文革”即將結束,中國社會將要邁入新時期的歷史節點上,偉人離世的歷史悲愴疊加著父親牛正國莫名離家的恐慌,將父性失位和父親失蹤的歷史與現實相互映照,透視了在社會轉型期到來之時,人們無序而混亂的生活狀態。父親牛正國失蹤前,妻兒們對他熟視無睹,似乎暗喻著父親的存在沒有多大價值;但是隨著牛正國的失蹤,母親將改嫁的議題提上日程,牛家三姐弟,尤其是二兒子牛青松,才意識到權力交替時代的到來,利益和話語權要重新分配了,于是開始蠢蠢欲動起來。為了爭奪話語權,牛青松用姐姐牛紅梅的身體作為籌碼,換取寧門牙對繼父金大印的毆打。“《耳光響亮》中父親的失蹤和母親的出走使牛家頓時墮入文化、道德與秩序的真空,因而造就了強烈的歷史斷裂感,也助長了文化破碎感與虛無感的升騰。”父親的死活似乎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利益的再分配和人物“活下去”所需要的物資配給。
父親的缺席,卻使牛家三姐弟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感受到父親存在的意義,因此,父性“缺席的在場”尤其使人懷戀秩序存在的意義和作用。牛家三姐弟享受著父親留下的這些財富,卻不得不面對父親已經“缺席”了的現實,所以只能繼續在茫茫人海中去尋覓父親的存在。但是所有的消息都指向了否定,進而顯示出文化的不可賡續,或者是使人感到茫然的斷裂感。牛家的話語權更替以及新秩序的建立仍然處在交接的過程中,他們無法擔負重建社會、重整秩序的重任。有論者指出,“父之死亡、缺位則意味著這種秩序的解體、失范和人的內外生活的混亂和失序,這種混亂和失序又似乎成為了現代人無可逃避的宿命。”在父性失位的現實生活里,作為家中長子的牛青松并沒有在關鍵的時刻成為父性的堅定守衛者和代言人,反而在現實生活中追名逐利,在混亂和無序中手足相殘。如果說二弟牛青松將大姐牛紅梅出賣給地痞流氓是令人錯愕而感到齒冷的情節設置,那么當牛翠柏已經開始勸說姐姐牛紅梅去賣淫的時候,更令人感到絕望。這個曾經同情、關愛姐姐的“窮大學生”是在什么時候完成了他的人性蛻變?報復楊春光成為牛翠柏勸說牛紅梅賣淫的理由,實在太過牽強——但是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窮大學生”也和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迪涅一樣,蛻變成私欲不斷膨脹的野心家。而他的人性埋葬之路,卻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這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現實。在父性失位的狀態下,牛家三姐弟不斷地承受來自外界的物質條件的引誘和襲擊,直至所有的人性全部陣亡。
書寫時代轉型中的父性失位和由此帶來的生命悲情,東西小說開掘了家庭倫理和社會震蕩狀態下的共振路徑。隨著社會演變的進一步推進和城鎮化時代的到來,凋敝的農村被城市逐漸地吸納,子女們比父親更早、更決絕地離開鄉土,那么,執著地守候在鄉土和傳統里的父親以及父性的遭遇同樣具有審美的價值和意義。小說《我們的父親》里,父親從農村老家來到“我”居住的城市,但是卻和敘事者在城市里的“家”有著非常大的隔閡感,無法深度融入這個家庭之中。父親覺察了其中的生疏感,于是離開我家到姐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在醫院工作,吃飯的時候要拿酒精棉給筷子消毒,但是卻故意沒有給父親消毒他要用的那雙筷子,因此父親重重地拍下筷子,離家出走,最終消失在夜幕之中。小說的最后,父親摔死了,身為醫院院長的姐夫并沒有發覺,簽發了死亡記錄的公安局長大哥,也沒有發覺,甚至是埋葬了父親的慶遠,也找不到土堆里的父親的尸首,那么,父親到底去哪兒了?他怎么能夠和牛正國一樣,突然就從我們的生活里消失得無影無蹤?作家通過父親的失蹤,深刻地反省了欲望時代親情和倫理的旁落,以及人倫和價值的缺失問題。
2 父性的審視
父親的失蹤使人們不由自主地反思,進而審視父親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新時期到來之后,隨著商品經濟浪潮滾滾而來,泥沙俱下的時代生活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存方式,影響并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父親以及父性的遭遇又呈現出新的特色。
如果撥開小說《后悔錄》的種種敘事迷霧和“干擾”,其中的一條敘述線索是值得讀者注意的,那就是小說以“我”的口吻,敘述了一個“文革”時期成長起來的小孩,剛開始的時候被“文革”的革命狂熱裹挾,告發、陷害了自己的父親,結果幾乎家破人亡。荒誕但是卻異常殘忍的人間慘劇,終于使敘事者開始醒悟,并開始了自己的“后悔”之“錄”,小說的結局正是在敘述者喚醒了已經處于植物人狀態中的父親結束,顯示了人性的最終復歸和對“父性”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的重新認可。
小說里,曾家是解放前的資本家,解放后把家產全部捐給了國家,但是,當“文革”到來之后,紅衛兵們仍然沒有放過這樣的資本主義的“尾巴”,小學校長趙萬年就一直在千方百計尋找資本家的兒子,“我”父親的生活污點加以攻擊。當“我”發現父親和趙萬年的妹妹偷偷地在一起之后,卻把這個秘密告訴趙萬年,以換取“革命組織”和“領導”對“我”的賞識和提拔。不僅如此,“我”還數次告發自己的父親,顯示出“我”,以及在那個荒唐的年代成長的年輕人的荒誕和無知。“大字報”、“高音喇叭”等摧折人性的極權政治符號把“我”給塑形了,使“我”變成一個親情泯滅、六親不認的狂熱分子。“文革”被東西典型化為兒子出賣父親的力比多的狂熱,典型化為一種秩序的更替和話語權的爭奪過程。當父親掙扎著從批斗現場爬回來,在雪地上留下了兩道深深的印跡的時候,“我”終于“后悔”了,于是通過照顧受傷的父親以換取他的諒解。
從《耳光響亮》到《后悔錄》對“文革”的歷史敘述,顯示的是作家對父性所遭遇的思考路徑,已經經歷了從混亂無序的狀態中逐漸找到價值坐標的漸進過程。始于尋找,而終于審視的父性遭遇,使人物從弒父的懸崖邊緣被拽拉了回來。牛家三姐弟的野蠻生長源于父性失位和秩序混亂,《后悔錄》中“我”的力比多狂熱更顯示出這種狂熱的“革命”情結的極端化發展。但是,當“我”意識到自己照顧父親的責任感如此之重大時,“我”不得不審視“父”的存在之于自己的意義,實際上就是對“文革”里推翻一切、打倒一切的質疑和反思。
審視父親以及父性的價值,不僅可以置放在歷史的罅隙間,而且同樣可以將它和時代熱點并置,進而觀照在疾駛的時代巨輪下,父性在場域位移和文明變遷的過程中的尷尬境遇。小說《篡改的命》通過新世紀中國城鎮化背景中“農民進城”和高考被人頂替的網絡熱點問題,剖析了父親以及父性在新世紀遭遇的時代苦難。小說通過兩個父親的際遇,思考了生存之痛和生命之悲,當汪長尺承繼著“光宗耀祖”的父訓,將自己的親生兒子移植到城里,成為仇人名義上的兒子時,心中百感交集。小說的最后,是汪長尺的兒子汪大志去追查自己的身份,以血緣上的繼承人的身份,替父還鄉,實際上正是以新一輩人的觀點,去審視父親,以及父親的父親,還有汪家祖祖輩輩生存的鄉土。雖然小說戲仿了俄狄浦斯的故事情節,但是個中人物卻背叛了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林方生也就是汪大志把記載著自己身世的檔案扔進了邕江里,顯示出他和這段身世和血緣關系的決絕之心。東西用不能再殘忍的事實告訴讀者,城市文明已經無情地吞噬了鄉村文明和鄉土歷史,在市場經濟時代,在物質條件下異化的人文生態對血緣、親情以及倫理道德的踐踏,已經變得無以復加,正如論者所指出的,“《篡改的命》對存在之境的考辨,就是去察看從鄉村到城市所經歷的制度及文化的碰撞,鄉村人必然所經歷的一種思想及行為、人性及意識的蛻變,簡單地說,就是在這種境遇中他們是如何應對的,是怎樣一種在世的方式。”
3 結語
借助于尋父的敘事脈絡,作家東西導引出歷史運行的秩序以及社會運行規則的反思問題,而父親與父性的時代遭遇,更是新時期社會秩序重組給人帶來的生活經驗以及心靈感悟。裹挾在歷史際遇和時代特征里的父性價值反思,體現了作家對文化傳承以及社會價值走向的深刻思考,它必將隨著厚重的歷史和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走進更為深刻的藝術探討層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