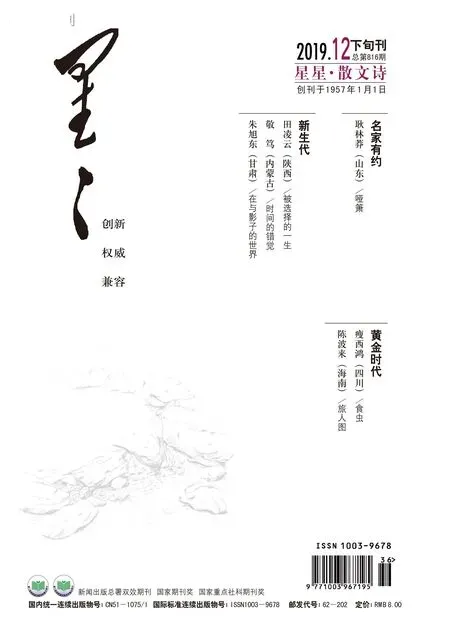不老的,不止流水(三章)
——懷念姥姥
2019-12-29 05:48:15黃鶴權福建
星星·散文詩 2019年36期
關鍵詞:流水
黃鶴權(福建)
姥 姥
你的身體正在變成沙漠。你發明了人人畏懼的啰嗦術。等著我,在你面前掉眼淚。寬闊如一條沉重而陌生的赤道。
姥姥,風吹紙甚于紙嘆息。
地址簿中的標記,還記得嗎?拿星星擦亮眼睛,等你凱旋。
不老的,不止流水
不老的,不止流水。那些五味雜陳,那些一株茅草似的命運,那些木槌鑿開的蜜和白云,正從沉重的夢魘中醒來。端端正正,又大,又亮,都做了消逝的土。
只有那些白色淚滴,薄薄的,沒有分量。無所依持,更無需交代,不停地奔返這春天的光亮。那么努力。
仿佛,能爬過一個八十三歲老年人的一生。喚來一句乳名朝向圣潔的一面。
日 落
遠山入斜陽,那是什么樣的飛翔啊。在水韻里的余暉,那又該是什么樣的暢想。
此刻,端坐在時間的裂紋里。遠遠的,一小片前生的蜜糖,正冒著亮光直挺而孤絕地聳立于墳地之上。
它的真實仍可預見,它的高眉婉轉地唱著。有鵝毛般小,漢白玉般澄明的情愫。它是屬于此地十萬異鄉人的專利。連飽滿的腹部,也有可供啞語行駛的另一條航線。可替我找到生銹的鹽分和春雷。
猜你喜歡
故事作文·高年級(2025年7期)2025-07-27 00:00:00
云南畫報(2021年8期)2021-12-02 02:46:08
文苑(2020年10期)2020-11-07 03:15:26
揚子江(2018年1期)2018-01-26 00:36:54
天津詩人(2017年2期)2017-11-29 01:24:12
數位時尚(幼兒教育)(2017年6期)2017-07-18 11:47:56
視野(2015年6期)2015-10-13 00:43:11
六盤山(2015年3期)2015-06-29 12:26:37
火花(2015年1期)2015-02-27 07:40:13
海峽姐妹(2014年5期)2014-02-27 15:0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