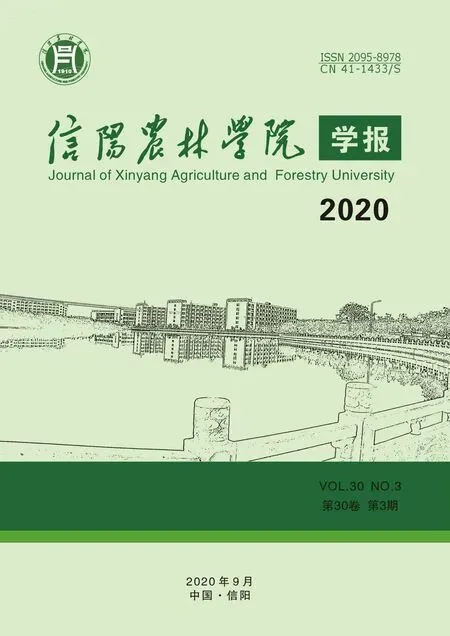毛姆筆下的海外中國人形象
——以《阿金》《葉之震顫》兩部短篇小說集為例
王夢瀟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英國文學作品中常常出現對中國的想象和認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人的形象在英國作家的筆下不斷變化,這種形象的復雜變化在20世紀的英國文學中尤其明顯。19世紀末,黃禍論興起,英國作家對中國的否定性描寫占據主流。但一戰爆發后,許多西方人對自身文明的前途生出憂慮之情,想要去往遙遠的東方國度尋找出路。毛姆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了東方,踏上了中國以及周邊的許多國家的土地,想要在這里找到他理想中的東方國度。
毛姆在很多作品中都塑造了中國人的形象,但其被研究較多的幾部作品,如《彩色面紗》《在中國的屏風上》等的故事背景都是中國。這種設定雖然能更加詳盡地展現中國人的在地形象,但或多或少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而《阿金》和《葉之震顫》兩部集子中的短篇小說都不是以中國為故事展開的背景,《阿金》的故事背景是馬來西亞及周邊地區,《葉之震顫》的故事背景是太平洋地區。這就讓我們有了另外一個研究角度,即在毛姆筆下,中國人在世界范圍內處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此外,在這兩部作品中,中國人都不是最主要的角色,大多數是毫不起眼的配角。在文學作品中,配角往往只是功能性的人物,但正是這樣的特性,使得毛姆減少了對這些中國人的人性共同層面的挖掘。這樣的角色設定讓中國人的形象更像是作為一個符號而存在,這就更能顯示出,中國人在一個多民族混雜的地區的處境。我們可以以此探究,在毛姆眼中,中國人在異國是以什么樣的身份、形象、姿態存在的。
1 毛姆筆下的海外中國人形象
1.1 身份
在這兩本短篇小說集中,中國人大多以下等人的身份出場,其中,仆人和廚子是出場頻率最高的中國人形象。在《阿金》的序言中,作者告訴我們,阿金是毛姆在游覽馬來半島及周邊地區時的中國仆人,這部短篇小說集也以這位中國仆人的名字命名;而在《麥金托什》和《火奴魯魯》中,毛姆都塑造了中國廚子的形象。在《阿金》和《葉之震顫》這兩部短篇小說集中,仆人、廚子前幾乎都要加上“中國”兩個字,仿佛在毛姆筆下,這兩個職位是中國人專屬的。
中國仆人和中國廚子的設定顯示出了毛姆眼中的海外中國人的地位,即白人的附屬品。一方面,這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絕大多數中國人在異國都難以找到理想的位置,而只能處于下等階層。另一方面,這也顯現出中國人在他者眼中的形象。雖然毛姆反對殖民,但他畢竟是英國人,流淌在他血液中的種族優越感是無法磨滅的。在他看來,在一個多民族混雜的區域,處于主導地位的還是白人,而中國人只能處于附屬地位。當然,從毛姆對廚子的中國人身份的定位,我們也可以推測出毛姆對中國食物是比較喜愛的。
再者,中國商人也有在這兩部短篇小說集中頻繁出場,但毛姆沒有對他們進行過多的刻畫,我們只能看出,在毛姆眼中,商人是中國人形象的典型代表。在《阿金》一集的《叢林中的腳印》中,毛姆寫到中國商人的房屋體量之大和中國海外商人之多;在《窮荒絕域》和《尼爾·麥克亞當》中,他都有對中國商鋪的描寫。在《遭天譴的人》中,中國商店只是作為金格·臺德事件的爆發地點出現,沒有什么特別的敘述用途,而這個“中國佬”也只是作為功能性的人物出場。但毛姆下意識地會將商店設定為中國人開辦的,可見,中國人與商人常常聯系在一起講,中國海外商人在毛姆筆下的典型形象便可想而知了。毛姆偶爾也會寫到中國商人的狡猾,寫年輕人受到中國人的哄騙,買了一些沒有用處的東西。這大概是源于西方人對中國商人的固有印象。
除此之外,海外中國人還以妓女和中國醫生的形象出現在這兩部短篇小說中。毛姆對中國妓女的描寫并不友好,相比較他筆下日本妓女的體貼周到,中國妓女骨子里仿佛透著一股冷漠感,有種排他的傲氣。
1.2 體貌
關于中國人的外形,毛姆在《阿金》和《葉之震顫》中有幾個典型的描寫,這些描寫也體現了毛姆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
首先,毛姆筆下的中國人個頭矮小。他描述阿金個子很矮,《叢林中的腳印》中撿到懷表的中國人身材矮小,還有著羅圈腿。這些都表現了毛姆內心的種族優越感,他對中國人身材矮小的刻畫來自于潛意識中對中國人的矮化。再者,中國下等人民在毛姆眼中是落后的、未開化的。他在《麥金托什》中描寫中國仆人是“光著腳板”的。從某種層面上講,衣著完整其實是一個人文明的表現,而這里對中國仆人光著腳的形象的刻畫,表現了毛姆眼中的海外下層中國人文明程度是很低的、較為原始的。
而對于注重打扮的中國人,毛姆的敘述口吻也是頗為貶斥的。在《火奴魯魯》中,他寫道:“再就是中國人,男人一個個肥胖闊綽,穿著古里古怪的美國式衣服。”或許在毛姆眼中,中國人就應該維持他們的樸素、未開化的原始形象,當他們學習“文明”的西方人的穿著,或是化上妝的時候,就丟掉了他們本身最為純粹的東西,變得面目全非了。這也許與毛姆對中國古老、神秘的想象有關。他不希望現代化的東西污染了純凈的中國人,因此,當看到中國人的現代化裝扮的時候,便會心生厭惡。
1.3 性情
首先,在毛姆筆下,海外中國人,尤其是底層的勞動人民,是不愛多嘴、默默埋頭做事的。他在《阿金》的序言中寫阿金“做事干凈利落,不愛多嘴說話”。在《葉之震顫》中的《麥金托什》寫中國廚子總是一言不發地在做事情。在《火奴魯魯》中他又寫道:“愛吃苦的中國人和狡猾的日本人便從他們手上奪走了生意。”毛姆對海外底層中國勞動人民性情的評價比較高——他們不愛說話,但很能吃苦,默默地為主人完成所有的事。
其次,毛姆常常把中國人與犯罪聯系在一起。在《叢林中的腳印》中,布朗森的死亡一度被認為是“中國人”干的。“中國人”在這里被懷疑為殺人犯,不是因為布朗森與中國人有什么瓜葛,而是在當地人眼中,“中國人”經常干出搶劫殺人的事情。然而,這一案件真正的殺人兇手并非中國人,那么我們可以猜測,這或許是毛姆為了讓西方人反思自己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而作出的設定。
再次,毛姆還認為中國人是類型化的,缺乏變化的。他們沒有西方人性中復雜的一面。在《阿金》的序言中,毛姆寫道:“他們多少都缺乏變化……他們的古怪表現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以說,在他眼中,中國人的人性是較為單薄的。這表現了毛姆對中國人的復雜情感——一方面對中國人未受污染的淳樸性情表示贊賞,另一方面又不自覺地流露出自己的種族優越感。
當然,毛姆眼中的中國人形象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他與中國人接觸的深入而有所轉變。最初他認為,中國人是神秘的東方人,是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的生物,他們沒有什么復雜的情感,并認為阿金除了把自己當作雇主之外,不會對自己有什么別的感情。彼時,在他眼中,中國仆人不過是用以交易的物品、為己所用的服務者。但他沒有想到,阿金在離開他的時候,竟因為不舍而流下了淚水。這時,他才意識到,中國人也是像西方人一樣有感情的生物,他們的感情比西方人更純粹、更真誠。
在這兩本短篇小說集中,毛姆經常借西方人對中國人的預設和中國人的實際表現之間的落差,來表現自己對中國人印象的轉變。同時,他也以此糾正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2 毛姆筆下復雜的海外中國人形象產生的原因
2.1 集體想象的無意識
經過長時間的歷史積淀,英國已經形成了一個集體想象下的中國,但“集體想象又不是一成不變的”,英國人視野中的中國人形象是游移不定的,這與不同歷史時期英國的處境、中國的地位、兩國的關系以及交流的方式都有很大的關系。因此,英國集體想象下的中國是相當復雜的。毛姆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其對中國的想象也會因此受到影響。
2.1.1 西方優越論 雖然毛姆對中國是充滿興趣的,對殖民文化也是厭惡的,但是,從小在西方長大的他,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早已產生了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印象,難以避免受到集體想象的影響。“當我們掀起遮在毛姆中國形象上的那塊彩色面紗,源自于西方優越論的自負心理也就展現無疑了。確實,無論如何,毛姆都難以逃過那傲慢與偏見的文化心態。”[1]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政治、經濟地位都大不如前,西方列強在侵略、壓榨、控制中國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讓他們認為自己是比中國人高一等的民族。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長大的毛姆也深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因此,他會不自覺地用一種俯視視角觀照中國人。或許他對自己這種居高臨下的視角是不自知的,但從他的作品中,我們的確能讀出微妙的種族優越感。
2.1.2 黃禍論 1893年,英國歷史學家皮爾遜(Charles H. Pearson, 1830—1894)發表了《民族生活與民族性:一個預測》(NationalLife and中racter,A Forecast)一書,在書中,他反復強調以中國人為首的有色人種的“可怕”之處。這使得“黃禍論”席卷西方,西方人對中國人產生了普遍恐懼的心理。此后,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 1883-1959)在13部傅滿楚系列小說中塑造了險惡的中國佬形象,加劇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恐懼心理和厭惡情緒。
處于同一時期、同一國度,毛姆不可能不受到這兩位英國人的影響。在他的作品中,也會不時地流露出西方人對于中國人的恐懼,將中國人與犯罪聯系在一起。但毛姆并沒有陷入到“黃禍論”帶來的恐慌中,他在與中國人接觸后,認識到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這種看法是一種偏見。因此,在他筆下,中國人不是真正的兇手,中國苦力的暴動輕易就被鎮壓了。毛姆的這些敘述都表現了他對中國人印象的轉變,也顛覆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固有認知,糾正了西方人因為“黃禍論”對中國人產生的不必要的恐懼。
2.2 個人經歷的影響
2.2.1 童年的不幸遭遇 毛姆的童年是不幸的。在他8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兩年后,父親也過世了。此后,他寄居在叔父家,叔父對他很冷漠,家境又很是貧寒,這使他的童年過得非常凄慘。11歲的時候,他被送去學校讀書,身材的矮小和口吃的毛病讓毛姆在學校受盡了嘲諷,他倍感孤獨,也變得異常敏感。
童年的不幸讓毛姆更能體會到不幸之人的情感,從小就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他也更能理解底層民眾的處境。因此,他在觀察生活在苦難中的海外中國人時,常常抱著悲天憫人的情懷。他欣賞中國仆人與廚子不愛多嘴、能吃苦的品性,用人文主義悲憫著無休止勞動著的中國人,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勞動人民有著深沉的同情和敬意。因此,在毛姆的筆下,生活在最底層的海外中國勞動人民沒有喪失對生活的熱情和信心,他們不屈不撓地與艱苦的生活和自然環境相抗爭。
2.2.2 哲學思想的影響 毛姆的叔父是一名牧師,而這是一位極其自私的牧師,讓毛姆在童年時期就對基督教產生了質疑。隨著年歲增長,苦難與不幸讓毛姆用一種更為悲觀的態度審視生活,無數次祈禱未果后,他不再相信基督教,甚至對基督教嗤之以鼻。在毛姆不斷求索的過程中,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使毛姆產生了共鳴,而叔本華對東方哲學的推崇則讓毛姆對東方充滿了向往。于是,東方就成了毛姆尋求智慧的方向。
2.3 對西方文明的反思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西方工業文明的弊端被完全暴露出來,一部分西方人對自身的文化產生了質疑,毛姆也因此感到不安,他想從東方文明中尋找出路。
毛姆來到中國之前,已經在心里有了對于中國的想象,雖然中國不像他想象得那般古老、神秘、輝煌,但他還是會帶著這種眼光去審視中國。他在一定程度上無視了東方的現代化,認為中國人是落后、原始但又淳樸、真摯的人,這種頗具選擇性的描述與毛姆塑造中國人形象的目的之一有關,即與西方人形成對照,用中國文化彌補西方文明的缺失。
他在《阿金》的序言中寫阿金不緊不慢、有條不紊地做事,寫阿金總是在最后一刻登船,寫阿金被罵還笑嘻嘻的,并將阿金的這種慢節奏和自己的急性子進行了對照;他又在許多篇目中都寫了中國仆人安安靜靜、勤勤懇懇地工作。他用中國人的安靜、平和、舒緩與西方工業社會的浮躁進行對比,進而否定西方文明。在他看來,工業文明壓抑和扭曲了人性,西方人的自然本心在不斷膨脹的物欲之中逐漸喪失,而東方文明是沒有受到工業文明污染的一片凈土。在毛姆筆下,中國人在沒有被工業文明玷污的東方文明的庇護下,身上有著那種最為淳樸的、未開化的情感。這在毛姆看來,是難能可貴的。“中國形象也作為文化‘他者’參與塑造了西方文化的‘自我’”[2],毛姆塑造的作為“他者”的中國形象就是對西方“自我”殘缺部分的補充,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人形象是毛姆的心靈投射。
3 結語
毛姆對中國的認識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毛姆與中國人接觸的深入,他對中國人的認識也逐漸深入,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對中國人的看法也有所轉變。在來到中國之前,毛姆可能會受到西方身份的影響,以俯視的視角觀看中國人;可能會受到英國傳統文學對中國浪漫、輝煌、神秘想象的影響,對中國人有烏托邦式的想象;可能會受到19世紀黃禍論對中國丑化的影響,將中國人與犯罪相連。但經過對中國人的近距離觀察,他有了新的理解。他看到,中國人也是和西方人一樣具有人性的、真正意義上的人。雖然毛姆無法避免地受到集體想象的影響,但他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駁斥了19世紀以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