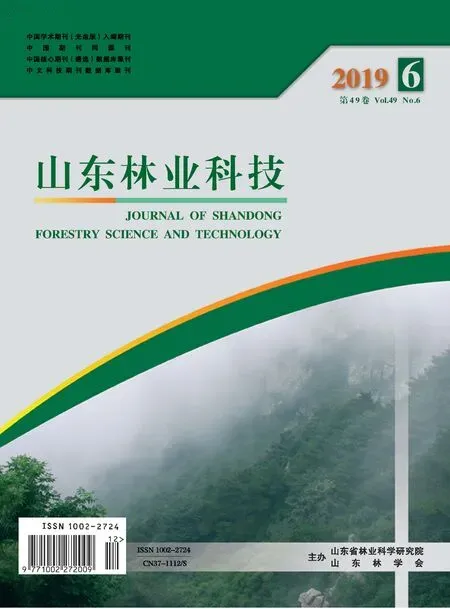基于形式美法則的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探析
黃云暉,張 云
(西南林業大學園林園藝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4)
1 引言
位于云南滇南文化中心的建水文廟,始建于公元1285年,至今已有700多年歷史,占地面積達7.6hm2,規模宏大僅次于山東曲阜,“規制宏敞,金碧壯麗,甲于全滇”[1]。它仿照曲阜孔廟的形制建造,平面為中廟左右學布局,整體上坐北朝南,縱深625m分布著 1殿、2廡、2堂、2閣、5祠、8坊等建筑,圍合成其建筑空間[2]。建筑空間包括屋頂、墻體、地面圍合的內部空間、與周圍環境形成的外部空間,以及介于兩者之間起過渡作用的灰空間。本文是對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進行研究。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指的是建水文廟中的坊、門、壇、廟、祠、堂、廊、亭等建筑單體及其墻體圍合成的且與環境相聯系的空間。筆者認為,建筑只有同環境即外部空間融合成一體時,才能顯示出價值與表現力。從這一點上看,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也是彰顯儒家文化精神的重要場所,具有研究價值。其次,任何空間自身都具有美的形式,符合一定的形式美法則。本文首先對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的整體格局、單元構成、組合形式及序列進行了論述,再運用形式美法則的多樣統一、主從關系、對比與均衡、節奏與韻律、比例與尺度五個方面去探析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的美,反映其中倡導中的以人為主這方面的儒家文化精神。
2 建筑外部空間的界定與內容
老子曾說“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是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3]。形象描述建筑實體與空間的辯證關系。建筑空間是人所使用的,是有所限定的。建筑外部空間亦是如此。蘆原義信說:“外部空間是從自然中框定的空間,是由人創造的有目的的外部環境,是比自然更有意義的空間”[4]。所以建筑外部空間指的是依附于建筑而存在,與自然環境相聯系,由各種建筑、植物、園林小品等構成,體現文化精神的場所。從這點看,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是其中各種建筑物所圍合形成的院落空間,其中蘊含著人倫禮制等儒家思想。
任何建筑都勢必處于一定的環境當中形成和諧統一的整體布局,由此獲得順乎自然、蘊含人文內涵的空間美,所以建筑外部空間極為重要。一個建筑外部空間單元通常由建筑、墻體、植物、地面、構筑物以及人的行為心理等要素構成,各要素間相互獨立又緊密聯系。建筑外部空間能夠反映平面整體布局,往往通過空間組合形式與序列去表達。建筑外部空間的組合形式是指若干外部空間單元通過某種方式去銜接成一個整體,通常具有兩個典型組合形式:一種是以空間包圍建筑物,簡言之即開敞式空間;一種是建筑實體圍合而成的空間即為封閉式空間[5]。建筑外部空間的序列是指按照空間功能將多個外部空間合理組織起來構成有秩序感的空間關系,它使外部空間巧妙連接起來,從而表達空間美。
3 形式美法則與建筑外部空間的關系
形式美法則是人類在創造美的形式與過程中對規律的經驗總結和抽象概括。它是自然、生活、文化藝術中美的外在呈現,通過有規律組合點、線、面、體等各種形式元素能使創造物擁有視覺美感[6]。形式美法則包括多樣統一、主從關系、對比與均衡、節奏與韻律、比例與尺度五個方面。其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任何藝術領域都能夠被運用。多樣與統一是它的基本規律,它是構成整體和諧的前提,其他四個方面最終也要回歸到多樣統一。通過明確、秩序、勻稱與和諧的感性形式去探析建筑外部空間,能使人在變化空間中獲得視覺、心理美感,從而與外部空間形成一種共鳴,獲得與環境的最優化。

圖1 建水文廟總平面圖Figure 1 General plan of Jianshui Confucian Temple
4 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
4.1 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的整體布局
中國傳統建筑講究山水環繞。在建水文廟南面有一山脈稱煥文山,其借景入文廟,在空間開闊的學海中形成倒影,景色宜人,構成了建水文廟的山水格局。文廟是儒家文化主導的產物,亦與所建地區本土文化交融,它的建筑形制和空間形態在各時代背景發展過程中逐步完善,并形成秩序儼然、和諧統一的整體布局[7]。在建水文廟整體布局中,建筑結合其外部空間構成“點”,人行進道路為線進行串聯,由線串點,以點帶面,遵循儒家文化中“禮者,天地之序也”的嚴格禮制,以中軸線中祭奠孔子的先師廟及外部空間為主,左右側軸線為輔。從而形成中廟左右學的富有空間邏輯美的平面整體布局(圖1)。
4.2 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單元構成
建筑外部空間單元是整體外部空間的基本構成,其內部都有特定構成并形成單元特性。建水文廟的外部空間單元是構成各院落空間及中廟左右學平面布局的基礎,主要是通過坊、門、壇、廟、祠等建筑單體及其墻體圍合形成,其構成要素包括通過踏步、鋪磚、材料進行變化的地形、歷經千百年風雨的古樹名木、體現儒家文化思想與建水當地文化融合的小品等裝飾藝術,以及活動其中感受空間美感與儒家文化交融的人(圖2)。每個獨立空間單元之間通過構成要素相互獨立又彼此聯系,從各自不同的特性中形成統一。

圖2 二賢祠、古樹、道路鋪磚等構成空間單元(圖源:《千年名府——建水》)[8]Figure 2 A space units composed of the Temple of Two Square Sages,ancient trees,paving bricks(Source:《The Millennium Masters-Jianshui》)[8]

圖3 洙泗淵源坊半月形唇臺外部空間(圖源:作者自繪)Figure 3 The outer space of the halfmoon shaped lip table of the Zhusiyuanyuan(Source:author self-painting)
4.3 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組合形式
建水文廟外部空間形式有三種:一是由主體建筑、廊道、門、道路及植物圍合形成,有欞星門、先師廟以及東明倫堂的外部空間;二是由幾組建筑、門形成合院空間,有杏壇所在空間及新建文廟廣場;三是由坊、門及相聯系的景觀物圍合形成,有太和元氣坊、洙泗淵源坊的外部空間。三種外部空間形式相互穿插,通過融合、滲透、對比、序列連續等顯示其中特定的功能和儒家文化,構成建水文廟規律且豐富的外部空間組合。
4.4 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序列
空間序列是將一系列不同形狀、性質的空間按一定觀賞路線有序地貫穿、組織起來[9]。“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儒家思想的表現形式,反映在建水文廟外部空間中則是形成起承轉合的序列。“不學禮,無以立”禮樂秩序強調外部空間中的人際倫理規范,形成空間莊重肅穆的氛圍。
4.4.1 起—緣起儒學,引入圣域
從太和元氣坊及其萬仞宮墻圍合形成引導性入口外部空間,通過其中兩側有石碑書“建水文廟”強調了其引導感,距坊門30m處正對一尊高3m的孔子作揖雕像,起到點明空間主題與“開門見像”之意,避免了整個建水文廟空間一覽無余,同時賦予文廟一絲神秘感;由太和元氣坊進入取自“學海無涯苦作舟”的廣闊學海,面積30015m2,形狀為南北長東西短的不規則橢圓形[10],空間即顯開闊,給人震撼的直觀感受,北端有一小島通過三孔橋與岸邊相連,島上建有思樂亭形成空間中的視覺焦點,泮池兩岸植有高大香樟樹與榕樹,彰顯君子“比德”[11],池中植荷花,以“思樂泮池,薄采其芹”意喻孔子思想“孔澤流長”,此空間功能在于表達對孔子儒學的崇敬之情。

圖4 洙泗淵源坊與思樂亭成對景(圖源:《千年名府——建水》)[8]Figure 4 Zhusiyuanyuan Square and Sile pavilion in pairs(Source:《The Millennium Masters-Jianshui》)[8]

圖5 “進禮門,行義路”的禮門、義路坊(圖源:《千年名府——建水》)[8]Figure 5 Limen,Yilu Square from“Enter the door of etiquette and take the road to justice”(Source:《The Millennium Masters-Jianshui》)[8]
4.4.2 承—感受儒學,延續場所
沿泮池兩邊至其最北端,是由洙泗淵源坊及東西“鳶飛魚躍”墻、禮門、義路以“環抱式”圍合形成半月形唇臺外部空間(圖3),尺度為30m,與高10m的洙泗淵源坊形成舒適的視覺觀賞角度,洙泗淵源坊與思樂亭形成對景(圖4),此外部空間的尺度感有所收攏,給人以舒適之感的同時彰顯其莊嚴靜穆。在此空間中,依照儒家文化規范人的行為方式,通常是“禮門”進“義路”出,表示君子應“進禮門,行義路”(圖5),即要尊禮守義,給人莊重的精神儀式感;由于圣域由茲—德配天地—道貫古今—賢關近仰四坊呈東西方向相互滲透,拉長了人的橫向視線感,在四木雕柱穿脊而出的欞星門這一獨特建筑的展示前,兩邊方形地塊植側柏植物群夾合形成外部空間視線的聚合點。圣域由茲意思就是圣賢之地由此進入,故在此又開一門造有“天圓地方”建水孔子文化廣場,象征天人合一,以及從古至今對于文人君子的尊崇。
4.4.3 轉—崇敬儒學,形意相通
由欞星門進入以杏壇為視線中心的外部空間(圖6),十字形道路分割的高大植物群落地塊聚攏到杏壇,銀杏高雅,古木蕭森,形成肅靜之境,讓人感受置中的杏壇不張揚。杏壇,即環植以杏,原是孔子講學之地,在建水文廟中在栽植銀杏以還原環境,其空間功能在于傳播儒家文化思想,象征有教無類之精神。杏壇方形外部空間上角是金聲玉振門,分別通往東西明倫堂,即建水州學、臨安府學所在地,而向正北則通往主體空間先師廟。從講學之所滲透延伸至中廟左右學所在地,在時空上進行了轉化,由此升華空間意蘊,進一步以空間語言傳遞儒家文化思想,教化當地民眾。
4.4.4 合—升華精神,呈現主體
儒家思想中強調禮制,等級嚴格,強調“尊者居中”。建水文廟外部空間的主體是先師廟、大成門及其東西兩廡、兩碑亭緊密圍合形成的封閉空間,此外部空間中又以九級踏步與高浮雕云龍紋丹陛石形成的臺基御路分割上下兩空間,以垂直交通聯系空間使其得以抬升形成垂直空間的態勢,即韻律感,從而顯示等級。上空間為體量碩大的先師廟的拜臺空間,中間有一乾隆銅鼎,其造型符號采用龍與象,象征儒家文化與滇南文化的融合,該空間主要功能是祭祀孔子,建水當地通過在此舉行三獻禮表達對孔子及儒學的崇敬之情,同時,拜臺空間將先師廟抬升,在下空間訪進時人的心理形成一種高大莊重的尺度感,突出顯示其莊嚴肅穆,秩序儼然。下空間周環回廊,巍峨壯麗。古樹柏木,“象呈太平”、銅鼎香爐、祈福榜等小品及地面踏步變化構成了此外部空間的觀賞性,兩邊兩廡供奉有歷代以來儒學先哲,稱四配十二哲,亦是空間中的精神文化元素,構成此空間的主體完整性。
4.4.5 尾聲—心靈回歸,空間感悟
建水文廟以崇圣祠外部空間收尾,其是供奉孔子五代祖先、四配及五賢之父的場所,與先師廟相對,彰顯儒家“孝”文化。其背后是圣林,更是營造了一片祥和寂靜之感,在訪進至此之人心靈在儒家文化思想浸染下回歸一片凈土(圖7)。

圖6 建水文廟杏壇外部空間——文昌閣(圖源:改繪自《千年名府——建水》)Figure 6 The outer space of the Apricot Altar at the Jianshui Confucian Temple (Source:Repainted from《The Millennium Masters-Jianshui》)

圖7 建水文廟崇圣祠旁的倉圣祠、二賢祠(圖源:改繪自《千年名府——建水》)Figure 7 The Temple of Cangjie sage and the Temple of Two Sages,next to the Temple of Worship sage in Jianshui onfucian Temple (Source:Repainted from《The Millennium Masters-Jianshui》)
5 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形式美法則的特點
5.1 多樣與統一呈現外部空間和諧美
多樣與統一是形式美法則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在統一中求變化,在變化中求統一[6],其通過形式美另外四條法則加之呈現。在平面布局上,建水文廟外部空間呈現多樣的空間形狀,以方形為主,如各個院落空間,還有半月形的唇臺,不規則盾形的泮池以及梯形的孔子文化廣場,而最終歸于“天圓地方”思想,通過路線的組織使其形成統一的平面。在空間序列上,建水文廟外部空間的開合、虛實、大小不斷變化,同時相互以門坊、門樓、植物等相互滲透形成統一軸線,以特定功能彰顯不同等級,反映儒家思想中“不可僭越”的嚴格等級秩序。在構成要素的獨特性方面,建水文廟外部空間以不同要素如廊、亭、小品、植物、鋪裝以及人的行為心理構成了其多樣性,而“天人合一”思想最終將各要素組合成統一的空間單元(圖8)。

圖8 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多樣與統一(圖源:作者自繪)Figure 8 Diversific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external space of the Jianshui Confucian Temple(Source:author self-painting)
5.2 主從關系反映靜穆中彰顯的莊嚴之勢
在若干要素組成的整體中,每一要素在整體中所占比重和所處地位,將會影響到整體的統一性[5]。在建水文廟中,以一系列外部空間組合來說,通過空間態勢呈現的變化,即可確定某一空間的主體地位。先師廟是整個文廟中的主體,而其外部空間則是文廟建筑外部空間組合中的主體,所以其他空間的存在都是為先師廟所在空間服務的。首先,在建筑空間中,圍與透是相對的,其可以用來反映空間的主從關系,先師廟外部空間以建筑圍合成一個閉合空間,僅留大成門與其他空間相滲透,而其位于南北軸線序列的終端,各空間相互滲透最終聚焦此空間,由此構成其空間主體地位。其次,先師廟在外部空間態勢中的處于高潮部分,通過裝飾等的復雜程度,以及九級踏步至拜臺抬高建筑,使人置身其中具有與眾不同的生活、心理及文化藝術感受,由此彰顯主體莊嚴之勢。而以具體某一空間來說,建筑外部空間都是作為從屬空間服務于主體建筑,其與建筑的關系對比又體現空間主從關系。在五進外部空間中,四周以文昌閣、魁星閣(遺址)、名宦祠、鄉賢祠、金聲玉振門等建筑群圍合成院落空間,杏壇置于幾何中心,有兩層臺基,高度為10.3m,是整個空間中視線最高點,體現其主體地位。四面留有足夠的視距觀賞,南北約為25m,符合中國傳統的“千尺為勢,百尺為形”形勢觀[12],以道路及兩邊栽植銀杏、無患子等植物引導視線,杏壇體量與所植植物尺度適宜,構成和諧的主從關系,營造出肅靜祥和之感。

圖9 建水文廟外部空間方向性對比(圖源:作者自繪)Figure 9 Directional comparison of external shape of Jianshui space of Jianshui Confucian Temple

圖10 建水文廟外部空間形狀對比(圖源:作者自繪)Figure 10 Contrast of external space Confucian Temple
5.3 對比與均衡中產生穩定感
建水文廟外部空間的對比可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述。一是方向性對比(圖9),通過建筑的朝向營造不同的方向感受,把具有豎向感覺的泮池空間、先師廟外部空間與具橫向感覺的圣域由茲—德配天地—道貫古今—賢關近仰四坊外部空間、杏壇外部空間等交替穿插,讓人在行進中體驗方向不斷變化的空間感,而各外部空間適宜的組合又使空間平穩、舒適,產生均衡感。二是形狀對比(圖10),建水文廟多樣的外部空間形狀讓人在感受中體驗不同,通過適宜的路線的組織又使平面獲得均衡。在對比與均衡中感受外部空間美學與生活體驗,同時滿足了文廟祭祀與教育的功能需求。

圖11 建水文廟外部空間態勢——南北剖面圖(圖源:作者自繪)Figure 11 External Space Situation of Jianhui Confucian Temple-North-South Section Map
5.4 節奏與韻律構成時空秩序
節奏與韻律源于音樂和詩歌,指按一定秩序和規律組織變化去激發美感[13]。這在中國建筑空間構圖中往往成就了節奏化、音樂化的“時空合一體”[14]。而當它運用到建筑外部空間時,則構成了一種和諧的外部環境,通過時間、空間的推進,以及人在其中的活動去營造獨特的空間韻律與節奏,激發空間美,產生認同感[15]。建水文廟外部空間以尊孔祭祀、禮樂教育等特定功能為引導,各外部空間通過門坊、門樓及高大植物進行多空間多層次之間的滲透,從而產生外部空間組合中的變化與聯系。首先,建水文廟的每一處建筑每一進外部空間,其形成都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積淀、逐漸完善而來的。文廟祭祀孔子的場所,至今保留著傳統的祭孔儀式,如三獻禮、開筆禮、成童禮、成人禮等,儀式所遵循的嚴格秩序在每一進外部空間獲得呈現,例如“進禮門行義路”,以及在東西碑廊、兩廡感受千古風流人物與紀事,人的活動構成其中撥動的弦,在感受千年時空律動的同時激起精神層次的起伏,相互交織構成空間節奏與韻律(圖11)。
5.5 以尺度與比例構建人與外部空間的交流
空間借由長度、寬度、高度、大小表現出來,以各種參數構成物質與精神的場所[4]。每處建筑的營建,無論單體還是整體空間,都需要有和諧的尺度與比例,才能讓人身處其中感受到美的精神意蘊的存在。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中,整體的比例與尺度是嚴謹和諧的,整體的尺度感是莊嚴靜穆的,讓人身處其中感受到與建筑空間的對話,體會到其中嚴格的秩序感卻不感到壓抑,耳濡目染其中的教化意蘊進而轉化為自身的行為準則。其處處體現人的尺度感,注重與人的交流。根據20~25 m為模數的“外部模數理論”。25 m左右的空間尺度是社會環境中最舒適和得當的尺度[16]。
從整體看,建水文廟的外部空間尺度關系中具有舒適尺度,每處院落空間的觀賞距離約為25~30m,視距與建筑物的高度比D/H約為2.5,合仰角約為22°。用傳統的形勢觀來看也是符合形式美學的。從總平面來看,建水文廟構成了大、中、小尺度外部空間關系,泮池為尺度外部空間、孔子文化廣場為中尺度外部空間、其余院落為小尺度外部空間,三種尺度空間之間互滲共生,在對比中產生和諧舒適的空間關系。在和諧比例上,泮池面積之大,約30015m2,占總面積40%,其北端約三分之一處建有“思樂亭”一島,由一座三孔石橋與堤岸相連從而分割泮池成大小兩個空間。這一分割符合“黃金分割構圖法”,由此呈現這一壯闊外部空間的和諧比例與尺度的美感,處于分割線上的思樂亭與三孔橋,亦成為人們的視覺焦點。
6 總結
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遵循普遍的形式美法則,達到了空間美與祭孔傳儒功能內容的和諧統一。本文通過運用形式美法則對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進行探析,得到以下特點:(1)其偌大的學海將煥文山倒影納入文廟中,形成獨特的山水格局。(2)“禮者,天地之序也”其遵循嚴格的禮制,以道路為線串聯各個外部空間形成整體,其中突出中廟軸線,再輔以左右側軸線,形成中廟左右學的富有空間邏輯美的平面整體布局。(3)以祭祀孔子、傳播儒學教育的功能內容為引導,形成嚴格等級秩序的外部空間序列,相互滲透,層層推進,將先師廟及外部空間置于高潮部分突出主體地位,而人“在社會參與中進入意義世界”,在參與空間營造的過程中感受空間美的內涵而獲得精神層面的升華。與此同時,人在空間中的祭祀行為以及對儒學的尊崇,反過來造就空間的精神內涵,“建筑以載道”,使其外部空間傳達著儒家的教育精神。(4)其以多樣的空間平面形狀、空間形態、空間構成在統一中求得變化,最終形意相連,在“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指導下歸于統一。第一,通過先師廟及外部空間主體地位彰顯莊嚴之勢點明文廟主題,加以從屬空間構成鮮明的主從關系;第二,從外部空間方向、形狀方面的對比中獲得整體空間的均衡感;第三,由外部空間態勢的起伏變化構成起承轉合的節奏韻律;第四,以比例尺度的和諧給人不同的心理感受體驗靜穆與莊重。
從形式美法則的五個方面探析建水文廟建筑外部空間,挖掘其中濃厚的儒家文化與莊嚴靜穆的空間氛圍營造之間的聯系,以及這種聯系作用于人的行為意義,從而獲取其中的空間特征與空間精神。反過來去識別建筑空間的內容與形式,分辨特定地域人文精神,以此探索建水文廟的保護與傳承方式,同時探尋對現代建筑空間營造功能與人文精神具有的指導意義。
圖表來源:
①圖6、7引自參考文獻[8];圖1、3、8、9、10、11由作者自繪;圖6、7改繪自參考文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