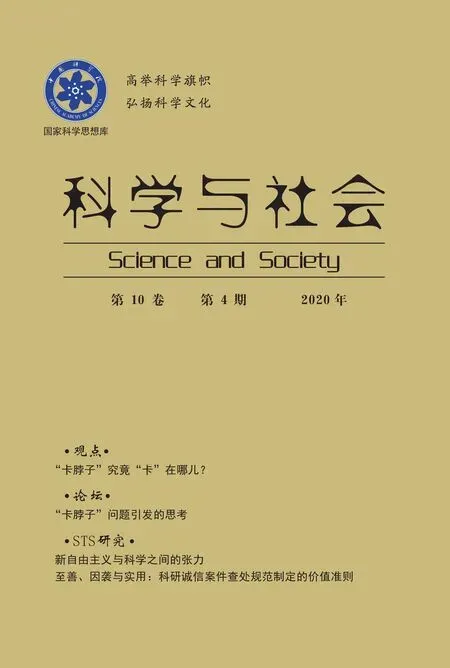重視基礎教育拔尖人才培養,解決我國“卡脖子”問題
鄭永和(北京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院)
焦點:中美之間競合格局的急速轉變使得高層次人才流動更加緊張,過去我國可以借助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人才交流吸引一些高水平科技人才,但當下我國必須著眼未來抓緊大量科技人才的自主培養,以此破解關鍵技術領域人才匱乏這一“卡脖子”問題。教育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的根本途徑,不斷涌現的創新型人才是國家擁有持久競爭力的根本保障,建設科技強國、實現創新發展最終還是要落實到教育。
近年來,我國經濟與科技實力大幅提升,科技發展從早期以開放、跟蹤為主要特征到如今實現了部分領域與發達國家并行、領跑的新階段。中美經貿關系逐漸由“合作大于競爭”向“競爭大于合作”轉變,雙方競爭格局開始發生顯著變化。為全面壓制我國發展,特朗普政府推行單邊主義和經濟霸權主義,從貿易、科技、人才等多方面對我國進行全方位打壓,試圖圍堵和孤立中國。2018年美國制裁中興事件發生后,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引起高度關注,圍繞搶占科技制高點的戰略競爭成為兩國博弈的核心議題。
實現科技創新,必須建立強大的創新科技人才隊伍。人才作為科技創新發展的第一資源,恰是破解美方壓制的關鍵“七寸”。那么, 相比美國我國科技人才的培養究竟如何?從人工智能(AI)領域來看,《2019全球AI人才報告》顯示,全球AI論文發表的學者中44%是在美國獲得的博士學位,我國本土培養的博士數量是其1/4;同時AI人才流動性很強,美國仍是對全球頂尖人才吸引力最大的國家。今年6月,《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名為《美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秘密武器:中國人才》的文章指出,“截至2018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公民中,有90%的人在畢業后會繼續留在美國至少5年,這些數字沒有下降的跡象”。直觀來看,我國科技人才流失現象嚴重,而且我國在科技尖端領域的拔尖人才培養仍有缺失,大多數人出國的初心是為了深造,不少人才在美國等其他科學技術強國成長為一流科學家。中美之間局勢轉變使得人才流動更加緊張,如果說此前我國還能借助美國進行科技人才培養,從而牽動我國部分行業的發展,那么當下我國必須抓緊自主培養大量科技人才,破解關鍵技術的人才匱乏這一“卡脖子”問題。
教育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的根本途徑,不斷涌現的創新型人才是國家擁有持久競爭力的根本保障,建設科技強國、實現創新發展最終還是要落實到教育。一方面,緊抓高等教育中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以超常規方式加快培養一批緊缺人才,為國家解決“卡脖子”問題實現最直接供給。另一方面,緊抓青少年科學教育,從基礎教育階段做好拔尖人才的充足儲備。面向未來30年后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宏偉目標,我國必須為青少年拔尖人才提供適當成長路徑,贏在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的最前端。
一是要更新對拔尖人才培養的觀念認識。教育公平不是指人人平均的教育,而是人盡其才的教育。公平的教育應當是為不同的學生提供適應其能力與需求的教育,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潛能。大眾對于拔尖教育即高智力兒童的精英教育的片面認識,導致基礎教育階段的拔尖人才培養在全國層面難以開展。正視拔尖人才教育是教育公平的重要體現,應當使有科學家潛質的青少年獲得拔尖人才培養機會,因材施教,助力拔尖人才發揮自身潛能。
二是要實現拔尖人才培養的體制創新。拔尖人才培養是一項系統工程,當前大多政策關注高中及高等教育的拔尖人才培養,但未能深入打通到基礎教育階段,形成對拔尖人才發現、保護、科學引導的合理體系。首先,在選才上加大拔尖人才的甄別力度,允許在基礎教育階段遴選科技特長中小學生,組織專家設計論證科學而靈活的選拔機制,也可借鑒國外做法,采用主動報名和學校推薦雙軌制。其次,在育才上支持設立科技特色天才班、科技特色學校,集中力量投入科技資源保障拔尖人才的專門培養,要讓那些有杰出能力又積極探索科學的青少年有學習和實驗的地方。最后,要保障成才學生的合理通道。
三是要重視拔尖人才成長規律的系統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了遵循青少年成長規律推進科學教育的戰略目標和發展方向,那么人才成長的規律研究必須得跟上,為拔尖人才培養提供理論保障。研究內容可包括但不限于:(1)對拔尖人才認知規律的探索,如拔尖人才的階段性成長特點、思維方式、環境影響因素等;(2)對拔尖人才教學培養的探索,如拔尖人才的評估方式、培養模式、教學支持等;(3)對拔尖人才社會支持的探索,如政策、體系、機制、社會文化等。
四是必須加強青少年整體對基礎科學的正確認知。基礎科學強調個體對外部世界的客觀認識以及動態的知識發現過程,要培養學生形成基于科學價值觀認同的科學行為與科學思維。如果青少年從小對“無用之用”的基礎科學缺少好奇,只是知道科學知識,但不知道科學知識怎么來的、科學何用、如何用科學思維方式解決問題,那么創新又從何談起?面向科技新時代,必須將重視基礎科學教育作為重要時代特征。
在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高考指揮棒作用下,一些具有特殊天賦的人才有時無法脫穎而出。2020年起啟動的“強基計劃”取代自主招生為拔尖人才提供了新的出口,旨在最大程度公開化、公正化實現人才選拔,但這一方式凸顯了“回歸高考”的特點,高考成績仍是人才選拔的主要標準,僅從分值占比上看,高校的自主權在一定程度是被縮減了。為解決培養儲備人才的“卡脖子”問題,必須正確認識“木桶效應”已不再適應當前時代,如何讓各類人才擁有足夠的平臺盡可能延伸自己的長板,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是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