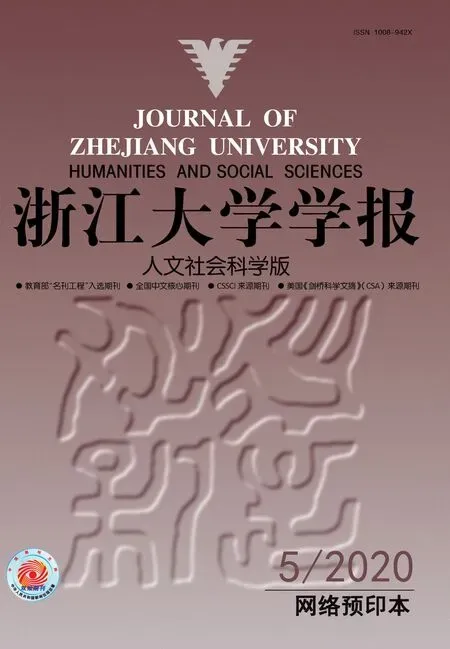電車難題新解: 兩難處境下的自由意志和自主責任
劉清平
(1.復旦大學 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上海 200433; 2.武漢傳媒學院 人文學院, 湖北 武漢 430205)
自從1967年英國倫理學家菲麗帕·福特(Philippa Foot)看似無意地提出了“電車難題”[1]后,半個世紀以來,許多哲學家甚至普通人紛紛圍繞這個成為思想實驗的著名案例及其不同版本展開了熱烈討論,尤其圍繞以效益主義(功利主義)為代表的后果論與以康德主義為代表的道義論的對立闡發了各種見解[2][3]22-25。本文試圖從以往很少涉及的自由意志視角入手,針對人們業已提出的各種基本解決方案進行分析,著重考察在設定了“不可害人、尊重人權”的規范性正義底線的前提下,人們在選擇這些方案應對電車難題時應當承擔怎樣的自主責任,由此揭示道德兩難的癥結所在。
一、 電車案例的兩難特征
從本質上看,電車案例無疑構成了道德兩難的典型表現:面對兩種倫理德性或道德義務不可兼得的對立沖突,同時又難以在它們中間分出主次輕重,人們該如何選擇?
一般來說,由于人的有限性等原因,在現實生活里,人們不可避免地都會遇到諸善沖突的局面:兩個(或幾個)好東西都是可欲的,卻無法同時兼得,怎么辦?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沖突都有資格算作“兩難”,因為倘若人們很容易權衡兩種善的主次輕重,盡管也要面臨兩選一的取舍,卻談不上有什么困難,那么只需遵循人性邏輯的“取主舍次”原則就是了,所謂“兩善相權取其重,兩惡相權取其輕”。只有在兩種善的重要程度不分上下的時候,人們才會落入不知道選哪個好的境地。比方說,假如只需花掉月工資的五分之一就能治好嚴重的疾病,很少有人會猶豫不決;可要是耗盡積蓄還不見得能夠治好癌癥等疾病,人們十有八九就要犯難了。人們常說的“這是一項艱難的選擇”,大都是針對這類權衡起來十分糾結的兩難局面來說的。
澄清了兩難概念,電車案例的定位也就清晰了:第一,它涉及的是兩種值得意欲的道德善(救五個人還是救一個人)的沖突。假如六個人都有機會活下來,沒有誰還會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第二,人們很難對兩種道德善的主次地位加以權衡,因為不管怎么選似乎都會出現麻煩。
誠然,這里也會出現一個疑問:救五個人與救一個人相比,應該說是很“大”的優勢了,選擇起來怎么還有難處呢?從某種意義上說,要是效益主義拒絕用任何道義原則修正自己,它就會這樣認為,因為按照它最純正的原初立場,不僅好的(后果)直接就是對的(義務),而且人們面對沖突時只要從大小多少的定量視角進行權衡就夠了。換言之,對邊沁式的純粹效益主義來說,電車案例算不上兩難:既然付出死了一個人的代價救活了五個人,相互抵消后多出了四條命的凈盈余,自然就實現了量上的最大收益,因此與死五個人保全一個人的選擇相比,完全符合“最大多數最大福祉”的基本原則。
然而,這種解答明顯與普通人的道德直覺相抵觸。面對西瓜芝麻等物品,取五舍一的做法可以說是天經地義,但是,面對人命關天的大事,它的軟肋立刻就暴露出來了:我們怎么能夠如此輕率,為了讓五個人活下來就讓一個無辜者死去呢?于是,人倫關系不同于人物關系的特殊性,就把只計算大小多少的純粹效益主義逼進了死胡同,哪怕求助于邊沁“一個只算一個”的命題也找不到出路:雖然這句名言表面上看彰顯了個體的重要性,但簡單地扳手指計量,還是會讓“孤零零”的一條命在“人多勢眾”的五條命面前顯得微不足道。眾所周知,電車難題特別是那些極端的版本,正是沖著純粹效益主義的這個阿喀琉斯之踵來的。一個在它看來很容易解答的問題,卻會讓它的答案落入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窘境。
主要出于這個原因,黑爾曾站在效益主義的立場上極力貶低電車案例,認為它脫離現實,缺乏說服力[4]139-140。其實,這種理屈詞窮的回避態度根本就站不住腳。思想實驗的確不同于技術實驗,只能圍繞理論上設計出來的抽象場景展開分析演繹,幾乎沒辦法在日常實際生活里檢驗。但要是我們因此斷言電車難題忽視了人生在世的具體內容,缺乏現實意義,沒有必要深入探究,好像就有點強詞奪理了,甚至是忘記了下面的常識:任何倫理學理論都不可能只是細致而微地直接處理張三李四在日常生活中實際遇到的具體道德問題,卻拒絕結合像電車難題這樣生動形象的特定案例展開邏輯上的理論分析。無論如何,如此多的普通人在如此長的時間里熱衷于參與這個思想實驗,還發表了大量針尖對麥芒的鮮明見解,就充分證明了一點:電車案例遠比當前倫理學界關注的眾多理論問題更有現實意義,更值得我們認真嚴肅地正面應對,而不可僅僅因為它向我們的規范性立場提出了嚴峻挑戰,就采取鴕鳥政策予以回避,因為那樣只會讓我們的理論研究更加不接地氣,最終淪為學究式的空談。
這樣辨析之后,我們就能發現一個有點反諷意味的事實:盡管直到今天人們仍然傾向于認為電車難題構成了針對后果論的嚴峻挑戰(它也的確觸及了后果論的致命弱點,即只從定量角度計算善惡后果的大小多少,卻忽視了定性維度上的主次輕重),但它歸根結底是道義論才會面臨的一場噩夢。如上所述,倘若將自己的原初立場貫徹到底、不加修正,純粹效益主義雖然也會覺得死了一個人有點可惜,卻不會認為取五舍一是個多么艱難的選擇。倒是強調“人是目的”的康德主義式道義論和人們的日常道德直覺,以及那些用“一條人命也很重要”的道義原則修正了自己原初立場的非純粹效益主義,才會在救五個還是救一個的問題上犯難,以至于打出了“權益”這張定性王牌的自由主義也會感到棘手:單靠定量計算支撐起來的取五舍一固然無法接受,但要是為了尊重一個人不可侵犯的神圣生命權,就讓五個人同樣不可侵犯的神圣生命權被否定,豈不是也說不過去?如果說一個人是目的,難道五個人就不是目的了嗎?如果在同樣神圣的生命權之間出現了沖突,我們該賦予哪一邊的生命權更高的權重,或者說該讓哪一邊的生命權更神圣呢?通俗一點說,兩邊出的都是至高無上的“權益”王牌,到底哪一邊能夠壓過另一邊呢?嚴格說來,兩難之難的關鍵就在這里,不然也不會出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僵局了。
為了走出僵局,本文試圖在堅持不可害人、尊重人權的規范性正義底線的前提下,引入自由意志的視角(當然不是西方學界依據二元對立架構談論的那種在決定論氛圍下甚至搞不明白是否真實存在的自由意志,而是人們在日常生活里實際擁有的與因果必然鏈條保持兩位一體關系的自由意志),仔細辨析人們在不同選擇方案下理應承擔的自主責任[5-6]。事實上,由于自由意志在哲學上被看成空虛幻覺,同時由于人們在把電車案例當成思想實驗討論時,較少考慮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必須承擔的自主責任,以往學界很少從這個視角探究人們應對電車難題的選擇方案,結果留下了一片盲區,沒有意識到解開這個難解之謎的關鍵恰恰就在其中。此外,由于電車案例的原初設定,人們主要提出了兩種實質性的解決方案,即“取五舍一”與“取一舍五”,本文當然也無法另辟蹊徑地給出其他解決方案,而只能從自由意志和自主責任的視角出發,針對這兩種基本的道德選擇展開學理分析,以推進對此難題的反思。
二、 取五舍一的方案
本節將重點考察多數人認同的取五舍一方案,并論證一個觀點:不管面對哪種版本的電車難題,只要主體基于自由意志做出了這種選擇,他就要對一個人的死亡承擔自主責任,盡管性質和程度的輕重會視具體境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首先,在極端版本的情況下,如外科醫生為了通過器官移植治好五個病人而必須殺死一個健康的人,或者旁觀者甲從天橋上推下一個胖子以期擋住將會軋死五個人的失控電車等,主體哪怕完全是出于想救五個人的善良意志,不得已采取了這種直接剝奪一個人生命的手段,他都應當承擔有意殺害這個無辜者的道德責任乃至法律責任。與這種極為嚴重的自主責任相比,他救出五個人的善好收益雖然在定量維度上大出許多,在定性維度上卻可以說是無足輕重的,更不會因為五減一等于四的結果就能享有只應受到褒揚、無須承擔責任的德性資格。毋庸諱言,鑒于主體在此只有利他目的、沒有利己動機,他承擔的自主責任肯定不能與某人為了貪圖錢財或緊急避險的自私目的殺害一個人的自主責任相提并論。盡管如此,這種純粹利他的自由意志依然不足以讓主體免于譴責和刑罰,因為他為了實現這個就其本身來看的確高尚的目的,殘酷地將一個無辜者僅僅當成了工具,自覺主動地實施了殺害無辜的犯罪行為,卻絲毫沒有顧及無辜者的生命權益[7]。有鑒于此,即便受害者沒有親友為自己討回公道,恪守正義的法治體系也應當嚴肅追究主體的嚴重罪行(考慮到他的利他目的可以適當減少其刑期),否則就沒有履行法律理應承擔的保護每個人生命權益的基本使命。同時,這里還可以補充的兩點是:第一,外科醫生的自主責任要比旁觀者甲更嚴重,因為他是在冷靜思考、細致準備后才殺害健康者的,不像旁觀者甲那樣可能是在來不及考慮、一時沖動的情況下推下胖子致其死亡的。第二,倘若外科醫生是由于自己失誤造成了五個病人需要移植器官的局面,他還應當承擔更嚴重的自主責任,因為在他殺害健康者的自由意志里,多了一個“彌補自己失誤”的利己因素。
其次,在原初版本的情況下,即電車失控后兩條軌道上分別有五個人和一個人來不及逃離,假如旁觀者乙基于自由意志扳動道岔,操控電車駛入了一個人所在的軌道,他有理由因為救出五個人受到稱贊,卻仍然應當對這個無辜者的死亡承擔一定的自主責任。在這種情況下,造成電車失控的人應當對這個失去生命的無辜者承擔首要的責任。更重要的是,旁觀者乙的自由意志也不包含漠視受害者生命權益的因素,表現在他只是扳動道岔造成了無辜者死亡,并非有意殺死了無辜者,所以他承擔的責任要遠遠輕于外科醫生以及旁觀者甲。盡管如此,鑒于他業已基于自由意志參與到了事件中,并且自己想救五個人的直接干預間接導致了另一個無辜者死亡,那么,他救出五個人的功德依然無法抵消他造成一個人失去生命的負面后果。畢竟,假如旁觀者乙不干預,聽任電車自行行駛,這個人是不會死的(雖然那五個人會死),所以,他才應當對自己的積極干預導致這個無辜者失去生命的結果承擔責任,包括來自這個人親友的譴責控告以及他自己的內疚自責。從某種意義上說,旁觀者乙之所以有理由因為救出五個人受到稱贊,也是以他理應承擔讓一個人死亡的道德責任為前提的:他明知自己要承擔讓一個人死亡的自主責任,還是不惜自己受到責罰也要救出五個人。
最后,在原初版本的情況下,假如主體是電車司機,他自然應當做出取五舍一的選擇。同時,盡管這個選擇是他的職責所在,因而他沒有理由像旁觀者乙那樣受到稱贊,但仍然要對一個人失去生命承擔一定的自主責任。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第一,與旁觀者乙不同,無論他做出怎樣的選擇,身為司機肯定都要承擔造成他人死亡的部分責任,而造成五個人死亡的責任明顯比造成一個人死亡更嚴重。第二,假如司機并非電車失控的責任人,他對取五舍一方案承擔的責任甚至比旁觀者乙還要輕,理由與他不應當受到稱贊是一樣的:如果說旁觀者乙是基于自由意志主動干預的,那么司機在基于自由意志進行干預時,還受到了自己職責的內在約束,因為他作為司機本來就有義務操控電車的行駛方向。
從這個視角看,純粹效益主義的理論錯謬就很清晰了,因為按照它的原初立場,它必然會將這些不同性質的取五舍一方案混為一談,非但不去辨析主體分別承擔的不同責任,反倒會把它們統統視為既正當又高尚的德性行為來推崇。畢竟,倘若只從大小多少的定量角度看,所有這些選擇都達成了多出四條命的凈盈余,因而都為整個社會提供了量上的最大福祉。然而,這種按照它的原初立場可以說是一目了然的價值評判,至少存在兩個同樣一目了然的嚴重弊端。
第一,它忽視了關鍵的一點:善就是善,惡就是惡,無從抵消,不會對沖。事實上,即便在性質或數量上可以通約,好和壞也不可能單純通過量化計算的途徑不留痕跡地湮滅。例如,一個人失去生命之惡無法在“一個只算一個”的前提下,通過簡單相減的計量途徑被五個人維系生命之善一筆勾銷;一個人的手臂被砍下之惡,也不會因為他事后得到賠償并裝上了具有同樣功能的假肢就消失不見。從這個意義上說,純粹效益主義幾乎有點善惡不分的意味[8]。
第二,它只關注定量的后果,卻忽視了定性的動機。沒有看到哪怕同樣是一個人死而五個人活的后果,主體在不同情況下基于不同自由意志實施的行為也會導致他們承擔不同的自主責任,就像外科醫生與電車司機的取五舍一方案所表明的那樣。事實上,由于試圖在第一個弊端的基礎上將后果論的立場貫徹到底,幾乎不顧及作為動機的自由意志,純粹效益主義可以說完全回避了自主責任的問題,以致在取五舍一的情況下只會讓主體成為履行“最大多數最大福祉”的效益原則的道德模范,卻不去考慮死了(甚至是謀殺了)一個無辜者的嚴重后果。從這個意義上說,純粹效益主義顯然還有是非不明的缺陷。
其實,撇開人們在課堂問答和模擬實驗時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淡化自主責任的因素不談(畢竟不是在日常生活里實際做出真要承擔責任的艱難選擇),他們更傾向于認同電車司機和旁觀者乙的取五舍一選擇,卻不肯贊成旁觀者甲尤其是外科醫生的取五舍一選擇,這已經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日常道德直覺與純粹效益主義的鮮明對立,因為他們內心深處依然覺得,即便出于救五個人的高尚目的,有意殺死一個無辜者還是于心不忍的。但同時也有必要指出的是,無論在哪個版本中,那些認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毫無愧疚地取五舍一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了純粹效益主義的錯謬思路(在極端版本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因為他們只看到了這些選擇的更大善好后果,卻遺忘了它們同時產生的嚴重壞惡效應,沒有意識到這些選擇因導致一個人死亡甚至謀殺了一個人理應承擔的自主責任,反倒沾沾自喜于他們能救五個人的“高尚功德”。至于那種僅僅訴諸“會引起巨大社會恐慌”的理由反對極端版本下取五舍一方案的見解,骨子里實際上還是純粹效益主義的扭曲路數,沒有看到侵犯一個人的生命權益本身就屬于不可接受的嚴重之惡,無論這樣做是不是會引起“巨大”的社會恐慌。理由很簡單:哪怕沒有引起任何社會恐慌,有意殺死一個無辜者也是無法寬恕的不義罪行。
一些西方學者引入了“雙重效應原則(雙果律)”,試圖通過辨析“殺死”與“讓其死亡”的微妙差異,來區分不同動機主導下的類似行為的雙重后果,因此要比純粹效益主義的單向度思路更切近電車案例的復雜面目:外科醫生和旁觀者甲的做法是為了達成善的目的而有意采取了惡的手段,旁觀者乙和電車司機的做法則是在達成善的目的時,順帶導致了可預見的負面后果(副作用),因此二者之間存在質的不同[1,9]。不過,只有在此引入自由意志和自主責任的視角,我們才能進一步看到:不僅外科醫生和旁觀者甲的選擇是不可接受的,旁觀者乙和電車司機也應當對自己做法的可預見后果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并不能因為這些負面后果只是副作用就將這些責任推卸得一干二凈。實際上,“可預見”這個修飾詞已經潛含著這層意思了:雖然旁觀者乙和電車司機都沒有直接剝奪無辜者生命權的自覺“意愿”,但還是“知道”自己的選擇會間接導致怎樣的負面后果;假如他們對這種副作用一無所知,也就不必承擔相應的責任了。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是:恰恰由于他們只是“知道”自己選擇的副作用,卻沒有剝奪無辜者生命權的自覺“意愿”,他們承擔的責任才在實質上不同于不僅“知道”會生成怎樣的負面后果,而且還有“意愿”生成這種后果的外科醫生和旁觀者甲。
三、 取一舍五的方案
本節將重點考察少數人認同的取一舍五方案。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在原初版本以及類似版本的情況下,這種方案不是指旁觀者在失控電車的行駛方向尚不確定的時候,就積極干預主動操控電車駛入五個人所在的軌道(除非假設旁觀者希望造成更多人死亡,否則他們自覺選擇這種取一舍五的方案是很難理解的),而是指下面的情況:旁觀者在失控電車即將駛入五個人所在的軌道時,拒絕通過積極干預讓它轉向駛入一個人所在的軌道,而是消極旁觀,聽憑失控電車自行駛入五個人所在的軌道造成他們死亡。第二,雖然許多論者已經指出這種消極的不做選擇實際上也是一種自決選擇,但只有引入自由意志的視角,才能說明這種選擇的內在原因:旁觀者是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經過自覺的權衡比較后才自主決定不加干預或不做選擇的。
雖然課堂問答和模擬實驗沒有給出明確的記述,但我們沒有理由排除下面的可能性:旁觀者丙主要是因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才做出了不肯積極干預、聽憑取一舍五結局自行發生的選擇。換言之,即便在現實中真遇到了類似的場景,某些人基于僅僅看重自己利益的自由意志,對事件關涉到的那些人(主要是陌生人)的生死存亡也會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所謂“形同陌路”。當然,在這種情況下,電車案例對他們來說也不是什么道德上的兩難,而不過是件無意義的瑣事,所以也不必操心如何解決。毋庸諱言,其他人顯然有正當的理據批評旁觀者丙的冷漠,譴責他沒有樹立把所有人當人看的立場,但旁觀者丙的一大特征就是對道德上的自主責任無動于衷,因此任何批評譴責都很難對他產生實際影響。
相比之下,旁觀者丁主要是自覺意識到了身處道德兩難才采取了消極旁觀的態度,做出了不干預的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觀點就是第一節末提到的那種規范性立場的集中體現:無論五個人還是一個人的生命權,都是同等不可侵犯的,五張王牌合在一塊也還是壓不過一張王牌。即使沒有剝奪那個人生命權的自覺意圖,但如果自己基于自由意志積極干預做出了取五舍一的選擇,結束了一個人的生命,這種可預見的負面后果哪怕只是作為副作用,也仍然構成了道德上的不可接受之惡,會讓自己承擔起無力承擔的嚴重責任,因此只能在焦慮、沉重而又愛莫能助的糾結心態中,基于自由意志拒絕積極干預,聽憑取一舍五的結局自行發生。
毋庸諱言,與純粹效益主義的后果論思路存在嚴重的弊端相似,這種康德主義的道義論思路也有著難以否認的缺陷:旁觀者丁為了恪守不可害人的底線,不愿通過自己的積極干預造成讓一個人失去生命的可預見后果,以致不得不看著五個人失去生命卻束手無措,所謂“哪怕天塌下來也要堅持正義”。然而,因此產生的負面后果并不會因為他嚴格遵循了“絕對命令”的道德義務就可以忽略不計,讓他感到心安理得,甚至自以為道義在肩、無比正當。事實上,旁觀者丁自己肯定會因為無法對那五個人伸出救援之手而感到遺憾惋惜乃至內疚自責。這種內疚自責與旁觀者乙的內疚自責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旁觀者丁是因為自己無能為力只能聽任五個人死亡而感到內疚自責,旁觀者乙則是因為自己積極干預造成了一個人死亡而感到內疚自責。同時,由于這個原因,人們也會像批評旁觀者丙那樣,批評旁觀者丁對五個人的死亡無動于衷,甚至譴責他剝奪了五個人的生命權。但嚴格說來,這樣的批評譴責在指向旁觀者丁時,就不像指向旁觀者丙那樣擁有正當的理由了,反倒帶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道德綁架痕跡。因為旁觀者丁并不像旁觀者丙那樣冷漠,相反還對六個人的生死存亡十分關注,只是由于同等看重五個人的生命權和一個人的生命權,才拒絕主動干預。
進一步看,旁觀者丁這種充滿張力沖突的糾結心態還充分展示了道德兩難處境下的嚴峻挑戰,并且比那些心安理得地選擇取五舍一方案,甚至認為自己立下了“高尚功德”而沾沾自喜的人更具有道德上的責任感,尤其體現出對那一個人生命權的高度尊重。所以,不在道德兩難處境之中的人們對他提出的批評譴責盡管貌似慷慨激昂、十分高尚,但恰恰由于不在道德兩難處境之中,其失去了令人信服的正當基礎:不在場者憑什么強制性地要求在場者必須通過積極干預做出取五舍一的選擇,逼著他不得不承擔間接導致一個人死亡的重大責任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有正當資格和有正當理由提出這類批評譴責的,只有那些在道德兩難處境中不僅愿意積極干預,選擇取五舍一的方案,而且勇于承擔間接導致一個人死亡的自主責任的旁觀者。可是,恰恰因為這類人親身經歷過如此嚴峻的道德兩難,做出了艱難的取舍選擇,并且還在事后因為承擔沉重的自主責任而體驗到了強烈的內疚自責,他們通常不會批評譴責旁觀者丁,反倒更容易理解他做出的聽憑取一舍五結局自行發生的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在學界圍繞電車難題設計的模擬心理實驗中,有一種奇特的現象可以佐證本文的上述闡釋:某些人最初對取五舍一的方案持認同態度,但在得知軌道上的那個人是自己的親友戀人后卻改變了主意,不再認同甚至反對扳動道岔讓電車駛入一個人所在的軌道。一些論者還據此探究了親情、友情、愛情等情感因素在認知之外對人們的道德選擇具有的重要作用[10-11]。倘若引入自由意志和自主責任的視角,我們或許還會發現一些更深層的問題。
第一,這種現象從一個角度表明,原初版本下選擇取五舍一方案的主體理應對一個人的死亡承擔一定的自主責任。其實,導致這些人在得知有關身份信息后改變主意的首要因素就是,如果說他們原來覺得為了救五個陌生人讓一個陌生人失去生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他們現在卻覺得,為了救五個陌生人讓一個親友戀人失去生命就是不可接受的了,所以才不愿承擔由于自己的積極干預導致親友戀人失去生命的重大責任。換言之,假如他們原來認為取五舍一的選擇是心安理得、毫無愧疚的話,那么,改變主意的現象恰恰表明,這種見解其實是某種扭曲性的幻覺,抹殺了一個人生命權的重要分量。因為倘若主體不必為一個人的死亡承擔任何責任的話,他們也就沒有理由在得知這個人的身份信息后改變主意,拒絕像原來那樣認同取五舍一的方案了。不管怎樣,如果忽視自由意志特別是自主責任的因素,我們就無從解釋這些人在分別涉及陌生人和親友戀人的時候,為什么會做出如此南轅北轍的雙標選擇。
第二,如前所述,無論涉及陌生人還是親友戀人,只要不是出于無動于衷的冷漠態度,那么取一舍五的方案本身盡管存在一定缺陷,在道德上卻依然有正當的理據。然而,如果像這些人那樣原本認同取五舍一的方案,但在得知了有關身份信息后卻轉而認同取一舍五的方案,不僅邏輯上前后矛盾,道德上也潛藏著嚴重弊端。因為這種轉折實際上隱含了某種規范性的預設,認為親友戀人的生命權重遠遠超出了陌生人的生命權重,所以才會在同樣處境下出于不同的態度做出不同的選擇:一方面為了救五個陌生人寧愿讓一個陌生人死去,另一方面寧愿讓五個陌生人死去也不肯讓一個親友戀人死去。相比之下,那些得知了有關身份信息后沒有改變主意,依然認同取五舍一選擇的人雖然貌似六親不認、冷酷無情,卻在某種程度上與那些無論涉及陌生人還是親友戀人都始終認同取一舍五選擇的人相似,前后一致地流露出了平等看待每個人的道德意向,所以才不會在生死關頭將權重的天平不正當地偏向自己的親友戀人一邊——當然,這一點并沒有讓他們的取五舍一選擇因此就變得完全正當起來。
從這個角度看,當代英國哲學家戴維·米勒在論及電車案例時提出的那個帶有偏愛的倫理訴求,即“人們應搬動軌道轉撤器,以便電車撞死一個陌生人而非自己的配偶或孩子”[12]52,已經徹底打破了平等尊重每個人應得權益的正義底線,如同某些西方國度在法律上認同的緊急避險那樣,無法得到道德上的證成。比較而言,康德兩百年前有關“緊急法權”的見解倒是充分體現了“人是目的”的正義感:假如我在自己有喪命危險的情況下剝奪了另一個沒有加害我的人的生命,就像船沉落水后我為了活命搶走他人的木板而導致他人喪生那樣,盡管法律不會給予我對等的懲罰(判處我死刑),但我的行為仍然是不正當的,因為緊急情況并不足以讓不正當的事情成為正當或合法的[13]243-244。
綜上所述,與取五舍一的方案相似,對取一舍五的方案我們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而論,而必須結合主體在不同境遇下擁有的自由意志及其理應承擔的自主責任進行細致的辨析,才能深入揭示這種選擇的內在機制和道德屬性。
四、 電車難題的啟示
從上面的分析中不難看出,電車案例作為道德兩難,并不像某些論者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脫離現實、不夠具體、無關身份、無意義的空洞話題。盡管存在種種爭議,但只要引入了自由意志和自主責任的視角,同時堅持不可害人、尊重人權的正義底線,我們就能從中發現一些對人們在日常生活里處理類似局面很有意義的積極啟示,并且揭示后果論和道義論的缺陷和弊端。
首先,雖然兩難處境只是諸善沖突的一種特殊形式,但它迫使人們做出艱難選擇的嚴峻程度,卻充分突顯了導致所有諸善沖突的關鍵因素:人的有限性特別是實現自由意志的有限性。事實上,在這個思想實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一個預設前提:人們無法基于自由意志阻止失控的電車前行。假如有誰能像蝙蝠俠那樣,在生死攸關的緊要時刻突然現身,神通廣大地讓失控電車停下來,道德兩難也就煙消云散了,以致整個話題都變得像“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地生活下去”的童話結尾那樣欠缺吸引力。有鑒于此,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處理這類兩難處境,我們都應該牢記這個簡單的事實。要是我們自以為人沒有局限而無所不能,就很容易造成實然性和應然性兩個維度上的嚴重扭曲。
其次,諸善沖突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人們的理想愿景不可能真正實現。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分析性的命題:按照人性邏輯的趨善避惡原則,任何理想愿景的實質都趨于可欲之善,避免可厭之惡。但各種好東西的不可兼得,卻決定了人們無法達成所有的愿景,讓“既要、又要、還要、更要”的十全十美落到實處,而只能是陷入“有得必有失”的片面有限。尤其在相互沖突的兩種善都很重要的實質性兩難中,這種片面有限還勢必導致刻骨銘心的悲劇結局:你選擇了某種你看重的好東西后,會因為同時放棄了另一種你也看重的好東西而遭遇到嚴重惡果。電車難題或許是很少發生的現實案例,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會頻繁地面臨類似的緊要關頭,以致我們在艱難選擇中邁出的每一步都很可能決定我們的人生軌跡只能是封閉地朝著某個方向前行,卻杜絕了另外的可能,如:大學畢業后是讀研還是直接去工作?拿這筆錢投資辦廠還是去炒股?換言之,諸善沖突從根本上決定了人的有限存在的殘缺冷酷。要是我們不僅自以為無限全能,而且還戴著玫瑰色眼鏡溫情脈脈地打量這個世界,一味想要得到所有的可欲之善,注定會碰得頭破血流。說穿了,既然面對的是“兩難”,就不可能有“容易”的解答。
再次,正是諸善沖突迫使人們在“善惡好壞”的價值標準之外,還要訴諸“是非對錯”的價值標準。如果不存在相互抵觸的現象,人們只要遇到喜歡的好東西就追求,遇到反感的壞東西就避免便夠了,完全沒必要考慮正當還是不正當的問題。可是,一旦出現了諸善沖突,情況就變了:兩個東西都是可欲之善,卻無法兼得,于是就要權衡它們的主次輕重,再按照取主舍次的人性邏輯展開選擇。更重要的是,人們在做出這類取舍時,關注點也不像后果論斷言的那樣僅僅聚焦在“怎樣選擇更好”上,而是首先聚焦在“怎樣選擇才能防止不可接受之惡”上,從而在“值得意欲還是厭惡反感”的善惡標準之外,又確立起“可以接受還是不可接受”的是非標準:如果某種選擇足以防止人們認為的不可接受之惡,他們就會認為這種選擇是對的;反之,倘若人們在選擇時只考慮“怎樣選擇更好”,卻忽視了“怎樣選擇才能防止不可接受之惡”,以致生成了嚴重的惡果,他們就會認為自己做錯了。旁觀者丁可以說是以訴諸是非標準的方式處理電車難題的,盡管取五舍一的方案能夠生成救五個人的“更好”后果,但由于它同時還會導致一個人死亡這種不可接受的副作用,讓自己承擔無力承擔的嚴重責任,所以是不對的,應當拒絕。
復次,由于上述原因,電車案例的道德兩難清晰地展現了后果論與道義論的弊端和缺陷:對后果論來說,它的嚴重弊端就是忽視了善與正當的深度區別,將兩者混為一談了,以為好的就是對的,卻忘了在沖突情況下為了實現更好的后果,很可能產生不正當的惡果。對道義論來說,它的內在缺陷則是把善與正當割裂開來,嵌入到二元對立之中了,認為關涉正當與否的道義與關涉善惡內容的后果之間沒有什么關聯,而僅僅取決于所謂的理性立法、邏輯一致、可普遍化等,未能看到正義的底線恰恰在于防止不可接受之惡,也未能指出在沖突情況下遵守某一條道義原則,同樣有可能導致負面后果的殘酷現實。比較而言,后果論的弊端要比道義論的缺陷更為嚴重,因為如果說道義論主要是在理論上把善惡好壞與是非對錯割裂開來了,那么,后果論不僅在理論上把善惡好壞混同于是非對錯,同時在實踐中,也會因為鼓勵人們為了實現“成功”的目的不惜打破“正當”的底線,而造成不可接受的惡果[14]。以電車難題為例:后果論會慫恿人們在外科醫生和旁觀者甲的情況下,主動選擇取五舍一的積極干預方案,甚至因為達成了救五個人的“更好”后果沾沾自喜,卻對一個人的死亡甚至被殺害的所謂“小惡”視而不見。相比之下,受道義論影響的人們在選擇取一舍五的消極旁觀方案時,雖然可能沒有自覺地意識到,但歸根結底還是會自發地把一個人失去生命的可預見后果看成不可接受的嚴重之惡。
最后,在任何兩難境遇下,尤其在像電車案例這樣的實質性兩難境遇下,只有打破后果論與道義論各執一端的僵化模式,我們才能找到解決難題的正確思路:牢記人的有限性特別是實現自由意志的有限性,遵循趨善避惡、取主舍次的實然性人性邏輯,堅守不可害人、尊重人權的應然性正義底線,自覺地意識到各種可供選擇的取舍方案可能導致的不同善惡后果,然后基于自由意志做出自決選擇,并且勇于承擔自主責任。舉例來說,倘若你不忍心看到五個人失去生命而拒絕消極旁觀,想要積極干預救出他們,那么,第一,這種干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有意剝奪無辜者的生命,因為那樣就會突破不可害人的正義底線。所以,假如你處在旁觀者甲的位置上,你可以自己跳下去擋住電車,并且因此得到人們對你舍己救人行為的高度贊美,卻不可把那個胖子推下去。第二,在做出任何符合正義底線的積極干預后,你也應當勇于承擔這種直接干預間接導致一個人失去生命的道德責任,卻不可因為救了五個人就自以為高尚無比。以此類推,哪怕你是為了迫使恐怖分子說出核彈藏在哪里的秘密,才殺害了他無辜的孩子,你也沒有理由因為救了無數人就自以為功德無限,而依然應當勇于承擔自主責任。對想要做出其他選擇的人們來說,情況同樣如此:只要你是基于自由意志做出了自決選擇,你就無可推卸地應當對這些選擇的后果承擔自主責任。
從某種意義上說,以不可害人的正義底線為前提,強調兩難處境下的自由意志和自主責任,在理論和實踐中首先是針對那些受到后果論影響,只想追求完美結局,卻忘了防止不可接受之惡的見解和做法。問題在于,這類見解和做法忽視了人的有限性,沒有看到人們在諸善沖突中根本不可能實現兩全其美的圓滿結果,而只能是落入有得有失、善惡交織的悖論性結構。實質性的道德兩難尤其殘酷,如同電車案例那樣,不管人們做出怎樣的選擇,別說生成“更好”的結局了,就連完全符合“對”的基本道德標準也很難做到,相反總是既包含了某些正當的因素,又包含了另一些不正當的因素(要么五個人、要么一個人會失去生命)。所以,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即便我們基于大愛無疆的良好意愿想要成就盡善盡美的烏托邦,也可能會在努力實現最大多數最大福祉的同時,造成侵犯某些人應得權益的不義之惡,就像外科醫生或旁觀者甲的做法那樣。其實,由于種種不可抗拒的自然和人為原因,在這個并不那么美好、反倒有點殘酷的世界上,總會有人遭遇像罹患不治之疾、搭乘失控電車這樣的不幸苦難。我們雖然有必要遵守不可害人的正義底線,盡力防止和嚴厲懲罰任何侵犯他人權益的邪惡罪行,卻不應當以無所不能的救世主自居,想當然地以為自己能夠無所不能地干預一切,將所有處于不幸苦難之中的人統統拯救出來,甚至不惜自敗地做出坑人害人、侵犯人權的不義之事[15]。
有鑒于此,處在人的有限性導致的諸善沖突特別是道德兩難局面中,我們能夠并且應當做到的,不是為了追求皆大歡喜的美好愿景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坑人害人、侵犯人權的不義之事,而是腳踏實地地基于自由意志,守住正義底線,承擔自主責任,哪怕為此要克服種種障礙,付出沉重代價,遭受挫折失敗,感到遺憾沮喪。